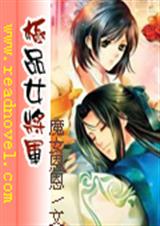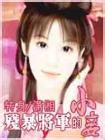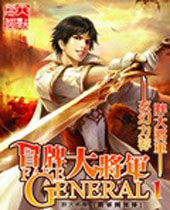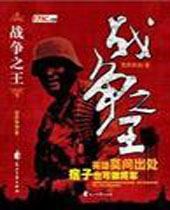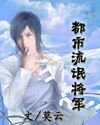隐形将军-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隐形将军韩练成
韩兢
1。母子俩奋力破开废墟
2。参加北伐战争
3。这块冥币“救”了韩圭璋的命
4。这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5。他与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
6。究竟为谁而战,他想不清楚
7。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8。参加张学良办的露天舞会
9。结果不是这么回事
10。他拒不交代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
11。更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
12。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3。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
14。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
15。周恩来说:如果有急事,董老会派人跟你联系
16。韩练成接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指示
17。开始单方面采取行动,掩护琼纵
18。由我们两人直接见面
19。把董必武接到白崇禧的公馆
20。党中央希望我做些什么
21。可以先在这几个方面达成协议
22。你们要和敌人斗智斗勇
23。必须设计一种两全的方案
24。韩练成拖住了李仙洲集团
25。李仙洲满脸疑惑
26。周恩来同意韩练成返回南京的要求
27。韩练成的危机化解了
28。蒋介石说:“我想单独听听你的想法。”
29。韩练成身边仍然危机四伏
30。秘密会见潘汉年
31。韩练成心里有了底
32。他来干什么
33。突然有了对策
34。危机已经到了身边
35。亲自送韩练成到机场
36。不要让同船的任何人知道韩练成的真实身份
37。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
38。一生中和毛泽东的唯一一次谈话
39。加入中国共产党
隐形将军
一个被冯玉祥誉为“在北伐时与我共过患难”的青年军官,一个在中原大战的危机中救出蒋介石的勇将,一个统御桂系主力在正面战场奋战的抗日将领,一个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最高机密的智囊,但,他同时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单线联系……中共军事情报工作领导者李克农上将称他为“隐形人”,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称他为“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他就是“隐形将军”韩练成。韩练成唯一的儿子韩兢先生潜身史海,遍访前贤,历尽了20余年的遥遥心路,拨开重重迷雾,写就《隐形将军》(近日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该书展示了一代开国名将的人生传奇,解密了一段令人神往的激情岁月。本报今起首家节选连载。
1。母子俩奋力破开废墟
韩练成1909年2月5日出生于(今)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山区一个叫谷地台的山村,属鸡。韩练成的父亲名叫韩正荣,早年曾在清军董福祥部队当兵。母亲娘家姓樊,是陕西乾县人,1901年家乡闹灾,她16岁,被族人带出来,卖给在固原巡防营做哨官的韩正荣为妻。不几年,韩正荣因腿上有伤,退伍务农,家境每况愈下。好在有木匠手艺,又有行伍的经历,在五里八乡人缘很好;樊氏性情泼辣、很能吃苦耐劳,家里虽然贫困,却能勉强过得下去。韩正荣是独子,只有几个叔伯兄弟,他和樊氏共生育过四个孩子,三个先后夭亡,只有韩练成一人活了下来。
民国9年(1920年)12月16日20时06分,震中位于(今宁夏)海原西安州至干盐池、烈度12的8。5级特大地震爆发。根据当时的记录,海原—固原—隆德一带死亡12万余人、大牲畜15万余头,房屋倒塌4万余间。那天,韩正荣在固原给人帮工多日,家里只有韩练成母子二人。韩家位于一个土崖边,有一孔不能住人的窑洞、两间偏东南向的一明一暗的土坯房。韩练成总是睡在暗房炕上靠隔墙的一边,因为墙那边就是灶台,暖和一些。
地震发生时韩练成睡得正酣,他被强烈的摇撼和母亲嘶哑的呼唤声惊醒了,又被令人窒息的烟尘呛得喘不过气来,他看不到光亮,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几乎不能转动的狭小空间里。他好像听到母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喊着,于是他尽量大声回应,却被烟尘呛得连连咳嗽。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母亲遇到了危难。一种强烈的本能促使他向母亲呼喊的方向拼命寻找出路。他摸到了一把刀,用力在阻隔他出路的障碍物中寻找缝隙。此时,他才弄明白过来,困着他的不过是坍塌的屋顶。他憋住气,在晃动中奋力破开一个巴掌大的洞,烟尘像烟筒一样冒了出去,冷风也猛地钻了进来,他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也在暗红色的黑雾中依稀看到母亲惊恐异常的脸。母子俩不再出声,奋力破开废墟。韩练成被拉出来时,身上除了土和灰,竟然连一点损伤都没有。但母亲的头上脸上却被灰土眼泪糊得变了样,双手染满土和血。
强震后,黑雾中的山村已成一片废墟,天际闪现着令人恐惧的红光,伴随着地底发出的雷鸣声,人们的号哭惊叫声不绝于耳。余震中,大地像巨浪中的破船一样摇晃着。在村民们的挣扎自救中,母亲很快从灾难的恐惧中镇定下来,她不知道窑洞能不能住,于是叫韩练成找出能用的东西,并把不能再用的、能烧的都集中起来,在废墟中垒了一个能避风寒、能取暖的小窝。母子俩没有来自家族的支持,也不知道韩正荣是死是活,目前最重要的是,在韩正荣回来之前,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第二天晚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大雪飞扬,韩正荣赶回家时韩练成已经睡着了。
天还没大亮,父母已经收拾停当,全部家当分成三份:除每人一份干粮、熟肉外,父亲背木料、粮食、羊肉,母亲背被褥、粮食,韩练成背锅灶。看到父亲后腰那把锋利的斧头、母亲被褥中露出的刀把、自己腰间的快刀,韩练成心里丝毫没有背井离乡的凄凉感,反而产生一股兴奋:哈哈,这不是四处漂泊、浪迹天涯了吗!父母把能用却背不走的东西分给邻居以后,就带他上路了。
2。参加北伐战争
没有了土地,流向城镇的农民是一群失去根的人。好在韩正荣有过多年行伍的经历,又有木工手艺,因此并不太在乎流动;樊氏也找到一份为人缝缝补补、拆拆洗洗的零活,很快,一家人就顺其自然地汇入了城镇最底层、最边缘的人群。
韩正荣夫妇眼看儿子渐渐长大,虽然可以帮他们打个下手、挑个水之类的,长期下去也总不是个办法。于是,他们送儿子去读私塾,那年韩练成12岁。韩练成一边念私塾,一边帮工。课外,只要能找得到的书,他拿到手就看。他知道那会儿是民国,但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洋总统徐世昌谁比谁大、谁管谁,他还搞不清楚。当然,他看的大多是流传在民间的残缺不全的话本和章回小说,那时最向往的就是成为像小说中的侠士高人。一天,城里来了一个给黄埔军校招生的老师,他的条件是要中学文凭。夫妻两人商量妥了:与其看着儿子和自己一起自生自灭,真不如让他从军,况且这是去上学做军官,不是当大头兵,远比“当兵吃粮”要出息得多!于是,樊氏从做零活的东家家里借了甘肃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生韩圭璋的文凭,让儿子假冒“韩圭璋”之名报了军校,出生年月也随着真正的韩圭璋改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了。韩练成离家的时候,父亲正在病中,母亲也没有任何迟疑:“你只管放心去,有命穿个绸裤子,打死就算妈没养!”儿子心里的志向远比“绸裤子”大,他一定要挣到二百元钱,回来开一家铺子,这样全家人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师生五人徒步走出山区的途中,韩练成已经改用“韩圭璋”的名字了。他们迎着隆冬的风雪,越过了残缺的长城和冰封的黄河,那种苍凉、肃杀却又充满悲壮的景象震撼了韩圭璋的心,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报国之志”中的“国”字的真实存在。
但谁都没想到,他们只走到了宁夏(今宁夏银川),韩圭璋就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经过简单考试,于1925年元月被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录取;而那老师却独自一人去了苏联,此后再无音信。韩圭璋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为黄埔招生却把他们送给了宁夏。韩见到的招生简章要求他们在8月25日以前入校,如果当时他真的上了黄埔,应该是第三期,也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黄埔生。教导队的学习、训练使韩圭璋很快适应了军旅生活,这个借来的“学生”身份也让他一下子脱离了城镇贫民低下的社会地位。走出山区时,他的黑布棉袄、棉裤使他在其他学生中间显得极不协调,他的发型、举止、谈吐,甚至连眼神都和那些真正的学生不同。但是,在军营“求同”的大趋势中,大家都剃了光头、统一了着装、规范了日常用语,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兵”生活,韩圭璋从父亲那里承袭下来的军旅基因被激活了,他的体能好、协调性强,在众多的学生兵中崭露了头角。
1926年9月,韩圭璋所在的西北陆军第七师正式被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师长马鸿逵升任军长。部队向西安进发时,已经是排长的韩圭璋知道,他们是国民军联军十路援陕部队中的第四路主力。守西安的是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李虎臣和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所部一万人,他们被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刘镇华的镇嵩军的十万人马围着打了半年,真正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史称“二虎守长安”。
国民军联军的总司令是冯玉祥,那是一支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军队,军事政治顾问是苏联的乌斯马诺夫,总政治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刘伯坚。冯总司令的进军方略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马鸿逵的第四军虽然军阀积习很重,但在改编后,联军总政治部派来了共产党人刘志丹任政治处长,部队作风有了明显改善。朝会时,长官训话,士兵们则高唱冯玉祥亲自编写的《出操歌》《吃饭歌》《射击歌》等歌曲。像韩圭璋这种学兵出身的新军官,对新思想、新作风接受得很快。多年以后,韩练成还记得当时的《吃饭歌》:“这些饭是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人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3。这块冥币“救”了韩圭璋的命
一天晚上,疏星历历,部队在干涸河道及两边荒坡上快速行进。韩圭璋是当日的值星排长,走在大部队中段右翼外沿作侧卫的连队前面,依稀看见前方地上似有一物闪闪发光,他刚刚弯腰去捡,突然枪声响起,身后已有战士中弹,他就势卧倒滚入凹处、拔枪探视,枪声是从右前方坟地和更远一点的破砖窑处传来的,听着只有两三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也不像大部队伏击。连长命韩圭璋率两个排出击,对面敌人很快就缴械投降了,原来只是一个不满员的加强连,本来想隐藏起来,等到国民军联军大部队过去再说,眼看藏不住就打,可打开了又怕,联军一还击他们就缴枪了。这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遭遇战是韩圭璋从军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险情,在他受降将俘虏枪支清点上缴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左手一直紧紧攥着、慢慢张开的,竟然是一块幽幽闪光的冥币!如果他没有弯腰去捡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他肯定在敌军的第一波射击中倒下,非死即伤。这块冥币“救”了韩圭璋的命,也“帮”他立了北伐出征后的第一功。
在韩圭璋担任军部警卫手枪营排长时,一天宿营,刘志丹路过警卫营驻地,就近在韩圭璋所在的连队住下,和他挤在同一间民房里。那天,偏巧连里抓到联军其他部队的两个逃兵,已经被脱光了上衣绑着示众。当年逃兵被抓到的下场是很悲惨的,被当众打个半死也是常事,不经审判就枪毙更是司空见惯。连长是马部的老军官,小有心计,他知道有军部大员在场,无论自己怎样处置,都不一定妥当,于是“请刘处长指示”。
刘志丹不假思索,就说:“把衣服穿上,先关禁闭,明天再叫他们团来领人。”连长下令执行。韩圭璋不理解,刘志丹说:“严肃军纪、严守军法是必要的,违反军纪一定要处分;处分处分,处理得要有章法、有分寸,咱是革命军,不能沿袭旧军队、军阀部队随便打人杀人的恶习。”韩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很感兴趣,那天谈到很晚。刘志丹是黄埔四期的学生,韩说自己对黄埔军校“救国、革命”精神的印象极深,毕竟他当年向往的本来就是黄埔军校。
11月,国民军联军援陕总指挥孙良诚部(援陕第三路军)已在西安接敌,马鸿逵部抵近咸阳后,韩奉命押送数十万发子弹给孙部。28日,西安解围,尸横遍野,满目都是饥寒交迫的军民。韩圭璋当时已升任步兵五十五团连长,率部押粮由东向西进城,是马部进入西安的先头部队。国民军联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见到韩时,重重地拍着韩的肩膀,惊异地说:“哎呀,这娃是连长?好好好!咱兄弟一见如故!”旋即握住韩的手不放。
1927年初的西安,已经不见解围初时的惨状。满街都是反帝反封建标语,到处都可以看到列宁、孙中山肖像。冯玉祥到西安以后,经常到下属各部队指导训练,军官的集训也日渐频繁起来。他的方法是:先教官,官学会了再教兵。当时,冯还亲自向营以上的军官教授战术,他带来的教官则教授单兵军事技能。韩圭璋杠架(单双杠)看一遍就会,伏地挺身(俯卧撑)一口气可以做七八十次,队列、射击、劈刀、拼刺、投弹、目测、口令、号音等更是一学就会,集训中曾多次受到冯玉祥的夸奖。
在军事集训的同时,总政治部主办了多次政治集训。韩圭璋参加了一次由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亲自授课的集训,受训的都是从各部选调出来的连长和连一级的士兵委员会主席,共有21人。刘伯坚、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邓飞黄、简又文都讲过课,韩圭璋记得当时学习的内容有“建国大纲”、“三大主张”、“苏维埃”、“二十一条”,等等。有位共产党员教官教唱《国际歌》,那时的歌词是“……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集训期间,刘伯坚、刘志丹曾单独找韩圭璋谈话。说到参加革命军的想法,韩照实回答:“我是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