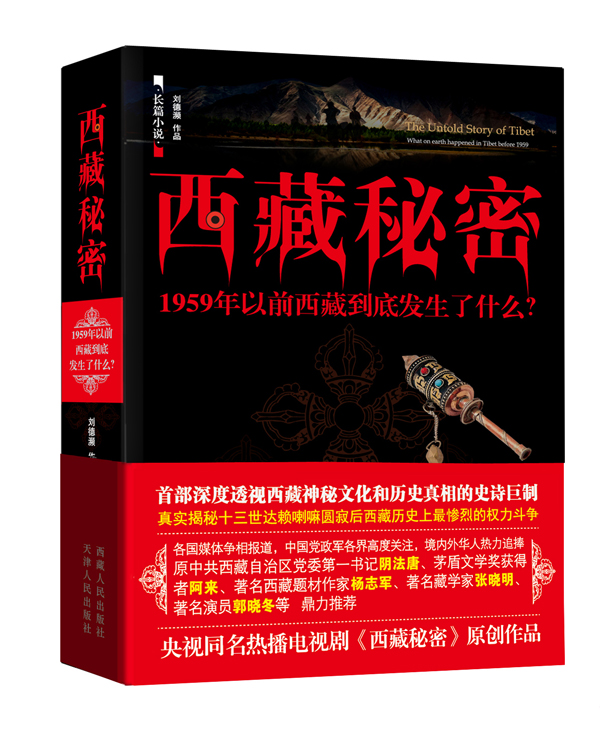西藏·远方的上方-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远方的上方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1)
一
现在我得说说我的这趟旅程了。我一直回避我初次进藏的缘由是因为它实在乏善可陈。我的周围有许多朋友去过西藏,他们总是比我勇敢、果决并富于牺牲精神,进藏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构成一次事件。我的一个朋友是在赴美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变卖了所余的家产,独自去的西藏。他说,离婚对他的打击说不上致命,他想凭借残存的毅力和理智,努力使自己不至跌倒,身体却不听使唤,变得脆弱。一些细菌乘虚而入,神秘地植入他体内,他感觉到它们在迅速成长、扩散,也许正演变为癌症,因此产生的忧惧令他燃起对冰清玉洁的高原的神往。喜马拉雅,多少次来到她的门槛,又掉头而去,就像个经过长途跋涉未洗征尘自惭形秽的人,觉得尚未做好觐见女神的准备。这一次,他准备了两个星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次漫长的准备,把他一步步推到西藏的门口。因而,西藏在每个人生命的重要关口等待着大家。西藏不仅仅表现为空间,也表现为时间,这会在某一个神秘的时刻,与每个人发生联系。一个人无论距离西藏有多远,他都可能在某一时刻来到西藏。不知西藏是否真的成为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诊所,再沉痛的精神创伤在西藏都会神奇地痊愈?是它不识人间烟火的圣洁融化内心的阴霾,还是人们从西藏的生存极限中获取了某种自信和资本?或者它六道轮回中的生命规则比触手可及的神灵更鲜明地提供了某种暗示?我看到人们前赴后继地进行着精神实验,把一颗如核桃般枯涩坚硬的内心放在缺氧的环境中,等待它在阳光执拗的照耀中重新发光。人们把进入西藏当作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对此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但我从未去过西藏,因而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对西藏的误读。
二
我的少年时代没有幻想,当然为应付老师而写的作文不计在内,在作文里,我的理想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些年中,西藏是以一部充满雪斑的黑白片的形式存在于心的。那部据说在今天看来仍是艺术经典的电影,一开头就以一幅被腰斩的农奴的画面给我一个下马威,以至于在今天,神经足以经得起美国恐怖片考验的我,始终没有勇气重温这部老片。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其中的许多细节。在那部电影里,农奴强巴因为为寺庙的佛像涂金,被金粉迷了眼睛而双目失明。很多年后,我迷失在哲蚌寺,无意中闯入一个殿堂。一尊身高达数十米的巨大佛像令我怵然一惊,这不仅因为这个我平生所见最为巨大的躯体,使我除了仰视和匍匐不能采取任何其他的姿势,更因为它的丹凤眼所透露出的那种温暖、容忍、慈爱,无法用虚假二字一笔勾销。我在整个成长年代里被训练出的对它的敌意顿时不见踪影。午后的哲蚌寺,宁静、慵懒,空无一人,我感觉到被神明注视的幸福和荣耀。我不知该感激神明,还是感激像强巴一样奇妙的手。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再高明的工匠也不可能虚构出一个如此“真实”的神,它本来就在那里,等待神奇的手在空气中复原它身体上每一个应有的曲线。这让我确信自己是在西藏。我从不拜佛,只有在西藏,我那么自然地匍匐在地。
没有亲历过阶级斗争的这一代人注定让所有苦口婆心的阶级教育泡汤,这一点如同夏虫不可语冰一样毋庸置疑。对暴力的渲染已经无法令我们少见多怪,即使在内地的任意一个地方,极权时代的暴力也毫不逊色于旧西藏的剥皮抽筋。在灵魂深处,青春的力必多开始挤占意识形态的份额,这时的西藏,被各式各样的包装裹携,出现在我们面前,势不可挡。与老旧的黑白片对照,它绚烂、神奇、浪漫,刚好为青春期供大于求的力必多指明了去向。或许因其无与伦比的高度,西藏是一个迷路的人最容易选择的目标,更何况它有着百变之身,变成无数明媚妖娆的照片,变成李娜、朱哲琴、韩红的歌声,扎西达娃、马原、马丽华、巴荒的文字,《藏地牛皮书》,以及在盗版光盘上才能目睹的洋人的胶片,煽动我们的双腿。我明知与少年时期的阶级教育一样,这时的西藏已被众多的来路不明的符号所绑架,它所发出的未必是自己的声音,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对西藏的向往。西藏是横在我面前必须迈过去的一个界限,由于我的软弱,我一再拖延自己的行程。
于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余纯顺成为一个大英雄。他的业绩是徒步走过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它的壮举并不比一个普通藏民更加伟大,因为藏民们不但要在藏区徒步行走,而且经常要负重、劳动、应付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即使是徒步朝拜,其强度亦丝毫不亚于铁人三项赛。如果余纯顺是伟人,那么我就更应该向高原上的每一位藏民致敬。但后者显然不会写日记,不会发表,甚至无法用汉语同我们交谈,因而他们的幸福与痛苦,都只是他们的隐私,都伴随天 葬台上纷飞的肉沫而告诉了鹰隼。余纯顺的表情是专门给以上海小男人为代表的都市侏儒们准备的,高原使他有了炫耀高度的资本,但他不能以青藏高原为参照系,无边的高原会嘲笑每一个冒失的征服者,使那些自命不凡的身影显得可怜和渺小。关于这个问题,余秋雨先生显然与我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写: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2)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1'
这段类似于“文革”庆功信的文字,颇有点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将整个高原作为英雄的布景和陪衬,这样的“三突出”原则显然不适用于西藏,甚至,不符合余纯顺的本意。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余纯顺从未有过绑架“壮士”这一称号,或者将自己的旅行与寻求真理一类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的企图。西藏并不需要观赏者,更不需要征服者,即使从不怠慢远道而来的人,但他们显然无足轻重。所有旅人都只是过客而不可能成为永恒,他们不是英雄而最多只能成为乞丐,他不是征服者或者施予者而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在西藏,乞丐这一称谓与轻视无关,许多藏民都是通过沿途行乞去朝拜的,因而每次在公路边上遇到行乞者,我都会投以尊敬的目光。
我不知书本上那些颇为吸引眼球的旅行是否真的构成探险,没有任何人能为此提供证据,然而这些文字听上去却像红头文件一样确凿无疑。它们仿佛浓烈的青稞酒一样迷惑我们。在这份由想象提供的欢乐里,西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对于西藏的冲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这些信息的蛊惑,它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我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需要治疗,我敢爱敢恨,敢写文章骂领导,从来不舍得亏待自己;说复杂,是因为那种冲动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我至今不能对它作出理性的分析——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自己祖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如此向往?是因其自然、宗教和文化奇迹在四千米高度上的巧合,还是企图背叛四平八稳的生活而投靠眩晕、梦游般的流浪?果真如此,那么,被切?格瓦拉和马尔克斯联袂渲染过的美洲大陆,那些被丛林覆盖的神秘金字塔,不是更加深邃和鬼魅?西藏向每个人提出问题,但没有答案,答案藏在每个人的腿里,并且关乎他们生命中最敏感的部位。
三
没有任何征兆,西藏在一个沉闷的傍晚突然出现。那天,北京电视台的导演卢小南给我打电话,尔后我们就相约在一尊毛主席塑像下见面,同来的还有主持人金毅。短暂的交谈之后,我就成了一部电视片的艺术顾问,并因此获得了随摄制组进藏的机会。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突然到来,剥夺了我做出一个苍凉而绝决的手势的可能。西藏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如我文前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这将使我的文字大为逊色,因为我的西藏之行,缺少了必要的悲壮成分。
有一点或许可以事后炫耀,那就是我向整个摄制组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我的童年时代有整整一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白雪皑皑的高原,与无菌的病房颇有几分相像,会本能地诱发我对于疾病的记忆。但为了避免与西藏失之交臂,我守口如瓶,到最后都没向组织坦白交代。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暴露出自己的任性、自私和不预全大局。
高原的酷寒缺氧和我被病变撕扯得奇形怪状的呼吸系统,会合谋在途中向我发动突然袭击吗?无法呼吸的记忆是那样深刻,肺部缺氧的痛苦要远胜于胃部缺食,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折磨的我或许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发言权。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通过一次被努力拉长的呼吸来为肺部争取一点氧气的艰辛,那点吝啬的空气如同爬过一片粗糙的山石一样,艰难地穿过我的喉咙,到达目的地时已所剩无几——缺氧于是成为我青春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而黑紫的嘴唇和凸出的双眼则成为我的标准肖像。疾病甚至改变了我睡眠的姿势,我只能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度过整个夜晚,每一分钟都像用冷水深化冰块一样缓慢和艰难。据此我曾被宣布与西藏绝无缘分。但那一天我却把这一切忘记——也许是有意回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剥夺了疾病出来表态的资格。我用了一个星期进行准备,包括添置必要的设备,诸如防水鞋、手电筒、水壶和刀,并且通过北京台的制片人吴群和他的女朋友李小萌打探珠峰的情况。我把沿途携带的所有家当摊在地上,并不止一次地端详地图上那片红铜色的土地,这时我才发现,西藏就在眼前了。
旅途令人狼狈不堪。疲惫删去了所有虚张声势的表演,那些浮肿的豪情和虚假的浪漫,剩下的只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诸如如何跨过一座坍塌的桥梁,如何应对空虚的胃肠,如何尽早结束一天的行程,等等。而奇迹,就混迹于这些庸俗问题之中,悄悄地到来。翻越唐古拉山口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也就是说,漫天的飞雪将我们全部变成瞎子,它的险恶在于涂抹了道路与悬崖的界限,把危险送到我们身边同时又将它遮盖起来。但我们不能停车,那样会导致一连串的追尾,只能硬着头皮在湿滑的山腰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显然这是一个因为赌注过大而显得并不好玩的游戏,每个参与者脸上都布满负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雪的恐怖,地道的“白色恐怖”,仿佛预见了上帝盖在死者身上的雪白布单。我不知道从上帝的视角除了看到山脉的瞬间变化外是否可以看到人们的表情,而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降临的阳光是出于恻隐还是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了他的考试。我相信飞旋的风雪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可以像雨伞上旋出的水珠一样飞旋出去,我甚至已经听到了在游乐场可以经常听到的充满快感的惊叫。但上天不开无限度的开玩笑,他分寸得当,刚好在生死的临界点上终止了游戏。但在那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任何所谓超越极限的英雄感而只有一点可怜的求生本能,我知道,在西藏,任何一点狂妄都可能受到制裁。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3)
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对司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离奇的故障,平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尝试过各种救援办法,但是崎岖颠簸的山路对我们想出的所有办法都提出否决,最后一个办法只能是把车抛在绒布寺边上,等我们开车到拉萨,购买一个新水箱后,再返回原地,更换水箱。这样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个星期。
将风和日丽这个词语用于修饰唐古拉山口,令我多少觉得有点离奇,我甚至感到一点受宠若惊,我相信并非所有人在刚刚进入西藏边界的时候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已对这些山神的性格多变习以为常。此刻的海拔表显示的高度已超过了五千米,我的呼吸系统比汽车的机械系统要正常得多——越野车的发动机那时正因缺乏氧力燃烧不充分而显然棉软无力,它像服用了鸦片一样一厥不振,而我却格外清醒。我等待着身体内部的那只魔手突然掐住我的脖颈但它始终按兵不动。
我警惕着埋伏在草丛中的蛇,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突然昂起头颅。如同一部惊险片的最后,凶杀并没有发生,放松之余我感到略微的失望。它不仅使我携带的繁琐的药物成为累赘,而且使这趟极限之旅(至少对我个人如此)仿佛一次平常的外出,以致于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的这趟旅程更像是一个谎言。
事实证明,西藏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近人情,尽管道路遥远而艰辛,我们不必把这里当作刀山火海,也无须把自己的旅程想象为某种壮举。天堂或者鬼蜮,皆是人为的想象或者杜撰。这里与我们的家园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出区别,那就是那里的常住居民还包括神明,它们占据着一定的人口份额。但是神明偏好最朴素的愿望,对豪言壮语心存反感。明察秋毫的神明早就看穿旅行者的阴谋——他们一面在记录本上写下悲壮的语录,一面劝说天真无邪的藏族少女在清沏的圣湖边脱去衣服……
四
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达定日以后,我们汽车的时速就再也没超过过十公里,再也没看见过河流和植物,只有灰色的石头,如同被天国废弃的单词,把没有止境的山坡堆砌成冗长乏味的史诗,令人无法回避。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词语的顿挫逐渐变成脚下的起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