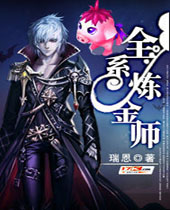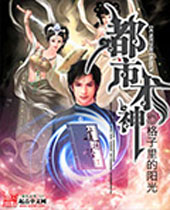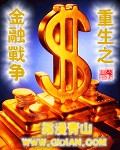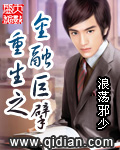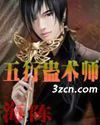金融炼金术-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偿债意愿。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偿债意愿就必须采取另一种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计算方法。最关键的变量不是还本付息而是净资金转移(资本流入),这也就是还本付息同大量吸收新贷款(以维持债务)之间的区别。只要债务国能够自由地贷款,他们的偿债意愿就是无可怀疑的,因为他们总可以借到偿还利息的钱。一旦信贷流入的渠道被截断,偿还意愿就成了关键的问题。然而在国际贷款极其活跃的背景下,银行家们不愿意正视这一问题。花旗银行的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甚至断言:“主权国家不存在破产的问题。”
①
我们已经看到了,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债务比率始终是令人满意的,银行也非常乐意贷款。而当债务比率转入恶化时,银行家们开始感到担心,其贷款的意愿也受到了打击,于是突然之间陷入了1982年的危机。这一危机揭示了净资金转移同偿债意愿之间的反身性关联,从而使自愿贷款就此绝迹。此后发生的一切将是下一章的讨论题目,在这里我们所分析的是1982年以前的体制。
商业银行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保持国际贷款业务如此迅猛的增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后几年间,围绕着这一问题定将展开热烈的讨论。部分的答案在于,银行的确没有意识到它们要为这一体系的健全性负责。银行业是竞争极为激烈的行业,此外它们还要分心触犯避免各种管制条例。防止经济过热是中央银行的事。商业银行在保护伞之下运营,他们所追求的,是在现行规章制度的框架之中求取利润的最大值,他们不可能拿出过多的精力来分析自己的行为对整个系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个放弃有利可图交易的银行几乎可以肯定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另一方面,即令这个银行拒绝了,其他银行也还是会趋之若鹜以图取而代之,占领市场。这样一来,就算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在国际贷款勃兴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也还是别无选择:要么随波逐流,要么退出竞争。
这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当一种趋势发展起来的时候,参与者们的处境往往不允许他们采取抵制的行为,即令他们知道这样下去将会酿成灾难。这是所有繁荣/萧条序列过程的共同点。一致拒绝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例如,根据分析结论,我明明知道抵押信托公司(Mortgage Trusts)的前景不大妙,然而我的建议却是立即买入,因为在暴跌之前必将会有剧烈的上升。果然,有一批投资者欣然跟进。当然,即使他们不这样做,繁荣/萧条的序列过程仍会发生,尽管要慢得多。
市场参与者的最高境界在于适可而止。然而有时的确力不从心。例如,在浮动汇率体制下,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所面临的就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他们不可能回避币种的选择,除非购入期权。仅就国际贷款活动的情况而言,在繁荣阶段的末期,花旗银行也曾审慎地减少了它在市场中的份额,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剧情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不能挽救它免受其害。尤其是在最后的阶段,几乎所有的银行都知道债务国的状况正在迅速地恶化,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它们早已是欲罢不能了。
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督。只有某种形式的干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令或者来自中央银行的和缓的暗示,才有可能阻止繁荣/萧条序列过程的失控。
中央银行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系列的危机继以机构改革的过程,然而它们却至今未能记取国际债务危机的教训,这真是一桩奇怪的事情。不受控制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其影响力也比以往要大得多。他们之所以敢于为所欲为,无非是看准了银行管制当局的无能,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没有看错。参与者们无法阻止国际贷款活动的失控,然而货币当局本来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呢?
①
纽约时报,1985 年4 月21 日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 1985)。
这个问题的答案始终不很清楚。中央银行对欧洲美元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显然是了然于心的,尽管他们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最后贷款者的责任,并且早在1975年就已经划定了各自的责任范围,然而他们却坚持认为没有必要规范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停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还必须对历史作一番更为透彻的研究。我在这里贸然提出两种尝试性的假说。
第一种假说指出,商业银行所承受的压力同样也影响到了作为保护人的中央银行。如果他们采取了限制措施,商业银行就会在竞争中败北。只有各国中央银行的协调行动才有能力将发展中的欧洲美元市场置于控制之下。这就需要机构上的改革来加以配合,可是货币当局并未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通常总要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变得迫切起来。
由此又产生出第二种假说。我认为,中央银行在其行动上受到一套错误观念体系的支配。当时,货币主义在中央银行里占了上风。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应过多引起的,与信贷规模无关。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管制的对象就应该是货币供应而不是信贷的增长。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对欧洲美元市场进行干预。只要中央银行能够管好自己的货币供应,市场也就能管好自己的活动不出乱子。
问题是神秘而复杂的,我不能宣称自己已经探到了其中的底蕴。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一边列着货币项,另一边则是信贷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告诫我们,只有货币这边才有考虑价值,因为信贷是取决于货币的①反身性理论的引入昭示了他的错误。我确信,此二者必然以反身性的方式互相影响,而控制货币的梦想最终是行不通的。由于缺乏足够的专门知识,我无法进行直接的反驳,但我可以指出经验证据,说明控制货币供应的实际效果一再地令管理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70年代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中,欧洲美元市场的迅猛增长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搞清。因此,同样也很难估计国际贷款的收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今天笼罩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通货紧缩的阴影负责。我坚信,无论是国际贷款的紧缩还是扩张,它们都对世界经济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是我的观点还远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这一问题也仍然悬而未决。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国际贷款的规模就应该成为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重要参量。任其泛滥的货币当局在70年代后期铸成了大错,1982年的危机既是管理方针的破产,也是自由市场体制的破产。
我们将在稍后一些再回到这一议题,管制市场与自由市场的不完善性是本书的主题之一。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贷款的新体制,它是在1982年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1867—1960 美国货币史》,《美国货币统计》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and Moneto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第六章贷款的集团体制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管理当局进行了积极而富于想像力的干预,国际债务危机势必令银行体系陷入崩溃,从而给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上一次可能与此类似的崩溃爆发于30 年代。鉴于以往的教训,国际间成立了一个授权机构以防止历史的重演。因此,听任形势恶化而熟视无睹是难以想像。别具一格的干预方式将世界经济引入了史无前例的新局面。
这个机构赋予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的权力与义务。然而债务问题实在过于复杂,仅仅向银行提供周转资金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所涉及的款项大大超出了银行的自有资本,如果坐视债务国破产而无动于衷,整个银行系统早已资不抵债,无法维持了。因此,各中央银行突破了自己的传统角色,联手出面担保债务国渡过难关。
英国人是这种新模式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 年,英格兰银行(England Bank )就曾决定出面担保那些并非它责任范围之内的所谓边缘银行(fringe banks ),以免清算银行的清偿能力受到怀疑,因为边缘银行曾从后者那里获取了大量借款。不过,在国际范围内采取这种担保负债者的做法,还是始于1982 年的债务危机。
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的权威来执行这一行动策略,只有有关债权国政府才有可能做出权宜的安排,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一揽子的挽救计划出台了,它将各个有关的国家召集到了一起。照例,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承诺份额,国际货币机构投放了新的现金份额,债务国家则接受了为提高其国际收支平衡能力而设计的紧缩方案。在绝大多数场合中,商业银行还不得不提供额外的现金,以便债务国可以维持足够的周转能力来支付利息。挽救一揽子计划是国际合作领域中的巨大成功。参加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许多国家的政府与中央银行,以及为数众多的商业银行。例如,在处理墨西哥债务问题时,牵涉到的商业银行多达500 家。我认为,将这些参加者冠以“集团”的称号是合适的。
整个过程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几次反复。有关具体进程的描述无疑将会是引人入胜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却不得不将讨论的范围局限于最终结果的考察。
危机之后所确立的体制,在许多方面同1982 年以前的体制正好相反。后者是竞争型的:银行为追逐利润而自愿提供贷款,并且相互间竞争激烈;前者却是合作型的:银行被迫进行贷款,以求保存它们已经投入的资产,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同其他银行密切合作。旧体制在积极的方向上体现出反身性:银行的贷款意愿与贷款能力同时加强了债务国的偿还意愿与偿还能力,反之也是如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反身性表现为反方向的作用:银行无力也不愿贷款的倾向同债务国无力也不愿偿还的倾向之间相互碰撞,将事态逐渐扩大。如果参与者们不能进行积极的合作以防止崩溃的爆发,那么这一体制必然就此寿终正寝。贷款方所采取的措施是增加新的信贷,以使债务国有能力归还既存债务;而借款方则要接受一种严厉的紧缩方案,以使新增贷款的数目减少到最小。具体的界限将由贷款双方在微妙的谈判过程中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并组织了这些谈判,尽管债务国大都不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议的监督中发挥长期的作用。
这个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因为它要求贷款双方克服各自的狭隘利益以维护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债务人一方,牺牲表现为消极的资金转移(资本外流),而在银行一方,则是追加新贷款。这种牺牲是不对称的,因为债务人要为新增加的贷款支付利息,而贷款方则享受拥有这些利息的权利。请注意,贷款的集团体制乃是基于以下的原则,即保存债务的完整性——正是这一原则将集团聚合起来。不幸的是,它未能解决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债务国必须做出让步才有可能偿还债务,而每一次的让步都加重了未来的偿债负担。由于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银行开始提取呆账准备金,然而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债务国了,除非破坏那个原则。
贷款集团体制的确立没有经过认真的规划,甚至没有正式宣布过,它从一开始就是过渡性的,并且注定将被某种另外的形式所替代。关于它本身,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它的最终结局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无法获得满意解答的问题。一方面,反身性过程不存在某种预定的结局:结局决定于过程。另一方面,预言本身也会影响到结局。在这个例子里,集团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完成自身使命的期望,任何有关这种期望的陈述立刻就会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令讨论保持客观性。然而,问题是迫切的。我所采用的方法能否有助于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答案?这样一种形式的答案又是否会有助于发展一种反身性的理论呢?
在此期间我撰写了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3 年7 月和1984 年3 月——我试图应用反身性的理论来分析国际债务问题,但并不公开声明。下面就是我当时的说明(做了微小的改动)①:
对重债务国而言,自愿贷款体系的崩溃迫使他们进行激烈的经济再调整,这一调整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进口锐减;第二阶段,出口增长。在头两个阶段中,国内经济进入衰退;第三阶段,国内经济复苏,进出口回升;第四阶段,国内生产总值与出口的增长超过了偿本付息的水平,从而结束了调整。
第一阶段是自发进行的。当信贷资金的来源被切断后,贸易赤字因进口的削减而自动消除。生活水平下降,生产过程被迫中断,整个国家陷入萧条。“集团”所需提供的信贷数额取决于债务国形成贸易盈余以抵偿债务的能力与速度。
在第二阶段,真正的调整开始了。货币贬值,恢复到真实水平,因国内需求萎缩而闲置的生产资源重新转向出口渠道。贸易平衡能力得到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债务偿付能力的增加。
到了这一步之后,偿债意愿与贷款意愿开始成为关键性的因素。债务国必须增加其出口以支持国内经济的复苏,这就意味着消极资金转移(资本外流)的规模降低了。只要能够克服这一障碍,前面就是第三阶段了。国内经济的复苏令消极资金转移(资本外流)的过程更为顺畅。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该国出口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