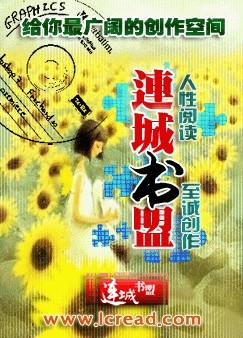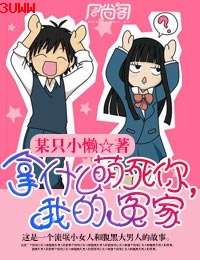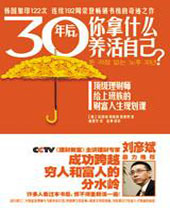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税收政策在我国属于行政手段还是财政手段,甚至是市场手段,各方意见不一。总体而言,如果设立新税种或者改变税率经过了人大审核、公开听证等一系列程序,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在合法性支撑下的公开而透明的财政政策。由于我国许多税收政策被让渡给财政部,缺乏应有的制约,导致行政封闭色彩浓厚。从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证监会提出上调印花税动议在半个月之前,而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行政程序,主要是财政部讨论形成意见报上级批准。在税收决策过程中有封闭而自足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
从坚持股市市场化调控到最后向行政手段缴械,说明A股市场仍未脱政策市窠臼,一言兴(衰)市与一文兴(衰)市的时代固然已经过去,但一政兴(衰)市的可能性仍继续存在。甚至有学者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保密性论证政策印花税保密之事,却没有看到美联储有制度性的固定沟通平台保持信息畅通,这是否能够反证缺乏制度性沟通平台之非?
在全球金融危机大发作之后,资本市场摆脱了挤泡的威胁,地位空前提高。汇金公司表示要为维持稳定出力增持金融机构股票,央企上市公司表示要增持回购,2008年年末出台的总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资本市场注入取之不尽的概念。而地方政府高达十余万亿元人民币的发烧级投资计划,更是让A股市场患上自大病,有评论将A股市场脱离全球资本市场价格走势称为,A股市场的腰板挺起来了,A股重获定价权,足以脱离愁云惨雾的全球资本市场。
所有的乐观者都提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都提到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财政刺激计划确实能够利好某些企业,尤其是基建类的央企,以及与基建相关的企业。从2009年1月1日开始的企业增值税转型,能够为企业带来切实的业绩。
股市自2008年11月之后的反弹,是政府的经济拯救方案在资本市场的尽情发酵,是政策市的典型表现。2009年一季度上证综指连涨3个月,季度涨幅为,深证成指涨幅更是达到;同期,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欧洲三大股指的跌幅也全部超过11%;亚太地区其他股市除韩国上涨外,日本、澳大利亚等股市也均下跌,香港恒指下跌近7%。作为最直接反映市场活跃度的重要指标,一季度A股市场成交量明显提升。一季度沪深两市共成交了94 388亿元,较2008年四季度增加了8成多,其中,2月份与3月份较1月份明显放大了倍左右。全部A股日均换手率在2008年长期处于1%~2%之间,2008年四季度是,而2009年一季度为,且在股指两次上攻2 400点时突破4%这一重要水平线,这说明,股市处于赤裸裸的投机之中,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此时的投机是被允许的,而2007年的投机则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的。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双重考验,一是能否以市场化的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危机,二是人民币能否成为自由兑换货币,这两重关卡对于我国经济是重大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万亿元财政政策能否收效?鉴往而知来,与1997年、1998年的经济紧缩周期相比,我国在1998年至199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自 1998年至2003年期间,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 100亿元,由此拉动的投资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短期效应在积极财政政策推出半年后显现,但中国经济仍然经历了4年的通缩期,直到2003年的房地产市场化,其实也就是高价化,2003年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才最终带动了国内的消费,解决了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
经历了2003年以后GDP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期,中国经济有了一定的抵抗力,不得不指出的是,与1997年、1998年时相比,经历数年经济高速增长,家庭消费支出占比在减少,而贫富差距在扩大。1997年家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998年为,而2007年为,民间消费在萎缩,中国过剩的产能只有靠外部投资与国际市场来消化。其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对农村居民平均收入之比从1997年的上升到2007年的。可见,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比1998年时更加严重,民间消费在削弱而不是在增强。
资本市场对政策到了痴迷的境界,形成群体性的政策依赖症,学界与分析师以政策赞歌为前哨,大队投资者尾随在后。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上涨火车头、引领全球经济走出紧缩泥潭等言论触目皆是,以为中国资本市场可以不顾所有利空特立独行,忘了我国资源配置低效这一长期隐患,忘了大小非这一制度顽疾。倒是一些政府高官不好意思,时时提醒市场,金融危机没有见底。这一清醒的论述写进了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周告天下。
建立市场机制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美国代替英国花了一个世纪,在中国资本市场被关闭半个世纪后,以为旦夕之间就能乘虚而入引领全球,实在是健忘、自大得可以。
倒逼出来的股改
股改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全流通的一步,也是为市场化扫清障碍的重要一步。这正是中国经济的吊诡之处,一方面社会迷信行政权力的威力,另一方面行政权力通过推进市场化,树立自己的权威。百余年的现代化之路,在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处,还是刻上了市场化的印记。即便是为行政正名,理由也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社会公平。
逼不得已出台股改
不到万不得已,股改不会出台。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把高价减持和首发、增发“捆绑”起来,名正言顺地以减持国有股为社保筹次的名义掠夺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两天后,上证指数见顶2 245点,随即以急跌方式,展开了199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下调,最低点达998点。这一高点直到2006年12月14日,才被突破。
徒劳地与市场对抗了一年后,行政权力被迫让步,管理层宣布暂停在新股首发和增发中执行国有股减持政策,这一暂停等于变相终止。2002年6月2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发布了国务院决定: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财政部和证监会发言人进一步指出,停止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后,为了增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力,除继续采取国家财政增加拨款等方式外,有关部门将进一步研究,把部分国有股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部分划拨的国有股不在证券市场上减持套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在需要时,通过分红、向战略投资者协议转让等形式来充实社保资金。在国有股以市场价减持终止后,所有市场人士心里明白,通过股改实现全流通的序幕已经开启,政府将痛下决心革除弊端。
截至2004年底,上市公司总股本7 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 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4%,国有股份在非流通股份中占74%。通过配股、送股等滋生的股份,仍然根据其原始股份是否可流通划分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
2005年5月,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发表股改造势宣言书,痛陈股权分置六大弊端:
―扭曲证券市场定价机制。股权分置格局下,股票定价除包含公司基本面因素外,还包括2/3股份暂不上市流通的预期。2/3股份不能上市流通,客观上导致单一上市公司流通股本规模相对较小,股市投机性强,股价波动较大和定价机制扭曲。
―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利益基础。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资产净值的增减,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客观上形成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分置”。
―不利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股权不能实现市场化的动态估值,形不成对企业强化内部管理和增强资产增值能力的激励机制。
―不利于上市公司的购并重组。以国有股份为主的非流通股转让市场是一个参与者有限的协议定价市场,交易机制不透明,价格发现不充分,严重影响了国有资产的顺畅流转和估值水平。
―制约着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产品创新。
―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
这六大弊端表现在市场上,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彻底丧失投融资功能,失去信用,政府必须找到改革抓手,来激活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可获得一箭数雕的效果: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让利于民重拾投资者信用,可为未来的大股东兑现获得法理依据,更可让国有股部分可进可退,成为首善之选。
2005年4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随后,监管层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抑制投机,促进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价值取向接轨的新的市场交易办法。
股改差点夭折(1)
既得利益阶层组成反对同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股改最初阶段,国资委与外资携手,站到了同一战壕里。这显示不论内外,无论什么样的市场主体,既得利益阶层绝不肯放弃已经到手的红利。在股改过程中,破天荒地出现强势阶层喊冤的现象,强势与弱势阶层瞬间发生逆转―传统的弱势群体被攻击为违法的不当得利者,而传统的强势阶层却在管理层的压力下,摇身一变成为弱势阶层。虽然以股市经验看,小股东们不可能具备成为不当得益者的能力,先不用说股权的集中度与流通股股东的投票成本,单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审批权,就牢牢攥在国资委手中。
国资委只字不提在资本市场获得的溢价,不提中小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所支付的改革成本,中央国资委慎重缄默,由江苏、四川等地方国资委官员提出,在股改中向中小投资者支付对价缺乏法律依据,是国有资产流失。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推进,国资委必将强力介入股改过程,改变股改的力量对比,可能让股改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比赛,甚至最后不了了之。
国有资产流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魔咒,也成为资本市场的魔咒。国资流失就像密布于中国市场的地雷,从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管理层MBO,到股改试点的对价支付,全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国资流失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短期内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量存在未受约束的国资流失现象,另一方面,又成为利益群体之间互相指责的一根大棒。这根大棒,在股改初期被用来指向对价支付方式。
国资委对股改有三不满:第一,股改初期支付对价理论基础不足,造成“粉丝卖了鱼翅钱,鱼翅也卖了鱼翅钱”;第二,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来说,股改的结果不是股东权益减少(净资产损失),就是责任加大;第三,对价方案偏重于送股,形式比较单一。归结为一条,就是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权益被剥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一向说话不顾常识的专家们再次粉墨登场,从法律、市场各个角度论证现行对价制度的种种缺陷。国资委2005年9月9日颁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鼓励“对价创新”,并被明确界定为“根据上市公司和国有股股东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股权分置改革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将资产重组、解决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等与股权分置改革组合运作,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换句话说,并不鼓励对价支付成为股改的主流形式。这一指导思想体现在第二批试点企业的股改方案中。
防止国资流失关键要看两点:第一,现行的国有企业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有,即使不支付对价,国资照样会流失,这在股改之前的各种案例中早已证明;第二,国资流失到了谁的口袋,找到最终的获益者才能堵住漏洞。按照市场规律,能够从法律法规的夹缝中获利的只能是有能力调动资源的人。迄今为止走上被告席的国有企业蠹虫,有几个是平头百姓?
所谓大股东权益减少、对价方案单一,无非是为大股东要支付真金白银鸣不平。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说,大股东原来就占有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利益。对价不过是赎回市场诚信的一种方式。鸣不平当然可以,但不能将对价支付等同于国资流失,而后推断出获得对价的流通股股东不当得利,这显然有失公允。
股改差点夭折(2)
市场形成对价共识并不容易,这是市场利益各方协商的结果。以保护国有资产为名,非要打破共识,并不是对国有资产负责的态度,也不利于全面股改。国资委当然能想到,央企作为中国经济的长子,一贯在父爱主义下受尽宠爱,股改不过是“退一步进两步”之举,一味反对股改实属不智。因此,在博弈获得平均水准的10送3对价之后,国资委的反对声软化。
相比国资委的欲遮还羞、必须服从大局的政治觉悟,外资控股股东对于股改的反对要激烈、坦白得多。
2005年7月以后,单伟建先生与管维立、高志凯差不多同时抛出了反对股改的宏论:7月和8月单伟建借助宝钢独立董事的身份,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质疑宝钢支付对价,反对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和送股;管维立接踵发表《中国股市的荒唐一幕―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一文,这篇长文被形容为“全盘否定股权分置改革的三万言书”;高志凯先生于2005年8月中旬在《财经》杂志发表《“对价”之名剥夺财产》一文,认为现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对非流通股股东产权的剥夺,违反保护产权的法律条文。
管维立,前国资局司长、后任深发展监事会监事,保护国资的旗帜拿起来再顺手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