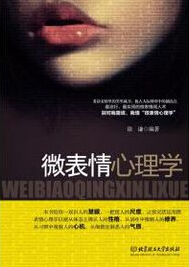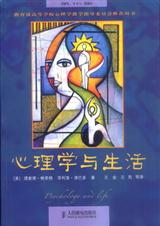性伦理学-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欲本身不是贞节。我们可以把禁欲和纵欲看成两个动荡而走极端的状态,而贞节即
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霭理士那本著名的《性心理学》中深刻地写道:“贞节可以有
一个界说,就是,在性领域里的自我制裁。换言之,贞节的人有时候可以绝欲,但
有时候也可以有适度的施展他的情欲,紧要之点,是要在身心两方面,对于性冲动
有一个熟虑的与和谐的运用,而把这种运用认做生活的一大原则。我们有此了解,
就可知贞节不是一个消极的状态,而是一个积极的德操。”'注'这个德操是万不可
少的,为了培植性功能的活力,我们少不得它向了维护做人的庄严,我们也不能没
有它。此外,对于可以增进幸福的恋爱的艺术,它也正是一个很大的要素。但是,
如果似宗教信条和封建伦理那样,把贞节看得过于绝对,把贞节变相而成强制的绝
欲以后,它就成为不自然的了,也就不成其为二种德操,并且也不再有甚么实际的
效用。贞节的根本性质也就消灭于无形。到此境地,不明原委的人便转以贞节为
“不自然的”或违反自然的行为,从而加以贬斥,许多人的性的活动甚至走上另一
极端,不但把纵欲和乱交看作一个理想,并且真把这种理想见诸行事;他们不了解
这样一个极端是一样的不自然,一样的要不得。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引述霭理士的见解时,使用的不再是“贞操”
而改成“贞节”。这种改动有何根据呢?译者潘光旦于1941年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贞节一词,原文为chastity。今酌译为贞节;贞是对人而言,节是对一己性欲而言。
贞有恒久之义,即所称“恒其德贞”,亦无从一而终之义;所谓从一之一,可以专
指配偶的另一方,也可以共指配偶与此配偶所共同生、养、教的子女。寡妇鳏夫,
或追怀旧时情爱,或于夫妇情爱之外,更顾虑到子女的少所依恃,因而不再婚嫁的,
根据上文的说法,都可以叫贞。前代所称的贞女,其所根据既完全为外铄的礼教,
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情爱,是一种由外强制的绝欲状态,而不是自我裁决的德操,我
们依据上文的了解,也就不敢苟同了。明代归有光以女子未嫁守贞为非礼,大抵也
用此立场。译名中的节字是对一己而言的。就本义说,也是就应有意义说,是不应
限于寡妇鳏夫一类的人的,甚至于不应限于已婚而有寻常性生活的人,凡属有性冲
动而不能不受刺激不作反应的人,自未婚的青年以至性能已趋衰弱的老年,都应知
所裁节。裁节是健全生活的第一大原则,初不仅性生活的一方面为然。总之,我们
在这里所了解的贞和节是和前人所了解的很有不同的。
我们以为,霭理士关于贞节的思想以及潘光旦所做的解说,都是相当深刻的。
这两位学者所界说的“贞节”,应该成为婚前关系中性伦理的重要内容。
四、同居
1988年春,《婚姻与家庭》杂志收到一篇题为《论同居》来稿。这显然触及了
一个敏感问题。为慎重起见,编辑部把该稿的复印件分发给有关编委以征求意见。
接着,编辑部在全国妇联召开了“关于同居问题的讨论会”。会议邀请的人不多,
但发言的热烈却超出预料。有鉴于此,1988年第9期的《婚姻与家庭》杂志发表了一
组谈同居的文章。编者按称:“同居,自然是指无配偶(未婚、丧偶、离异)的成
年男女自愿结合过夫妻生活,而未到民政部门进行婚姻登记。同居,作为一种婚姻
家庭形式,发达国家已屡见不鲜;在我国也不少见。我们发表这组文章,绝非有意
提倡什么,而是旨在引起各界热心人士的关注,对同居的基础、心态、利弊、发展
趋势作较深入的探讨和预测。”半年后,在1989年4月出版的《婚姻与家庭》“婚姻
与性问题专号”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同居的对话》,以期继续推动关于同居问
题的研究。
我们作为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主办的《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兼职编辑,认为
应当把同居问题列入我国性伦理学研究的议事日程。
不妨先看看国外社会学和伦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来自美国研究者的许多报
告指出,婚前同居代表了当今西方社会婚前关系的最新动向:以非形式化和非榨取
性为主要特征。这些研究者认为学生们现在受到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冲击,开始了对
人性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学生们在寻找婚姻的候选人,还不如说他们
渴望得到的是有发展持久关系可能的异性朋友。”专家们也意识到这种同居关系的
预测性意义,他们甚至推断:非婚同居将很快变成美国占统治地位文化的一部分,
它也许决定了大多数人在特定时期的私生活风格跨文化的。研究表明,婚前同居现
象并不局限于美国,这种现象在非西方国家,例如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正在发生变化
的国家也有增多的趋势。当然,这也与它们的文化伦理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高速率的社会变迁,更替了人们的行动价值,也逐渐填平了两性之间存在的传
统沟壑,这些都为青年异性之间广泛的社会交往扫除了障碍。于是,非婚同居现象
象野火一样在美国文化这种供其所宜的气候中迅速蔓延开来。据统计,近30年来,
非婚同居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种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对于
非婚同居这个事实的确认,人们似乎已没有什么歧议,但在其原因的解释方面可谓
众说纷纭。在这众多的观点中,婚姻问题专家马凯琳的见解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她认为,笼统地谈论同居关系是不精确的,美国青年人的非婚同居关系至少可以分
五种:(1)暂时方便型:临时同宿共居,各得其利。(2)虚饰型:并无约束,仅
以同居作为一种自娱性活动。(3)试婚型:在缔结姻缘前试探性同居。(4)暂定
择偶型:两厢情愿,暂定结合,见机行事。(5)持久型:共同生活年长日久,然无
法定手续。马凯琳基于她的研究指出:非婚同居的男女具有志愿性的结合基础,所
以在相互满足的程度上似与正式配偶没有很大差别,其生活风格也显得新颖别致。
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种关系的脆弱性(相对于正式婚关系来说),但是,即使关系破
裂通常也不会求助诉讼程序的调停或仲裁。在引证了其他研究者的有关报告后,马
凯琳又指出:即使是最摩登的同居方式,也没有完全会却最基本的性角色关系中的
传统价值,即性关系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自动地制约了同后双方的性行为。
以上是西方社会同居的分类模式,当代中国社会的同居现象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当代中国同居关系的普遍表现是事实婚模式。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事实婚姻作为一种广泛地存在于我
国社会生活中的婚姻形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持慎重从事的态度。在我
国目前的条件下,一概肯定或否认,都是不妥当的。
从历史上来看,长期盛行仪式婚制度。必须经过一系列婚嫁之礼仪程序,婚姻
关系才能得到社会承认。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革命根据地首次实行结
婚登记制度,但根据当时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法律上对法律登记婚和事实婚这两
种结婚形式都承认其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1日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第6条规定:“结婚应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
民政府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1953年7月29日东法行字第3806号批复指出:
“我们认为婚姻法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已建立地区;结婚而不去登记或在这次贯
彻婚姻法运动后,仍有不经登记而结婚都是不应该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婚姻法宣
传还不够广与深,因此对事实上已结婚,而仅欠缺结婚登记手续者,除给予一定教
育外,仍应视为夫妻关系。”第二次(1979年)和第四次(1984年)全国民事审判
工作会议文件均规定结婚不登记是违法行为,除进行批评教育外,可分别不同情况
予以处理。
建国以来的审判实践,历来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对待事实婚问题,即对于符合婚
姻法规定的结婚要件的事实婚姻,在产生纠纷时?除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外,
一般可承认其有婚姻效力。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结婚事实要件的事实婚姻,则不承认
其法律效力。如果我们对事实婚完全否认,从形式上似乎体现了法律和道德的严肃
性,实质上却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因为在事实婚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如果许
可当事人不负责任地抛弃事实婚姻摆脱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就会使一些品质不端的
人任意遗弃配偶、子女,抛弃家庭,尤其使妇女、儿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也会助
长一些农村妇女流浪在外与他人同居骗取钱财的不良现象;使一些人在“政府不解
决自己解决”的思想支配下,行凶闹事,矛盾激化,从而给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带
来破坏性影响。所以,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承认其法律效力和伦理价值,
是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性关系的需要。
当代中国同居关系的第二种表现是反传统模式。如果说置于事实婚同居关系下
的大多数是些法制观念淡漠,素质较低的人们;那么,以反传统面目表现的同居者,
则是些观点较新,素质较高的人们,其中不乏“思想改革者”。
反传统的同居模式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1923年在上海创刊的《妇女周报》第
9号上,一篇署名子荣的文章曾就结婚仪式发表了如下见解:“我以为这个仪式固然
不必规定,而且还是不必有的;即使不废止,也应彻底改过才行。”该文引述意大
利密该耳思所著《性的伦理》中的有关思想后指出:两性的接近应以渐,由最初的
漠然的性的牵引进行性择,加上智情的融合,发生恋爱,以肉体的结合为顶点,这
个过程当自然而然,不可稍有勉强;恋爱成熟而强令禁欲,恋爱未熟而强令结合,
都是有害,也都是不道德的。相爱的男女的性行为的开始只应以恋爱自然的发展为
准,不必一定在公布期日的某时刻;这就是说凡真实相爱而有互相厮守之诚意的男
女(普通婚约者亦在内),其同居的时日尽可自由开始,无指定之必要,至于婚礼
则当改为招待亲友的性质,在同居数月以至一年,或生了子女以后,均无不可,但
决不可在同居以前,因为这只是告诉亲友他们已经结合,并不是先求许可才去结合。
因此我对于普通的一切结婚仪式都很反对,觉得里边含有野蛮的遗习与卑狠的色彩。
平常总是要人死了才吊丧,小孩生了才贺喜,唯独婚事要在事前大吹大擂的闹,真
是荒谬极了。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陈望道撰文肯定了上述主张。这位《共产党宣言》的最早
译者还多次表述了类似的立场:“我以为男女真正以恋爱的结合,其开始共同生活
的日子,尽可自由不必通知任何人,也无通知的必要。倘必要行婚礼,也应改为一
种招待亲友的性质,过了几月,或一年,或意生了子女以后都可以。这时男的可以
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女子,女的也可以介绍许多自己的朋友给男子做朋友,大家互相
谈谈,倒也不是绝无意味的事;但决不能在同居之前举行。总之:男女的结合,不
重在仪式的如何严肃,应全以恋爱为基础。无恋爱的结婚,总是好淫,不管它是
‘百年偕老’,也不过是长期的好淫;真正的恋爱婚姻,无论形式如何简便,总之
是神圣的婚姻。所以我们不必管形式,只须问实质。”'注'
陈望道所持的同居立场,同恩格斯在生活中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4年前,一位
青年朋友曾来函讯问:“据说恩格斯与自思士长期保持着同居关系,真是这样吗?”
当时,我们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给这位远方的朋友写了复信。
1842年,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不久,认识了玛丽·白恩士。她那“野蔷薇”般
美丽和“黑亮勇敢的目光”给恩格斯以深刻印象。这个有阶级觉悟的女工,使恩格
斯增强了自己的这一决心:摒弃资产阶级的社交和宴会,全心全意同工人们交往并
专心致力于研究他们的状况。1843年,恩格斯与玛丽开始了最初的同居生活。从广
阔的社会背景分析,恩格斯与玛丽的共同生活就是对爱情生活的追求,对现实的反
抗。1845年4月初,恩格斯离开巴门,迁居布鲁塞尔。同年,玛丽·白恩士离开英国,
迁往布鲁塞尔和恩格斯住在一起。这对年轻人是在一种自由的、建基于互相尊敬和
独立自主的结合中同居生活。当时,在那些具有爱好自由的思想、不愿意从属资产
阶级道德法规的年轻人当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1850年,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
作为一个著名的曼彻斯特公司的职员和一个工厂主兼商人的名门望族的子弟,恩格
斯在公开场合下自然不得不注意社交礼仪,并且在好些方面要适应英国商界人士的
习惯。这一切,对于他这样一个非常厌恶资产阶级的伪善并且在以往岁月中一直过
着十分自由的生活的人,并不是一件易事。恩格斯在给自己的亲密朋友的信中以诙
谐的口吻来描绘自己的“双重生活”。恩格斯非常希望和玛丽经常共同生活,并且
事实上也是常在一起,但流行的资产阶级伦理观念和寄人篱下的地位都不允许自己
和她固定同住一所住宅。他必须另外有自己的单独住宅。但他真正的家是在戈顿,
海德路252号,也就是玛丽·白思士和她的妹妹莉希·白恩士居住的地方。
对恩格斯来说,玛丽是他所深情钟爱的人;既是忠实的生活伴侣,和她在一起
可以得到安宁和摆脱世俗的纷扰;又是热情的战友,和他并肩为共同的目标和共同
的志愿而奋斗。1863年1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