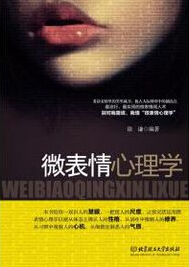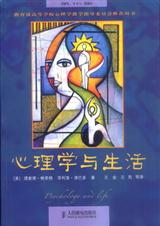性伦理学-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律干预的最起码依据就是配偶双方必须是异性、即婚姻的基本要素是男女两性。实
际生活中,人们也习惯把婚姻和异性相爱两个概念完全等同,以至于人们感到,探
讨所谓同性恋问题,简直是天方夜谭,毫无必要。然而,异性相婚的观念随着时代
的变化,也面临着现代意识的挑战。由于对婚姻与婚姻选择个人态度的变化,性爱
表达方式的改变,以及同性恋家庭的不断出现,加上现代人工生育技术的发展,试
管婴儿的产生,一些人不断对异性相婚这一传统观念提出质疑,要求修正。对此,
性伦理学应该进行考察和判断。
50年前,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翻译家潘光旦先生在对中国文献中的同性恋做
了详尽研究后推论说:质性恋的现象大约和人类的历史同样的悠久。一般的历史如
此,中国历史大概也不成一个例外。
《商书·伊训》曾说及“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
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风之一叫“乱风”,乱风包括回愆,其一
是“比顽童”。假如“顽童”所指的就是后世所称的“男风”,这便可视为是关于
同性恋的最早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同性恋首先被冠以“龙阳”的称号,其故事见《战国策·魏策》: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馀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
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
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里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
今以巨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王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
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寨装而趋大王,臣亦犹囗臣之前所得鱼也,
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日,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
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龙阳君姓名虽不传,但后人称同性恋为“龙阳
“,确源出于此。
此外,还称同性恋为“馀桃断袖”之癖。“馀桃”的典据见韩非子的《说难篇》: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
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日,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
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
人。及一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馀桃。故
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断袖”
的典据载《汉书·董贤传》。董贤年22,即为三公,哀帝兴会所至,甚至于要把汉
家天下禅让给他。《汉书,说他“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不久便
出则参乘,入同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
而起”,恩爱一至于此。
同性恋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的某个时候,某些地方,甚至发达。成一种风气,
如清代的福建、广东、以及首都所在地的北京,都有过这种风气。然而从总体上,
同性恋是为传统性伦理所坚决排斥的。从传统中国文献可以发现,同性恋的形成原
因被概括为四类。即环境劫诱说、意志堕落说、淫恶果报说、因缘轮回说。潘光旦
详论道:四个解释里,不用说,第一个是始终有它的地位的。第二个就有问题,除
非我们相信意志有时候可以绝对的自由。第三第四两说我们在今日已不能不放弃,
而代以遗传之说。还有应当注意的,就是四个解释都单单照顾到了被动的同性恋一
方,而与主动的同性恋者全不相干。这些都有待于近代科学的性伦理学来答复。
在西方的历史上,对同性恋的道德评价经历了大起大落。
在许多未开化与未开化的民族里,同性恋是一个很彰明较著的现象,有时候它
在风俗里很有地位。在古希腊人中间9同性恋的受人尊崇,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
步;他们认为它和理智的、审美的、甚至于道德的种种品性有联系,并且,更有不
少的人认为它比正常的异性恋还要来得尊贵。柏拉图的《恰尔米德斯》一书就描写
过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被一群崇拜者尾随着出现在公共场所。当这个小伙子走进来时,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去看他,一下子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当他在凳子上坐下时,
这些人你推我搡地争着抢占他身边的座位,竟把几个人挤倒在地。尽管成年男子中
聚集着可供同性恋者相互爱慕的对象,但是,理想的同性恋则被认为应该在成年男
子和青年男子之间进行。前者是“爱者”扮演着爱情中主动的角色(男性)。后者
是“被爱者”扮演的是被动角色(女性)。当然,“爱者”那种心醉迷迷的爱,并
不是男性同性恋者的发明。它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有关同性恋的描写,首先出现在希腊文学史上一个女性同性恋者的诗歌中。这
个人就是萨福。她的出生地来兹波斯岛,后来因此而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萨
福于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该岛上。她在那里办了一所专门教授贵族礼仪的私立学校,
教学生诗歌、音乐和舞蹈。她发疯似地一个接一个地爱上了她的学生,用巧妙而充
满向感的诗歌向她们表达爱情。她的诗歌为她在以后的希腊人心目中赢得了“第十
艺术女神”的美称。她的同性恋癖好并没有影响正常的婚姻生活。她有丈夫并生养
了一个女儿。
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的费罗用“同性恋”术语翻译了罪恶之地的故事。从此,
一个不精确的《圣经》故事便使同性恋变成对国家的严重危害。这个故事是讨厌希
腊习俗的犹太人描述的,接着基督徒也厌弃了“非本性罪孽”。在康斯坦丁诺普的
“新古罗马”时代,皇帝亚斯蒂尼将古罗马法和基督教的道德融为一体,并颇为成
功地在大部分领域付诸现实。他的观点是,亵渎和同性恋同样不虔诚。他命令首都
杰出的警察局长逮捕那受到警告而坚持上述违法行为和不虔诚的人,并对他们予以
严厉的惩罚,这样做,城市和国家才不会因上述罪孽而遭受损害。541年,亚斯蒂尼
的话几乎刚刚被传开,就在康斯坦丁诺普开始流行严重的瘟疫,这个城市中1/3的
居民在3年内都染上了这种瘟疫。这被视为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
另一方面,强烈否认基督教道德对于教会也是一种危险。教会十分清楚自己内
部也有同性恋者;僧侣生活开始时,教会法规开始经受偶然的神经颤抖。公元567年,
第二次检查会议上批准的、在公元529年创立的一个教派规定,一张床上永远不能睡
两个教士;几世纪后,对修女也有了同样的规定。再者,住宿的灯要通宵达旦。公
元693年,托莱多会议规定,如果一个男性犯了同其他男人进行的“非本性罪孽”,
而这人是主教,或教士、执事和职员时,他要被降级并被罚终生流放,使之遭天罚
而死去。协会对于罪犯的惩罚是鞭打100下,剃光头和驱逐出境。对于教会成员的惩
罚,国王加上了世俗的阉割惩罚。即使如此,基督教教规的要旨仍是,神父的异性
恋比同性恋的问题更严重。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教士独身的过分要求已引起世
人的惊恐,教士中同性恋的增加严重影响了俗人。11世纪,彼得·达米尼再次站出
来公开反对同性恋。13世纪的神学家汤姆阿维内思加强了传统上对同性恋的敬畏,
同性恋被定义为对上帝规定的自然秩序的歪曲,是贪欲和信奉异教邪说的结果。在
1976年关于性伦理学某些问题的声明中,罗马教廷重申同性恋不合法。
如果说在教会面前,同性恋作为一个主要抨击对象,那么在性学那里,同性恋
首先是个研究对象。卡尔·海因里希·乌尔里克斯在1864年至1879年间发表了12卷
关于同性恋的著作。这一成就对于卡尔·韦斯特法尔在1870年发现“相反的性冲动”,
对于克兰夫特一埃宾后来更为广泛的关于性变态的探讨,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克拉
夫特一埃宾那本被公认为性学确立的《性心理病》,自称是对“异常”所作的“医
~法学研究”(其副标题注为“特别涉及到厌恶型性本能”)。该书提出了从后天
同性恋到兽交癖的一套性反常分类表。其后,陆续出现了关于同性恋成因的三派观
念。自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学派在同性恋上做过大量文章。学说的核心是“异
性恋恐怖”说,这种观点认为儿时的遭遇在潜意识中种下了异性恐怖的种子,成年
以后会害怕与异性作怪的接触。按照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同性恋的行为是受环境
的影响学来的。如果与异性的交往受挫,有不愉快的经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而
同时又受到同性的诱导,走上了歧途,就成为同性恋者。对生物学因素的探讨多不
成功,但人们仍寄以较大希望。
同性恋的原因尚在探讨之中,这为同性恋的伦理评价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
性伦理学必须知难而进。
《金西报告》表明,在本世纪40年代抽样调查的美国男性中,有37%的人在他
们生活的某一时期曾经有过同性恋的体验,而且达到情欲的高峰。然而,这些人当
中绝大多数人主要是进行异性恋。自人男性中只有4%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专门搞同
性恋。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林德纳作了类似的估计,美国男性中名副其实的性颠
倒者占男性总数的4—6%。至于女性同性恋,其频繁程度被认为只相当于男性的一
半。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同性恋体验,男子同性恋的历史比女子同性恋的历史更为
悠久,情况也更为乱七八糟。金西还特别指出:“既然同性性行为如此之多。既然
古希腊和当代许多文化并不象英美社会那样严禁它,那么,一个人对任何一种性刺
激产生反应,而不管这刺激是来自异性还是同性,’就必定是人类的基本能力。同
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都是人类学习来的行为模式,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人生
长于其中的特殊文化的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人们在轻易断言同性性行为是遗传来伪
或终生不可改变的之前,最好仔细地考虑一下社会文化的作用。”'注'笔者并不完
全同意金西的观念,但以为他所强调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文化对同性恋的影响和作用
还是值得重视的。
整个20世纪,特别是在战后岁月里,西方社会里出现了带着同情心来描绘同性
恋的文学,并且为同性恋者争取得到法律和社会尊重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尝试也多了
起来。最公开的抗议是同性恋者自己发起的,他们通过象“玛塔齐纳会社”、“同
性恋活动分子联盟”和“比利蒂斯的女儿们”这样的组织进行抗议活动。玛塔齐纳
会社正式成立于1951年,目的是要增进同性恋的权利。哈里·海在1950年11月为该
会起草的倡议宣称它的目的是实现“使我们这个最大的少数派中的每一成员从社会
迫害下解放出来的英勇目标。”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说同性恋者与别的反抗压迫的
少数派,有一个共同的事业。唐纳德·米伯斯特·科里在他的颇有影响的是美国的
同性恋,一书中说:“同性恋者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于民族的、宗教的和其他种族群
体的成员。”同性恋解放的早期理论家期待着实现“同性恋者的目标”,即摧毁性
主体之间由社会而形成的划分。在创造遍及西方的城市社团过程中,同性恋者已经
变成一支有实际影响的少数派力量,它具有复杂的文化,不同的政治行为和物质手
段。1971年6月27日,5000多名同性恋者穿过曼哈顿向中央公园进军,进行“同性恋
大军”示威游行。不仅成人同性恋组织有代表参加,而且也有大学校园的组织,包
括来自哈佛、哥伦比亚、拉特吉尔斯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组织参加。
毫无疑问,在同性恋欲望被斥责的社会文化中,选定或鼓吹女性或男性的同性
恋个性身份,不仅是伦理选择,而且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政治选择。美国学者韦克斯
在80年代中期出版的《性,不只是性爱》一书中指出:同性恋的身份揭示了压抑与
机会,必然与自由,权力与快乐的作用。性身份在当今世界上之作为以性为中心的
政治的出发点似乎是必然的。按贝尔和温伯格的说法,男女同性恋身份最终关系到
的是“在世界上的生存方式”,或者按福科的想法。是“努力开创与发展一种生活
方式”。但这也意昧着它们关系到行为的伦理性。在韦克斯看来,除非以承认人类
的多样性为起点,否则不会找到出路。性欲,生活方式和性关系都存在着多样性。
彻底的性政治学肯定了在它们之间加以选择的自由。这种从性开始。但又超出了性
的观念是当代的性的政治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这里清晰地表明,同性恋的漫延同西
方社会政治伦理的自由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不过,尽管1967年英国国会已撤销了长期存在的关于成年人之间经双方同意的
同性恋行为构成一种犯罪的立法,同性恋在西方社会依然为广泛的社会舆论以及各
种规范所反对。曾经做过里根总统助手的帕特里克·布坎南1983年5月24日在《纽约
邮报》写道:“可怜的同性恋者,他们已经向自然宣战,而现在,自然正在施以可
怕的报复。”
台湾《联合报》1984年11月15日发表的《同性恋怪风吹乱美国三军》一文进而
写道:多年来,美国一直秉持全世界最严格的政一策,严禁军中同性恋。一项严格
执行的国防部政策指出二“同性恋者的存在,会对维持武装部队纪律、良好秩序及
士气产生不良影响。”国防部的纪律显示,每年约有1700名军官与男女士兵因同性
恋而被开除军籍。还有很多人为了同性恋而吃足苦头。他们很可能遭盘洁,在毫无
证据的情况下被迫出席多次听证会,受军法审判,甚至因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