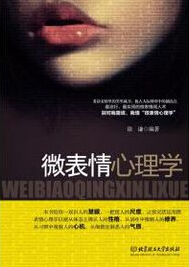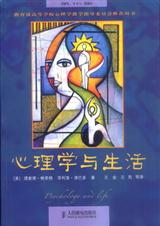性伦理学-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苦无处诉。她愤然出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被捕。
三是诉到法院,久拖不决,也使一些要求离婚的妇女心灰意冷,走上了犯罪的
路。农村妇女离婚起诉不易,且不说那30元诉讼费,使那些兜内分文没有的妇女望
而生畏,就是那介绍信、诉状又有谁能给开?谁能给写呢?(法律没有规定离婚必
须有介绍信和书面诉状)就是介绍信开来了,状纸递上去了,往往迟迟不见传讯。
据说有些执法人员认为离婚案件拖一拖可增加自动和好的可能性,于是一拖再拖,
一年两年过去了,要求离婚的妇女口婆家怕丈夫打,回娘家又不留,失去生活来源,
无奈再寻配偶,导致犯罪。罪犯靳某的丈夫司某被单位解雇,司怀疑是靳在作祟,
便经常对她进行打骂和人身污辱。靳某不堪忍受欺凌,多次向大队、公社、法院提
出离婚,法院责令司某具结悔过,司对靳的迫害愈加厉害。后来法院判决离婚,司
坚决不同意,并扬言“要判离,我就带刀子去。”当靳到法院要求快些结案时,审
判人员竟说:“他说拿刀子来,谁知是冲着你还是冲着我们。”法院不敢秉公执法,
迟迟不予结案。靳只得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而中级人民法院让她回基层法院解决。
在一年多的诉讼中,靳某四处奔走,每月找法庭一次,农村几个乡才设一个法庭,
翻山越岭,好不容易走到,不是见不到人,就是让你回去再等一等,她本想通过法
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摆脱不幸的命运,但法院的态度使她失去了信心,她厌倦
了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于是就断然与另一个未婚男人远走高飞,并生育了两名子
女。五年过去了,他们仍恋着家乡,当他们回到家乡,靳又到法院要求与司离婚时,
却被法院以重婚罪将她判刑入狱。
5、妇女贪图享乐,追求淫荡生活,导致重婚犯罪也是有的,但为数不多。
基于以上比较有说服力的调查,性伦理学对重婚问题至少应提出以下四点见解:
首先,从总体上看,重婚犯罪行为侵犯了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破坏了
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是一种严重的家庭犯罪,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反动力
量。其次,对重婚犯罪著必须依法查处。为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巩固和发
展,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重婚犯罪,特别是对那些在重婚中以种种卑劣手
段残害妇女儿童等严重罪犯,要按数罪并罚的原则追究其法律责任。其三,司法行
政部门应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使他们能够排除种种干扰,
为受害者申张正义。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案件,应果断判决离婚。对判决不
准离婚,或暂时不易判离的案件,应当深入细致地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协助有
关部门对坚持离婚一方,特别是女方,进行妥善安排,防止再受虐待和犯重婚罪。
对于由于反抗包办强迫婚姻,或一贯受虐待,要求离婚又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而
被迫出逃,为了生活又与他人重婚的妇女,应以教育为主,可不按重婚对待,特别
不宜收监。最后,需要特别强调在普及婚姻法和刑法的基础上,重视逐步提高广大
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性伦理素质;从长远意义讲,这将是在广阔的社会领域,有效
地阻止重婚犯罪漫延的最长久起作用的措施。
四、乱伦
乱伦。是指男女双方明知有血统关系,在一定的亲等以内,进行不法性交的行
为。例如:父亲与女儿,兄弟与姊妹之间的性交等。
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明确地把乱伦归之于犯罪行为。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6
4条(乱伦罪)规定:“与尊卑亲属、或与直系姻亲或与姊妹、兄弟犯乱伦而引起公
愤者,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继续为乱伦者,处2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成年人与
未满18岁人犯乱者,其成年人依各前项规定加重其刑。父母之一方经宣告处刑者,
丧失其亲权或法定监护权。”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30(2)条(近亲相奸)规定:
“知情而与直系等亲属、直系卑亲属或有共同之双亲或共同之父或母之兄弟姊妹
(或全血缘之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姨母,或侄儿、侄女,甥女)结婚、同居
或性交者,即犯等三级重罪之近亲相奸罪。所谓‘同居’系指有表现婚姻状态或外
观下,共同生活而言。本条所谓亲属关系包括非姻出之血缘关系与养亲子关系在内。”
在西方人看来,构成乱伦罪的要件一般是:第一,只要实施一次性交行为,就足以
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相互同意与否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诚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所言:乱伦这个主题对人类具有一种奇
特的魅力。人类远在掌握写作艺术之前,就被这一主题吸引住了。在无数民族的神
话中,我们都发现了有关乱伦的情节。人类似乎从未厌倦它,而是一再地发现它具
有新意和引人入胜之处。但是,即便在爱情和性是婚姻的主要促成因素的地方,也
存在着规定某个人可以或不可以和别的什么人结婚的规则。在所有文化中,我们都
不难发现最为严格的规范往往正是乱伦禁忌。
为什么普遍存在着乱伦禁忌呢?学者们提出过以下几种解释。
其一,童年亲密理论。这一理论是由爱德华·韦斯特马克提出的,它在本世纪
20年代初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韦斯特马克提出,从早期童年起就在一起长大的人
(如同胞兄弟姐妹)相互之间没有性吸引力。这一理论不久便被摈弃了,因为有证
据表明,有些儿童的确对其父母或亲兄弟(姐妹)有性方面的兴趣。然而,最近的
一些研究表明,韦斯特马克的理论可能有一些道理。阿瑟·沃尔夫对中国台湾北部
的研究证实了共同养育会产生性冷淡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沃尔夫着重对仍在奉
行“童养媳”习俗的一个社区进行了研究。证据表明,当小“夫妻”将来长大成人
结婚之后,这种安排就带来了性困难。报道人含蓄地表示,亲密导致缺乏兴趣和刺
激。他们之间缺乏兴趣表现为,他们的子女比那些不是一起抚养大的夫妻的子女少,
而且寻求好外性关系的可能性也更大。不过,这种理论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所有社
会都禁止兄弟——姐妹通婚的问题,也没有对为什么普遍限制父母——子女通婚的
问题作出解释。
其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提出《乱伦禁忌是对无意识的乱伦
欲望的反动。野蛮人对乱伦这件事比我们敏感得多。也许他们常承受更大的诱惑,
所以不得不建设更牢固的防御工作为证实这一论点,弗洛伊德从其丰富的资料里抽
出若干片断以满足读者:
在美拉尼西亚,男孩和他的母亲、姊妹间的交往,有着种种限制。例
如在里皮斯岛,新海布里地族的一支,男孩到达某一年龄后便不可再属于
家中,而必须迁入“营合”内吃、住。当然他尚有权回到父亲的家中寻求
食物,但如他的姊妹们在家里,他便难免于徒劳往返之累了;若无姊妹在
家,他可坐在门口吃食。在野外兄妹不期而遇时,她必须跑开或躲起来。
男孩若在路上认出他姊妹的足印,他便不再顺那条路走。女孩亦然。事实
上,他不但不可以说出她的名字,甚至在言语中避讳着它。此种“回避”
始自成年仪式,而后持续终生。儿子和母亲间的冷漠随年岁而增加,通常
母亲方百的态度变化得更为明显。一个母亲要送食物给他的儿子时,她只
把东西放在地上,等他来拿。和他谈话时她不再表现所谓的母子亲情,而
系使用着对待外人般的礼节。类似的情形在新苏格兰群岛也很普遍,兄妹
在路上相遇时,女的闪入丛林内,男的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行。
在新不列颠,瞪囗半岛上的土著,女人婚后再也不和她的兄弟谈话,
她再也不提他的名字,迫不得已时也只使用转弯抹角的话来表达。
在新麦克林堡群岛堂兄妹间也遭受如斯限制,彼此间互相不能接近,
不可握手,不可互送礼物;不过尚被许可站在远处交谈。与姊妹乱伦则必
须处以吊刑。'注'
弗洛伊德还强调指出,阻止乱伦的栏栅可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成就,象其他的
道德禁忌,在许多人身上已成了遗传的天性;然而,精神分析发现个人面对乱伦之
诱惑时挣扎是很剧烈的,他们常以幻想甚至在实际上逾越了此一栏栅。弗洛伊德的
理论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需要明确禁止乱伦。
其三,合作理论。这一理论是由早期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提出,并由莱斯
利·A·怀特和克劳德·萧维——斯特劳斯详细加以阐述的。泰勒在1888年发表的一
篇论文中写道:“族外婚能使一个发展中的部落,通过与其分散的氏族的长期联姻
而保持自身的紧密团结,能使它战胜任何一个小型的孤立无助的族内婚群体。这种
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屡次出现,这样,原始部落的人们在他们的头脑中必定直接
面临着一个简单而实际的抉择:或进行族外婚,或被彻底根绝。”怀特在《对乱伦
的限定与禁止》中进一步发挥说:乱伦禁律实质上有其经济的动因。族外婚的规则
不是个人心灵中的产物,而是社会制度在其变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结晶。禁止近亲
繁殖,强迫推行群体间的婚姻都是为了获得合作的最大利益。诚然,婚姻确实提供
一种性行为和性满足的手段,但婚姻制度决不是由性欲引起的,相反,乃是为促使
合作而竭尽自己的全部应变能力的社会制度所采取的紧迫措施。作为一种制度的婚
姻,能在社会文化过程中而不是在个体心理学中找到自己的解释。爱情不是婚姻和
家庭的基础,不管这种观点多么受人珍爱。没有一种文化会把象爱情这样短暂易变
的情感作为某种重大制度的基础。婚姻和家庭是社会满足个人经济需求的首要的和
基本的。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正是起始于对乱伦的限定和禁止。应该说,合作理论
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然没有充分解释乱伦禁忌在一切社会中的存在,因为其
他习俗也可以促进联盟。而且,在历史上乃至当今的西方社会,不乏有人借助乱伦
巩固和延续其经济利益。
其四,自然选择理论。这一理论是对乱他禁忌的科学解释。它着重指出近亲繁
殖,或家庭内婚潜在的危害性后果。同一家族的人很可能带有同样有害隐性基因。
因此,近亲繁殖的后代比起没有亲属关系的夫妻的后代来,前者由于基因失调而夭
折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摩尔根是这一理论的著名倡导者。这个理论多年来都受到
排斥,因为在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上,人们认为近亲繁殖不一定有害。恩格斯则以
其远见卓识积极支持并阐发了这一理论。恩格斯在《家庭一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指出,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
第二个进步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
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
大概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
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
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
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则是在怎样发生作用的最好例证”。
不容置疑,凡血亲婚配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
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由此可以得出结
论:禁止乱伦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进步的必然要求。
在当代中国,尽管刑法中没有乱伦罪,但婚姻法中则有关于禁止结婚的血亲关
系的明确规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除禁止直系血亲、同胞兄弟姊妹、同
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姊妹结婚外,对其他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
作了以习惯的规定。新婚姻法除保留禁止直系血亲结婚的规定外,又明确规定禁止
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第6条第1款)。这一修改的实际意义,就是禁止出于同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表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其目的在于提高人口质量,保障下一
代和民族的健康。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社会伦理价值。因之,乱伦行为必须受到社会
伦理的强烈谴责和惩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
处分的若于规定(试行)第十三条就明确规定:“与直系血亲发生性关系的,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性伦理学毫无疑问要对乱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有的性伦理学家居然公开对乱伦的不道德性提
出质疑。例如,法国学者热内·居伊昂在《性与道一德》一书中就鼓吹从性快乐的
观点来考虑乱伦。在他看来,如果性乐趣不受一些道德含义的影响,如果人们只把
性乐趣当作合法的以性行为为目的事情看待,那么乱伦只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事
情本身在伦理上就无关紧要了。假如没有理由对性意识所利用的特殊机制进行强制
性审查(只要没有强迫,各方都是自愿的),那么性伴侣的世俗身份与性行为本身
及随之而来的快乐就毫无关系。对乱伦的规定实质上完全是传统的,只存在人的脑
子里,而没有相应的生物的或生理的真实反映。此类观点不仅与恩格斯所阐述的关
于禁止乱伦的“自然选择”理论背道而驰,而且也是从前面所介绍的三种理论上的
倒退。对此,我们的性伦理学必须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