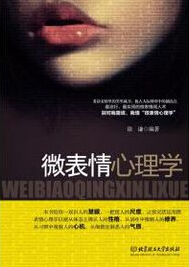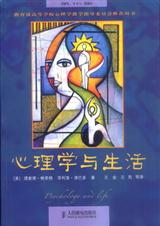性伦理学-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
的社会为Democracy的社会。”'注'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
社会主义》一书中则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上述有关内容。这部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世
界名著,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存在一个每天不断进展的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
精神的不安和动摇日甚一日,显著地表现在社会所有的阶级之间,要求着彻底的改
造。每个人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摇动。发生了许多问题,日益为广大范围的人们所
注意,而关于这些问题之能否解决都是从各自的立场来议论。其中最重要问题之一,
而且日益显著的,便是妇女问题。一切妇女,不问其社会的身分如何,在“性”的
方面向来在社会的发展途径上始终为男子所压制、所统治、所污辱,所以必须改变
现在的国家政体和社会组织以及法律的制度,以消除这种状态,这是妇女全体共通
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当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期望只欣赏在它的沃土上开出的鲜花,品尝它所酿造出的美酒,来免过于浪漫。期
望常常是单纯的,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因之,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性伦理的
大变革,既有积极的主流,也有其消极的支流,乃至一些沉滓的泛起。这里仅举两
例。其一:据合众国际社北京1988年11月28日报道:卫生部官员今天说,对6。72万
人进行血液检查的结果发现18位居民——7名大陆中国人和11名外国人——带有艾滋
病毒,另有3名外国人已得了这种使身体失去抵抗力的致命疾病。卫生部的这一宣布
是官方首次承认艾滋病在中国居民中间的扩散比原来认为的要严重。妓女、婚前性
关系以及离婚的增加促使性病发病率的上升。人们一度认为共产党政府在1949年掌
权后已消灭了性病。卫生部的一位性病专家说,社会性病正在中国卷土重来,卫生
专家却缺乏检查这种疾病传染情况所必要的法律手段。性病的年增加率为300%,尤
其是在对外国人开放的沿海城市。其二,据《光明日报》报道。1990年8月初,世界
卫生组织举办了“艾滋病在亚太地区”国际会议。30余国的代表聚首研讨防治艾滋
病蔓延的对策。艾滋病正在世界各地肆虐,中国不能高枕无忧。目前,我国已成立
了艾滋病委员会,并制订了3年规划。当前重要的是加强关于艾滋病的科学宣传。只
有当全社会对艾滋病有了广泛的正确认识时,各种防治措施才能效地贯彻。
《中国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
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
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
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
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在迎接势在必行的性伦理大变革之际,这段
话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之,在本世纪,中国性伦理的发展有两次大的变革。五四时期的性道德的大
变革没有切实完成。其主要原因,就是虽然具备了性道德变革的一些必要条件,但
缺乏变革所需要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充分条件。然而,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性道德的
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五
四时期作为中国性道德观念大变革的起跑点。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
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复兴中,我们又
一次面临着性伦理的巨大变革,我们需要并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道
德价值观,我们也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伦理学。
结束语 性关系的伦理展望
不管人类对自己记得多少,了解多少,他总是力图看到把现在和将来隔开的幕
布后面。这种愿望在两性关系领域表现得尤其强烈,其原因是每个人都与特定的性
关系发生着直接的联系。
人类性文明的进步,也要求我们善于大大地向前看,向前看好几十年乃至数百
年。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不仅要善于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敢于
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注'如果再能充分考虑到性道德本身就具有“超越性”
的重要特点(参见本书第一章),那么,研究性伦理发展的未来前景,便顺理成章
地成为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
回顾性文明的思想发展史,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十分关注性关系的发展趋向。
其中,为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普遍肯定的以下三位思想家的有关论述特别值得重视。
一位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这位出色地描绘了人类婚姻家庭发展史图的学者,
相当关注一夫一妻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
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
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
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
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
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
况。既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
别显著,那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
平等为止。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
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注'
摩尔根在1877年所做的上述预测无疑是大胆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人
类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
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
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
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
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
偶制。现在,已然在部分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少已把绝大部分耐久
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
减少到最低限度。于是,摩尔根的问题便具有了现实意义: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
的原因而产生的,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可以不无理
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这时它才可能十足地实现。男子的
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
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将逐步地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
将逐步地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将逐步地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
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
将逐步地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
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摩尔根的论断的实际价值恰恰在
于此。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更为简洁的语言揭示道:“我
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
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
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
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
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
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已
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
舆论——如此而已。”'注'
恩格斯的话发人深省。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中国公民,是不是恩
格斯所寄予厚望的“新的一代”呢?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从实际上看,尚不完全
是,或不真正是,相当一部分人则完全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
面的。旧的性道德的束缚是其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有必要首先对性道德的前进
方向有个总体的把握。概括地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两性关系必然要
发生巨大变革。与之相适应,也必然形成新的性道德。这种道德发展的基本趋势,
就是随着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其调节范围和作用越来越大,并将逐步超过直接的
经济调节、法律调节和行政调节,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变成决定性的调节工具。那
时,爱情将成为两性关系(包括婚姻关系)的唯一可能的主要调节者。
关于性道德发展的这一大趋势,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也做了精
采的论证。
‘将来的妇女”是《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第二十八章的标题。著者在说明该
章的宗旨时表示,他要从以前各章所说的一切,引出关于两性道德地位的结论:
人类对于冲动的满足,只要不损害他人,自己的身体尽可由他们自己
处置。满足性的冲动也和满足其他自然冲动同样,是个人的私事。既不必
对他人负责,也绝对无第三者插嘴的余地。我们要怎样喝、怎样吃乃至怎
样穿衣睡觉,都是我的私事,和异性的交际也是同样。见解和教养、个人
的完全的独立、因新社会的教育及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一切性质,使各
人对于自己有害的行为决不会做。所以未来社会的男女,将比现在的更有
自制,更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关于性的问题的一切假道学及神秘主义自然
消灭,两性关系将更为自然而健全。假使在结合了的男女之问,发现了不
和、失望和厌恶,那时候,对于已经不自然的、从道德来说就要求解散不
道德的结合。现在使妇女独身或卖淫的这些条件消灭的时候,男子便不能
再行支配女子。另一方面,因社会状态变化,对于现今的结婚生活给以重
大影响,屡屡妨碍结婚生活的许多障碍,可以彻底的扫除。'注'
不难看出,倍倍尔关于未来社会两性关系的展望同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
“性解放”思潮有着社会前提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列宁称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
主义》“全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注'这是应该明确的。
同样应该指出:倍倍尔关于未来两性关系的展望,同封建的、宗教的禁欲主义
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某些人所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性伦理观也有着根本区
别。
有些同志反驳说:恩格斯和倍倍尔关于两性关系发展的预测指的是共产主义社
会,现在讲就是超前,就是行不通的。不错,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恩
格斯和倍倍尔的有关主张的确还不能作为普遍道德要求通行于社会各个层次。但是,
难道为此就应该把这些科学的思想束之高阁吗?难道当代中国人在创建新道德方面
就应该守株待兔、无所作为吗?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所称为共产主义的就是
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我国,包括性道德在内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
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包括性道德在内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
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性道德是渺茫的幻想”
的观点是错误的。
“共产主义性道德”一词,从我们目前的理解来看,在使用中有广义和狭义的
区别。从广义上来理解,共产主义性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它包括了社会主义社
会性生活中的各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从狭义上来理解共产主义性道德,则主要
指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最高层次的性道德要求。其它一些要求是较低或最
低的层次。我们不能因为一般人还不能立刻达到共产主义性道德的最高要求,就认
为共产主义性道德只存在于未来,从而否认在现社会提倡和宣传共产主义性道德的
重要意义。相反,不同层次的性道德要求,在实践中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共产主
义性道德代表人类性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已实际上达到
的性道德要求。共产主义性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性伦理道德要求总体中,居
于主导地位,对于其他较低层次的性道德,都有指导作用。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不
能只停留在较低层次的水平上,还必须沿着性道德的阶梯,不断向上攀登。
当代性道德的进步,往往要以批判继承及扬弃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