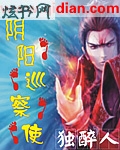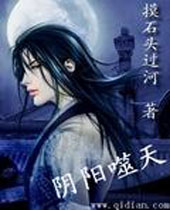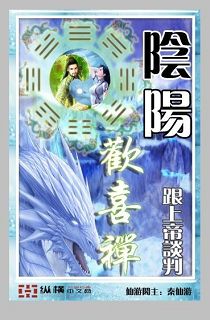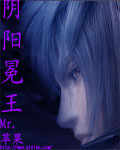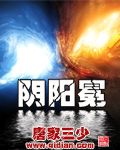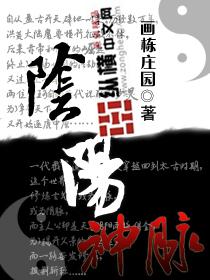阴阳碑-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六爷踏着小巷清晨的沸腾,回到了杠子铺。
六爷在杠子铺过夜,管家要给六爷暖脚,睡早床要随六爷的意。六爷若在城里太太那过夜,管家是不敢贪早床的。得早早地起床开门,照应杠夫们的活路和等着六爷回来。
“刚才城里刘府有请您,让我给挡回去了。”瘸子张向六爷讨好道。
“噢?”六爷盯着瘸子张。
瘸子张吓得大气不敢出,小心翼翼地说:“您不是有吩咐么?”
“就是那个刘篾匠?”六爷似乎记起来了。
“正是,这几天是他过期日,娶第十房姨太太。”
“噢?娶他娘个屁!”
娶第十房姨太太的刘老爷子名叫刘仁仕,府上坐落在城东头的一条名为“篾匠道子”的小巷子里,刘老爷子早年做过几天篾活,成年后就洗手不干了。刘老爷子的祖上是开篾匠铺的。说起刘老爷子的祖上开篾匠铺,可要追溯到清道光年间。那年一个叫刘智元的河南新野人流落襄阳,从隆中山里砍来几根南竹和十几捆茅草,在偏僻的城东头的一块荒地上搭起了一间茅屋,开了家小篾匠铺。刘智元幼从良师,篾活为当地魁首,只因原籍遭灾,遂独自来襄阳闯生意。刘篾匠的篾铺开业后,以诚待人,和气生财,无论粗活细活,总能巧夺天工,很快就在襄阳有了名头。慢慢又有一些穷人逃难到这里,在刘家篾铺左右盖起了一些茅草房,襄阳城也就有了一条名叫“篾匠道子”的小巷。
尔后,其子刘亭福继从父业,渐成名匠,清朝末年,孙辈刘书传广学博览,钻研技艺,生产、生活用品及工艺品,皆能编制得活龙活现,经久耐用,并带出了一子一徒。刘书传在襄阳有“四片篾”之誉,一刀子下去四片篾:一曰青子,二曰二道子,三曰三道黄,四曰四道,片片竹篾都能用。做粗活如篮子、筲箕、箩筐、篓子;做细活如药铺的药筛子、药浅子、粮行的米筛子、西筛子。刘书传做的葛纹团窝,赶马车的用来作盛水器,不滴不漏,不怕磕碰。打渔人请刘书传做竹毫子,其状如炮弹形,一头小,一头粗,里面放上鱼饵下到水里,鱼儿能进不能出。姑娘出嫁请刘书传编只陪嫁席,一张篾席四个工,编起后能折能叠,尤其席上有各种花鸟虫鱼,皆能底纹变化而成。可惜刘书传太洒脱、太任性,一次与襄阳名匠齐木匠打赌:只要木匠能做的,他都能做,竹房子、竹椅子、竹凳子、竹床竹枕竹柜子,若有不能,肝脑涂地。齐木匠用檀木挖了一舂米“对窝”,刘篾匠也用篾编了一“对窝”,齐木匠当众让人用石锤舂米以争高低,刘篾匠应战气壮如牛,结果刘篾匠所编的篾“对窝”当场被捣破。当夜,刘书传抱头撞墙身亡。
父亲的身亡,使刚刚成年的刘仕仁产生了与篾匠铺彻底决裂的念头,他要换一种活法。于是,刘仕仁高价变卖了父辈刘书传传下的家业,托人在襄阳城前街举办了一个刘篾匠篾竹工艺品拍卖会,引得汉口的商人和收藏家争相抬价收购,轰动汉江上下。刘仕仁将拍卖所得收入购置了田产出租,当起了刘老爷子,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
篾匠道子的刘篾匠消失了,诞生了一个刘老爷子。只是六爷不承认这个刘老爷子。刚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刘老爷子,吃喝不愁,唯一的嗜好就是娶姨太太,这就更让六爷可恨。不就是一个刘篾匠么,凭啥娶这么多的姨太太。可气的是,女人只要是进了刘府,那肚皮就好像充了气似的,一个赛一个。听说刘老爷子要娶进门的十姨太才十六岁,刘老爷子可是她爷的辈份了,六爷见不得这缺德事,六爷把牙咬得吱吱地响。
一缕晨晖从窗棂上射进来,透过纱幔,投射在那张双狮滚球的樟木床上。六爷斜躺着,一副惬意的样子。
瘸子张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他将颏儿尖尖的下巴贴近六爷那张光滑白嫩的长脸:“劳头忙派人来了,是城里刘府托的。刘府的礼品挺重的,就放在前面大厅里。”
“今日是刘篾匠过期的第几天?”
“第三天。”
“什么?”
“是第三天。六爷不到场,这几天弟兄们闹得开心着呢。”
“看来我是要买劳头忙的面子哟。走!”六爷说的是大实话。
今日是劳头忙派来人说情,这个帐六爷必须得买。说起劳头忙,只不过是一帮江湖上的散兵游勇而已。劳头忙长年活跃在汉江中游一带,没有固定的山头,也没有严密的帮规,其成员大都是汉江各码头上一些斜着嘴叼着烟卷的地痞和一些只敢隔着裤子摸女人屁股的流氓。帮派外形为松散型,其内具有黑帮性质。一言定论:成不了多大气候。劳头忙的兄弟称自己的头子为大爷,大爷姓劳。劳大爷年轻时靠一支在汉江上打野鸭的土铳起家,拉起了一帮子人,曾作威作福了一阵子。后来老了,再后来就瘫在了床上,长年呆在襄阳城内,已是苟延残喘。劳头忙里的一些小头目早就是各行其事,拉起了自己的小山头。在襄阳城,劳头忙与六爷青帮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但六爷并不小看他们。别看这些地痞流氓,成天在城里城外码头上下游手好闲的,成事不足,可要坏你的事也够你喝上一壶的。想当年,六爷在这古渡口打码头,有“龙鞭”保驾是一,劳头忙的弟兄们助威捧场是出了大力的。六爷有着一颗仁义之心,都是江湖上混饭的,按理也算是六爷的弟兄。六爷看重劳头忙的兄弟,劳头忙的兄弟对六爷也就百依百从,这里面的故事只有六爷心里清楚。
干燥的风从清晨就开始发狂,漫天遍野飘旋着枯叶儿,尘埃遮天蔽日,世界一片浑黄。
那个秋风狂舞的晨后,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们敲着打着各式各样的卜板缩蜷在刘府所在的篾匠道子小巷里,像田间寻找食物的野狗,面目上凝聚着饥饿和残忍。狂风摇摆着他们褴褛的衣衫和蓬乱得如杂草一般的长发,个个眼里都不时地泛出鱼白。散发在他们身上那种令人可怕的气息在空中萦绕凝聚,最后如黑云般朝刘府压来。
六爷买了劳头忙的面子,乘着轿子车朝着刘府而来。此时,刘府门前的气丐爷还没见到六爷的“神鞭”,折腾得高潮迭起。一大帮文叫花子,带劲地耍着“文讨”几十只竹板噼呖叭啦地响着,丐帮们即兴编唱着“莲花落”:
打竹板,命真苦,
眼前来到大刘府。
刘家篾匠娶姨太,
有钱无钱不见面。今日不请老爷来,
攒钱为的买棺材。
刘府棺材买得好,
装了死人跑不了。
本应是喜庆之日的刘府,门前却是一派乌烟瘴气的。刘府不是不懂规矩,娶姨太太的婚宴本是首请六爷的,谁知一连几天就根本见不到六爷的人影。这样闹得已经是第三天,刘府的人四处活动,不惜重金托人请出了“劳头忙”,才算盼到了六爷的回音。
六爷的轿子车离刘府还老远的,刘府门前的叫花子们就似乎闻到了什么气息,竹板声弱了,喊叫声小了。不一会,一衣衫穿戴都很规矩的小叫花子,头顶着一个四角周正的板栗色方木盘,被自己的兄弟们前呼后拥,来到了刘府门前。
“龙鞭到!”随着这一声吆喝,刘仕仁躬身小跑步地出门亲自接下了小叫花子方木盘中的“龙鞭”,他双手托捧着“龙鞭”,神情十分庄严地将其挂在了自己府上的大门外。霎时,刘府门前一片寂静。
六爷精致的轿子车停在了刘府的门前。车夫穿着青布衫,月白缎套裤,粉绿腰带,脚上穿着薄底快靴,头上一顶短梁小帽。既精神又有几分滑稽。瘸子张小心翼翼地揭开轿帘,六爷气宇不凡地走了下来。今日六爷穿着古铜色绸套裤,裤腿紧扎,上身一条半长的乌红拷纱袍子,外边套着件碧青色马褂。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刘仕仁点头哈腰地讨好六爷。
六爷拱拱手:“迟到,迟到了。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龙鞭挂在了刘府的门外,六爷请上座,刘府老爷子的十姨太才算是和和气气地给接了进来。
第二十三章
别说在这条窄窄的直线似的马背巷,就说在襄阳城,顺兴药铺都是叫得挺响的。
小巷的中间靠江的一面,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店铺。这座店铺是一幢旧楼。大门的漆皮几乎已经褪尽,木质表层朽成灰白。旧楼前的门檐下,悬挂着一块已分不出底色了的木匾,上面刻写着:顺兴药铺。大门的两侧,左边卧着一把大铡刀,刀口上飘着阵阵药香,刀座被一捆药草簇拥着。右边是一座石辗子,细长的石槽上,滚动着一个石饼。顺兴药铺进门迎面的就是一堵药墙,一格格的药抽屉,装着一个又一个关于顺兴药铺高超医术的故事。
如今的顺兴药铺坐堂的是字元先生。其父正福先生几年前上隆中山采药,不幸从山岩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脊骨,只能常年病卧在床。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一长,小字元就没有好脸给老子看,再加上字元太太是城里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那能终日守在公公的床头,也就少不了冷一句热句的让公公听话。正福先生躺在床上整日回想往事:从带着儿子字元沿江而下,到隆中山搭茅庐卖药,到马背巷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到如今襄阳城里的名望……。有一日,正福先生再也想不下去了,趁儿子儿媳外出之机,滚下床,爬到药柜前,从抽屉里抓了几味药,吞下去,躺在床上就永远地睡了过去。
父亲之死,字元伤心之余,更多的是解脱,他得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福先生是受够了儿子儿媳的气才喝药而死的,这就让儿子字元坏了名节。正福先生与人为善,行医重德,医术与德行都是有口皆碑。字元不尽孝道,乃有丧天害理之嫌。名医正福先生吞药而死,不说马背巷,就是整个襄阳城都似乎要把其儿子字元的背骨戳穿,弄得字元太太好长时间不敢进城。
人都是吃五谷杂粮,吃五谷杂粮谁都免不了要生病,襄阳城的人生病找顺兴药铺的居多。字元先生想,名声,名声能值多少钱?字元先生的处世哲学是:认钱不认人。字元年轻气盛,人精脑子活,他并不一味地躺在祖传的几帖秘方上睡大觉,而是讲求活用和发展。他从一个偶然的病例中,发现隆中山里的一条小溪的泉水,与几味草药相配后,让人服用后有壮阳补肾之功能。于是他积极着手对各种不同生理特征的人进行悄悄的试验,均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不禁大喜。
字元先生的为人与其上辈完全不同,他讲究的是实惠,是利益的交换。他不认为医德是兴旺药铺之本,而认为以医求富,乃是兴家之策。对上门来求药问医者,字元先生最关心对方是大户还是小家。他是大有大的安排小有小打发。一日城里来了一位神情沮丧的寡妇,进了顺兴药铺后,掏出钱来要买砒霜。字元先生一眼便知是妇人寻短见所用,却仍是收钱卖之。当夜,该妇人用在顺兴药铺买得的砒霜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后,引起城里城外的一片咒骂声。字元先生则是不以为然,名曰:药铺做的也是生意。这样,顺兴药铺的名声也就不那么好了。
字元先生名声不好,但医术还是地道,襄阳城有不少重病人,都是吃了顺兴药铺的药后起死回生的。人生在世命为首,只要能活命,那钱又算什么,钱是王八蛋。顺兴药铺的生意依然很好,字元先生依然忙得不亦乐乎。襄阳城的人不敢得罪顺兴药铺,即便恨,对字元先生也只能敬而远之。字元先生也有个性情孤僻的性格,不说在马背巷,就是在整个襄阳城,字元先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朋友。当然,这并不妨碍顺兴药铺生意的兴旺。
字元先生与六爷是好朋友。
字元先生与六爷成为好朋友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六爷与人为善,待人既宽厚又大方,讲的就是人和,他字元先生再小气,也不妨六爷与他相交。不过,字元先生对六爷也很敬重,除了昔日的权府有恩于顺兴药铺外,六爷的仁义,也让字元先生不可小看。字元先生不爱串门,可六爷杠子铺,他隔三差五定要去泡上一会。六爷朋友多,受吃受请,接人待物,进城回巷往往是疲于奔命,但每每路过顺兴药铺,只要见到字元先生在屋,他必进去坐上片刻无疑。
字元先生铭记着六爷的恩德。
讲起六爷有恩于字元先生,话要从城内洪字金铺说起。
洪字金铺是襄阳城一家大户,汉江上下几百里,要说购置金货认准的都是“洪字”金货。金铺的洪老板为人也算和善,只是把钱看得太重,显得太吝啬。城里人形容他,与太太做爱都舍不得多流出一点精气。当然,这话说得显然有点损洪老板。洪老板原有四房太太,多少年都没能给洪家半个后,洪老板为此在襄阳城一直抬不起头来。
洪老板的五姨太于一年前娶进洪字金铺。那天城里的刘媒婆领着一位泪眼红肿的姑娘走进洪字金铺,说这姑娘命苦,父亲被恶狗咬伤患了狂犬病,疯疯癫癫到处撒野,一头栽进了水井里。母亲跟着一个跑江湖的人走了。姑娘本有个亲戚在南阳做官,家事红火,没想到就在姑娘投奔而去的前一天,忽因匪盗深夜潜入,凶杀全家,抢走财宝,一把火将家宅烧个精光。刘媒婆说,细算起来自己还是姑娘的远房姨妈,闻讯后,就将姑娘接到了襄阳,寻思为姑娘找个好人家。正巧,洪老板托人上门求媒婆找个五姨太,这不,恰好瞌睡碰上了枕头。洪老板一看这姑娘长得挺灵气,他围着姑娘转了几圈,曲线也分明,便挤出了几滴眼泪,说道:“我这人就心软,这姑娘怪可怜的,让她留下吧。”其实,刘媒婆心里挺清楚,洪老板看中的不是姑娘可怜,而是姑娘“闪腰翘屁股”的身材。俗话说,闪腰翘屁股,生娃的老师傅呢。
其实,刘媒婆与这姑娘八竿子打不着边,媒婆说媒,不就为图得一点钱财。洪老板一高兴,让人打发了刘媒婆一只金耳环。刘媒婆当面道谢,一走出门,就转过身来,双手插着腰,朝洪字金铺吐了口痰:“我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