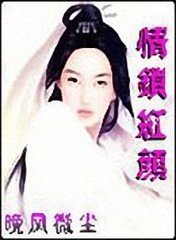红颜乱完结+番外-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房中安静了,楼澈看着楼盛半带威胁地“送客”出门,房中只留下他一人。
有些烦躁,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刚才为何会断然决绝舒豫天的提议,只是直觉上排斥着,想到不能留归晚在相府中,他就无法抑制地心痛;想到要把她送到那红墙高瓦中,更是心如刀绞……
他宠之爱之的女子,他怎忍她受半点委屈……
罢了,罢了……
“议事完了还坐着干吗呢?”书房门被推开,灼热的光线随之而入,楼澈睁开眼,在光晕中,看到归晚走了进来,清脆的声音带给他一丝平静。
他扬起眉,还没张口,看到归晚踏进房中,带着嫣然雅致的笑容,心中怦然一动,话到喉中,没有出声。
心如明镜,突然明白了。
滔天权势,只手遮天……换来的,原来只是她……
浅浅一笑啊……
****
走出院外,舒豫天一脸窒闷和不甘,回头望望相府的额匾,神色复杂,相府拐角的小道上一辆马车缓行而来,他跳上马车,才坐定身子,还来不及惋惜出声,车内早有一人盘腿坐着,姿势古怪,笑看着他:“怎么?看你的表情,似乎很遗憾……”
“楼澈本是权术之才,谁知也会如此死脑筋,”舒豫天看看对方,丝毫不感到奇怪,续说道,“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可惜?可惜什么?”
“可惜他败相已现,看来我这边也要输了……”
车上人忍不住一阵笑出声,好半天才忍住笑:“不用急,豫海那边似乎也不尽顺利,是赢是输还没有定论……再说了,你们个人输赢又有什么关系,最后得益的是整个家族。”
舒豫天脸色稍缓,想起刚才在相府中的情景,轻声一叹,不再说话。
马车向西,在落霞余辉中,渐渐消失……
*
天载四年,初秋之际,朝廷内风波不断,虽无影响局势之大事,小事却接连不断,党派之争愈演愈激烈,连京城普通民众都嗅到了些微气息。
秋风未起,八月末,京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小吏,突然上述弹劾户部尚书,在奏折中,他清楚明晰地指出户部尚书为官多年,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甚至连户部尚书所收取款目都标明地一清二楚,有如亲见,又哀呼此类官员不除,难以平民愤,难以肃朝纲,奏章所写,文笔犀利,饱含感情。就在第二天,皇上虽没有明言,却已有落案查实的意思。当朝首辅楼相不置可否。
第二日,又有工部官员弹劾那翰林院小吏,指出他在翰林院其间,为先皇所编写的史书中用意不良,有亵渎先皇的险恶用意。顿时,翰林小吏从原告沦为被告。朝堂之上,两派人争论不休。
这个事件拉开了天载四年党派之争的序幕,后史把它称为“翰林上书”。有后代历史学家指出,这个事件仅仅是把几年来小范围的党争拉到了一个大舞台上,同时,这也是皇上与楼澈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都有着试探对方的含义。而那个翰林小吏和工部官员,仅仅只是这场交锋的开路先锋而已。
*
相府依旧,红枫翩然。
自那场密谈之后,楼澈对舒豫天多出几分戒备,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原因无它,此刻分出精力与人手来对付舒豫天是非常不明智的,会直接影响到相府的实力,况且对付舒豫天容易,要铲除在南方根基稳扎的舒家却并非容易的事。
同时,他对舒家产生了极大的疑虑,皇宫后院之事,自从郑锍亲掌之后,消息极难打听,而舒豫天在书房中所提之事,分明对宫中之事了如指掌。难道他在宫中也有内应?
不动声色地继续利用舒氏,楼澈显得万分小心,暗暗警惕各方的动静,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部署,等着朝廷风雨的来临。
朝廷之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楼府外院官员进出议事,紧张忙碌。而内院之中,却依然是欢声笑语,不解忧愁。
内院中,丫鬟家仆,笑容依旧,没有经历过磨难,他们坚信着,只要有楼澈在,相府的天就塌不下来。
玉督(一)
轻托香腮,归晚一手拿着书卷,百无聊赖地看着,房门“嘎吱——”一声细响,她抬首,玲珑推门而进,脚步显得有些急,走到几案前,半低下身子,在归晚耳边低语。
“德宇公公?”微讶出声,归晚把书放到一旁,看着门口,沉吟起来。宫中总管此刻在院外求见?
对着玲珑点了点头,看着她又一阵急步出门而去,归晚提起十二分的精神,站起身,眺望窗外。这些日子,相府内院平静如初,只是这院中下人的欢愉平静是真,她却是半真半假,明白里掺着糊涂,这样,才能在暗涛下欢笑着,一天过完,又是一天。
德宇此时来,又为了哪桩呢?
“夫人。”斯文有礼的声音一如既往。
偏神想远了,归晚转过身,门口已站着一人,欣长的身形,宝蓝长衫,挟着薄薄秋意,倒似一个世代书香的公子,哪里看得出他是如今宫中大红人。
细一看,他虽含笑而立,那面色却有些苍白,眉间悬着忧。
“公公……”归晚先在几案一旁坐下了,玲珑乖巧,早已在一旁拿过椅子,待德宇坐下,身子还没稳,一杯清气四溢,浅香萦然的碧螺春已经递到了德宇身旁。
德宇拿过热茶,却没有触口,一转手,放回了几案上,微低着头,想说话又难开口的样子。过了半晌,终是耐不过这份外的静,一张口,声音低中带着哑:“夫人,你可知道舒氏?”
又是“舒氏”……“公公怎么对这南方望族感起兴趣了?”不答反问,探着德宇的话外音。
摇了摇头,拿过茶,一饮见底,润了润嗓子,德宇才又开口:“夫人也许不知,舒氏家族端的厉害,”说到这,也许是想不到好的形容,他顿了顿,迎上归晚疑惑的眼神,稍理头绪,续说道,“皇上曾出宫一天,就是在相府芍药花会之日,到日落之时才回到宫中,随行回来的,还多了一个人。皇上召他谈了足有一日,从那之后,此人就暗地为皇上出谋划策,皇上不能做的事,也借他的手去做。他行踪不定,又得皇上特赦,我费了些时日才查出来,他是舒氏子弟,听闻叫舒豫海。”
听到这名字,归晚心蓦地一凛,眉轻蹙:“舒豫海?”
舒氏的子弟,一个到相府,一个到皇宫,行事诡秘,其后深意难测,看到是野心勃勃,有备而来。楼澈应该看得出这点,皇上也不糊涂,只是这其中厉害关系牵扯不清,他们都想利用舒氏,身居高位,有许多事不能放手为之,有了舒氏,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可以借手为之。
一人之力有限,家族之力无穷。
“公公今日来就为了这舒氏家族的事吗?”
德宇抬起眼,突然从椅上站起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归晚面前,隔着几案,归晚微诧,忙不迭也起身,想要伸手扶起他,却被他一个沉重眼神压了回去。德宇的神情透着点肃穆,远看萧索,近看,那似乎是天堑下的巨石,千百斤的沉重。
“夫人,都是我不好,管教的小太监嘴巴不严实,把你的事透露给了舒豫天,这舒氏狡诈,一心为谋权,只怕他们会把主意打到你身上来,我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妥,今日特来请罪。”话音落,低低的伏着身,他跪在几案前不作声。舒氏的行动力比他想象得还快,舒豫天向楼澈进言已是好几日前的事,这点,德宇自是不知内情了。
归晚先是有些讶意,而后悠淡一笑:“公公不必这样,这天下间这么多张嘴,管也管不过来,小太监误事,跟公公没有关系的。”对着玲珑使了个眼色,玲珑立刻上前搀扶德宇。
谁知德宇依然纹丝不动地跪着,只是苦笑着摇头。他独在宫中寂寞,无以排遣,一日酒醉之后将泄露了皇上和归晚些许事,被小太监听去,这才恰巧透露给了舒豫海。事后,他懊悔无比,虽然将泄密的小太监暗地整死,却怎么也挽回不了既成事实,可惜这些话,他憋在心中,又如何敢对归晚说出。
见他跪在地方不肯起身,归晚也犯起难来,她一手把德宇拉进了这复杂的旋涡,害他身不由己,随之沉浮,现在他居然还为了她的利益安危,前来请罪,怎不让她心头震动,一时间竟无语可答,片刻后,归晚立到德宇宙身前,低身扶起他的臂膀:“公公,到底是我欠你多些,还是你欠我多些,你如此跪着,是要与我算清楚吗?”
德宇微愣,这才站起身,心头的大石放下,忧色减轻,退后几步,对着归晚细看了几眼,须臾之后,茶已渐凉,他开口:“夫人,请你多加防范舒氏,我不能多逗留,这就告辞。”
知道他身份特殊,的确不宜在此停留,归晚颔首,看着他恭敬地躬身一礼,就在他转身之际,忍不住唤:“德宇公公。”
“夫人还有吩咐?”
“今日公公是私自出宫吗?”
听到这句话,德宇身躯稍怔,心头暖流潺潺流过,知道归晚这句话在关心他的安危,怕他因为私自出宫担上关系,背对着归晚,他也能想像,她此刻必是浅笑如新月之弯勾,眸如夜,藏着如许的醇色,灿如星辰。
“夫人请放心,今天出宫是有公事,不会有纰漏。”头不回,他抛下话语,就这样走了,正如他来时一样,掠入暮色中,玲珑忙紧跟而出。此时谁也不知道,德宇今日的暗访,是最后一次见到归晚,这样的不回首,在日后,竟成了一种遗憾。
等人影完全消失,归晚收回眼光,坐回原位,心绪有些不安宁,她站起身,来回在房中踱了两圈,这不安却越积越大。瞻前顾后地细细一想,她吟然轻叹,拿出笔墨,就着几案写下两封信。
第一封信,是写给三娘,信中嘱咐其盯住南方舒氏,如果舒氏有任何针对相府的行动,请三娘全力对付舒家。
第二封信,是写给兄长余言禾,晋阳离舒氏家族的根基极近,归晚在信中请求兄长,在舒氏权势过大之时,不需顾及,直捣黄龙,务必要铲除舒家。
这个时候,归晚已经看出了舒家的狡诈手段,想在皇上和楼澈的争斗中占便宜,以这个为契机,做为家族上位的基石。
皇上和楼澈的斗争,她揣着明白当糊涂,因为这是男人的天下,这场争斗,不允许别人的插手。她只能默默地陪着楼澈,在他闲暇之余,一盘棋,一杯茶,清风遐迩,伴君盈然一笑。
在这份表面平静中,她不允许有人在暗地里阻挠甚至伤害相府的利益,即使只看到一点预兆,她也要在其行动之前将其扼杀。
看着墨迹未干的书信,她轻轻折起,放入信封,递到蜡烛旁,看着烛泪一滴滴地在信口封住,她的不安,她的惆怅,似乎也在这炙热烛泪中尘封住了……
即使归晚如此聪慧,也没有料到,她这两封信还是晚了一步。
历史的转动不会停留,就算机关算尽,欠缺了天时,地理,事情终难成功。历史里轻轻一笔,带过了无尽的心酸和无奈,又有多少肉眼所不及的努力在慢慢酝酿,是德宇暗访的忠诚,是归晚夜书的心计,还是楼澈运筹帷幄的布局……
天载四年,中秋之时,明月高悬空中,月辉倾洒大地,就在归晚的两封信送出相府的同时,别处发生了一些改变后来党争结果的大事。
玉督(二)
天载四年秋末,下相城门下。
夜幕低垂,暗夜无光,风呼啸而过,簌簌生冷,一个穿着厚重锦衣的男子站在城门口,抖缩着身子来回打着转,一边不停地搓着双手,不时地往大路张望,呼吸间吞吐着淡淡白雾。
“师爷,来了,来了!”微弱朦胧的光亮快步靠近,一个守城门的官兵小跑着靠近,手中灯笼忽明忽暗,在黑夜中显得虚渺不真。
听到小兵的话,师爷的精神为之一振,挺直了身躯,视线锁着前方。果不其然,一会儿工夫,马车辘辘声渐近,径直来到城门口停下。师爷连忙迎上前去,躬着身子:“大人,路途辛苦了。”
“张师爷,我不在的时候,城里还好吧?”车帘掀起,一个略显胖的身影在官兵搀扶下跳下马车,狐裘裹身,满脸疲惫,右手揉着酸疼的脖颈,左手上捏着一个梨木盒子。
“大人,一切安好。”
“恩。”身为下相的太守,第一句话只不过是官面话,下相是南方富裕之乡,民生安乐,想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他含糊地应了一声,下了车,顿时感到寒气逼人,嘟囔着,“今年这天还真反常,这会儿就这么冷了。”
首城的小兵去安顿马车,师爷紧跟在太守之后,轻声问:“大人此次进京拜见楼相,想必大有收获。”
“恩,事情紧急,这段时间京城局势紧张,相爷那边催得紧,”对着自己的心腹师爷,太守见四下无人,坦言,“相爷要南方连成一线,只要一致反对,中书院计划就不能成,如果让皇上把中书院给办了,起用那些近臣,那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好果子吃。你看,这是相爷亲笔书信,等明儿一早,给其他几位大人过目。”肥胖的手轻轻拍拍盒子,太守有些得意。
他是楼澈在南方重用的官员之一,深得器重,靠南有南郡王的维护,在京有楼澈的照拂,近些年来,为楼澈巩固南方势力献了不少功,春风得意,官场亨通,自是身宽体胖,一笑起来,脸旁的肉还会抖动。
“大人明智,等楼相独揽大权,大人腾飞之时,还要多多提携小人啊。”嘴上恭维着,师爷和太守都是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
两人走向城门,太守絮叨着进京所遇之事:“要说这京城什么都比下相好,但是这京城的美人啊,不够温柔,哪及得上下相的女子婉丽多情啊,”话音一顿,看着师爷听得津津有味,他又道,“话说回来,有一个例外——楼相的夫人,那可乖乖不得了啊……绝代佳人,也只有这样的佳人,才配得上楼相啊。”那日在院中一瞥,隔得甚远,他连楼夫人什么模样都没看清,但是那芙蓉含初露的风华,即使身处簇簇花团中,依然让人感到目眩,惊艳一瞥,难以忘怀。
两人说说笑笑,走进城门,师爷回过头来,正要指使着官兵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