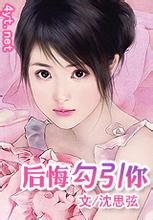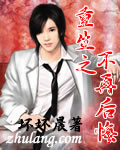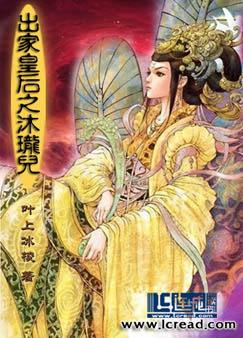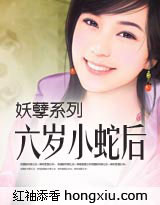诚信的背后-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我命名的〃FP 信托〃仍然在支付利息。尽管我不再了解这笔交易的具体信息,我还是在我的日历上记下了信托的到期日,2009 年 7 月 1 日。届时我肯定会留心新的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的话,日本的第四大证券经纪公司,山一证券,在 1997 年底突然因为所谓的〃表外事件〃亏损倒闭了。同年 11 月,另外两家日本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洋证券也垮台了 11 月不是一个幸运的月份。
山一证券在 1997 年底成立了一个衍生产品自营部,短短一年之后就公告了二十亿美元的亏损并宣布破产。美林证券立刻冲进来聘请了山一最好的经纪人,他们的衍生产品交易员也是供不应求。不等你说完〃表外事件〃几个字,日本第四大证券经纪公司就土崩瓦解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表外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一家公司能够把致公司于死地的
〃风险放在资产负债表的〃表外〃,那资产负债表还有什么用处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衍生产品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还有其他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
不过,我发现了另一家日本公司衍生产品亏损的一些答案。这个案例在美国没有被大肆报道,事主是乳酸制品生产商益力多会社公司。益力多的总部在东京,有点儿象雅芳(化妆品直销公司)和天使冰王(美国的一家乳酸制品公司)的混合体。益力多和雅芳一样,发动中年妇女上门直销它的产品,区别只在于益力多女士穿的是绿色(而不是粉色)外衣,推的是绝缘车(而不是化妆箱)。益力多的产品和天使冰王的一样,都是发酵牛奶制成的健康饮品;不过在我看来它的主打饮品远远不如天使冰王。益力多饮品是浅粉色的酸甜口味饮料,富含助消化的乳酸菌。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也和雅芳、天使冰王类似:低成本、高质量、高销量。这是个成功的计划,六十多年来益力多饮品在日本的销量稳步上涨,在海外市场也占有稳定的份额。
但是从八十年代起,益力多开始在它的配方里加进了复杂的金融材料,从而偏离了擅长的主业。当时日本的经济繁荣,市场节节向上,饮料的销售也屡创新高,益力多的现金极为充裕。公司决定开始运作一个名为〃特权信托〃的特别基金。那时很多日本公司都成立了类似的信托,投资股票或其他金融产品。特权信托最大的优势是公司无须每年申报信托的利润,因此也无须纳税。
特权信托在八十年代给益力多带来了双重收益:它的投资回报丰厚,而且没有缴纳任何利税。投资收益在信托里不断积累,却不用申报披露。然而,九十年代初日本的〃经纪泡沫〃破裂后股市也随之大跌,设立了特权信托投资的公司受到了沉重打击。骤然之间,这些公司都因为信托投资遭受了重大亏损,但是它们却不愿意关闭信托,实现亏损。随着损失的加剧,这些公司面临着两种选择:解散信托实现亏损;或是继续利用信托进行高风险的赌博,同时祈祷新的投机能够弥补以往的亏损。益力多选择了后者。1991 年,它不顾一切的采取了变本加厉的策略。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益力多的策略是个秘密,但是少数衍生产品业内部人士却很了解益力多的特权信托亏损,还有它谋求翻本的策略。怪事发生了:益力多成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大户。有个分析师后来回忆说,〃很早以前我们就都知道早晚会有重大的亏损要宣布。〃事实上,益力多早在 1996 年就悄悄的宣布了一笔相对不大的衍生产品亏损,大约四千万美元。1998 年 3 月 20 日,益力多公告了至少八亿一千万美元的亏损,原因是过去四年未经披露的衍生产品交易。公司的股票当天(星期五)就从八百二十日元急跌到了六百
二十日元,成交量也创出了天量。一家生产乳酸的公司怎么能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将近十亿日元呢?答案至今还不清楚。更为奇怪的是,对亏损额的估计不断变化。最初,全部八亿一千万美元亏损都来自衍生产品交易,后来又说衍生产品直接造成的亏损只有大约五亿美元;到了五月,这个数字又反弹到了七亿一千万美元。每过一个月左右,数字就要修正一亿美元,我不知道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显然,非衍生产品亏损是传统的信托和证券投资造成的。不知何故,看到还有这样过时的投资亏损竟然让人感到安慰。就算我们接受最保守的估计也无法消除疑问:一家生产乳酸的公司怎么能在衍生产品上损失了五亿日元呢?
益力多的日本股东以为他们投资的是一家乳酸饮品公司,就像宝洁的股东以为他们投资的是一家洗涤剂公司一样。他们全都错了,出其不意的发现他们投资的公司在利率和外汇上的豪赌。益力多的股东比宝洁的股东还要损失惨重,他们平均损失了一半的投资,而且很可能无法通过诉讼得到任何补偿。相比之下,宝洁的股东就幸运多了 信孚银行同意以将近二亿美元的代价庭外和解,这一数字符合衍生产品纠纷中投资银行一般支付索赔总额的百分之四十至七十达成和解的惯例。(案件对宝洁有利,证据中包括信孚银行的录音带,其中的一个经纪说:〃这些交易就象俄罗斯轮盘赌,每做一笔交易就等于又加了一颗子弹。〃)
益力多的雇员也没好到哪儿去。公司宣布计划裁员三百人,削减管理层薪酬百分之二十,甚至暂停向董事发放奖金。实际上,暂停董事奖金的计划只执行了一年。了解益力多交易内幕的银行家说它在一系列含有日经指数期权的结构性票据中判断失误。另外的消息说益力多的交易包括日经指数掉期和外汇掉期。还有报道说益力多的损失是因为看错了利率走势。准确的交易情况没有被公开,但不管真正的原因何在,益力多肯定很难向那些推小车的绿衣女士解释清楚她们为什么丢了工作。根据日本的传统,益力多把损失归罪于一个人,副总裁熊谷直地。大多数交易决策都是他做的,而且除他之外似乎没有人理解这些交易。也是他告诉益力多的董事要坚持,投资最终总会解套(或者只是他的愿望?)现在看来,熊谷本人是否理解这些交易也是个问题;无论如何,他立刻引咎辞职。益力多的董事长紧随其后。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日本财政部有个官员因为受贿而负罪自杀,益力多的这两个人倒没有步他的后尘。益力多事件还有一个文化插曲:这家乳酸公司还有一支棒球队,益力多燕之队。幸运的是,巨额衍生产品亏损并没有影响这支日本联赛冠军队。益力多的亏损正好是在那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前公告的,燕之队的领队酒井清人在比赛前一天向队员保证益力多不会出卖他们。球员的担心不无道理,燕之队一线球员平均每年赚四千九百六十八万日元,大概等于五十万美元。在东京这个水平刚刚超过贫困线,和美国的高薪棒球员相比更不值一提 加瑞谢菲尔德 1998 年一年的收入就和十亿多日元。
如果专家们说得不错,益力多的亏损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长期以来对日本所谓的〃金融大爆炸〃 即放松监管的改革计划持怀疑态度。益力多或许没有被亏损置于死地,但是它肯定不是唯一隐瞒衍生产品亏损的公司。衍生产品在日本的流行程度似乎和棒球不相上下,在游戏规则如此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日本的金融市场怎么能做到自由和公平呢?此时放松监管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美国本土也有不少公司深受衍生产品之苦,其中既有上一年新发生的亏损,也有 1994…95年衍生产品灾难的后遗症。最突出的连续故事非橙县莫数。它在 1994 年 12 月亏了超过十九亿美元,从那以后,该县千丝万缕的诉讼一直使加州律师协会的成员忙得不亦乐乎。截至1998 年中,橙县一共提出十五起诉讼,控告了二十八个被告,其中包括二十家华尔街公司。我的前雇主瑞银第一波士顿是第一家同意庭外和解的公司,支付了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此外第一波士顿和两个前雇员还支付了八十七万美元,作为在和橙县破产有关的债券发行中误导投资者的补偿。1997 年,为了确保橙县不对公司及其雇员提起诉讼,美林同意支付橙县三千万美元。美林还同意支付一百九十万美元与债券投资者达成和解。瑞银第一波士顿在同一个案件中付了九十九万美元。橙县坚持在民事诉讼中追讨摩根士丹利和其他的公司,联邦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1998 年 6 月,美林终于坚持不住了,支付了四亿美元的巨额和解费。在华尔街诉讼和解史上名列第五。还有牢狱之灾,橙县的前任财政官罗伯特塞荣被判罚款十万美元,监禁一年。不过在服刑八个月后,他于 1997 年 10 月被释放。塞荣的副手马修拉必被判监禁三年,不过到 1998 年 5 月,他还在上诉。1996 年,橙县从破产中东山再起,目前一切良好。很多其他诉讼也在庭外达成了和解。例如,普惠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同意向监管机构支付五十万美元罚款,原因是欺骗性的误导投资者普惠旗下基金的波动性;该基金投资按揭支持的衍生产品发生了重大亏损(普惠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一指控)。
然而,大多数衍生产品市场参与者积极活动的地方是市场而不是法庭。传言说德意志摩根建富在 1997 年夏天的亚洲市场暴跌中亏损了数千万美元;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 PNC 发生了一亿九千万美元的衍生产品亏损;1995 年宾西法尼亚州有七十多个学区投资于德文资本管理公司和金融管理科学公司,他们也损失了大约七千一百万美元。国民西敏寺银行高薪聘请了摩根士丹利的顶尖衍生产品人才,但是很快就蒙受了一亿二千万美元的利率期权交易亏损。瑞士联合银行也亏损了好几亿美元,幸亏他们卖的及时,不然要亏损几十亿。
监管者指控一些交易员利用期权操纵股票指数,包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伦敦金融时报 100 指数。国会、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还有众多强硬派的审计师也攻击了衍生产品交易披露的匮乏。
同时,寻求 AAA 信用评级的交易也越来越多。遵循九十年代中期的抵押债券(CLO)交易模式,几家银行完成了规模庞大的 CLO 交易(利润当然也十分巨大)。似乎没有人为这些交易的高费率而担忧。某家主要衍生产品公司的律师的解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巨额佣金压榨客户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利润完全不为人知;但是向客户销售爆炸性的衍生产品是不对的。〃重要的教训是:压榨是好的,爆炸是坏的。
拉丁美洲衍生产品市场也得到了复兴,不过这一次比九十年代初时主流得多。墨西哥银行经历了另一场收购兼并的狂欢;阿根廷发行的债券也漂亮多了;巴西的货币既然已经稳定,复杂的通货膨胀指数也就没用了。1998 年 5 月,整个拉丁美洲都有了活跃的期权和期货市场。
衍生产品的佣金肯定没有下降。实际上,我在这个问题上只触及了皮毛,低估了衍生产品创造的利润。有些交易员认为我也被人误导,居然误以为摩根士丹利是这个领域的〃玩家〃。有个对冲基金顾问对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部两年里间赚的十多亿美元不屑一顾,他说在衍生产品业〃摩根士丹利不过是另外一个输家〃。他在 1997 年 11 月的《衍生产品策略》杂志上对我的结论(摩根士丹利赚了很多钱)做出了相当非同凡响的评论:〃他以为的很多钱其实根本不是很多钱。他以为有五千万美元就算有钱人了,这个世界上有五千万美元的人多了!一年赚六百万美元不足为奇,对冲基金光是为了记录仓位也要付给账户管理人这么多钱。〃七位数的年薪算不算惊人要靠你自己来决定,不过据我所知,美国典型的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没有六百万美元。
不止是佣金,衍生产品的交易量也上升了。衍生产品经过了几年的黑暗,现在又恢复了名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个高级管理人最近的结论是〃衍生产品不再是肮脏的字眼了。〃根据国际掉期和衍生产品协会的数字,1997 年传统的利率和外汇衍生产品交易量上升了大约百分之五十。长期处于困境的信用衍生产品业务同年增长四倍,达到了四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近期行业内的合并也致力于复杂衍生产品的协同效应,一般是衍生产品重量级和轻量级的结合。每天都有更新奇的产品出现:共同基金期权、房地产期货、天气衍生产品(没错,是天气 有些人赌气候的变化和趋势)。衍生产品又强力回归了。
我对国内衍生产品造成的收益和亏损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我肯定我的遗漏多多,又一次〃只触及了皮毛。〃但是你了解了基本的情况。
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似乎也受到了启发,终于正式通过了法规,强迫上市公司披露拥有的衍生产品种类和风险,尽管还是给予公司很大的自主权避免披露某些信息。有上市公司对此投诉,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利维特指出有研究表明全国的监管成本预计在四千万美
元,而他曾经担任董事的一个慈善基金曾经由于基金经理误用衍生产品损失了三千万美元。我们的最高证券监管者终于看到了这个深渊,这至少可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安慰。
摩根士丹利与添惠公司合并后的新公司在无数统计栏目中都名列前茅。可是在 1998 年初衍生产品龙虎榜上,它的排名只是区区第六,远远落后于死对头高盛公司。为什么摩根士丹利的衍生产品业务不能象其他业务一样拔得头筹呢?公司作为衍生产品大户的声望似乎日益下降,而近来几起针对摩根士丹利的诉讼自然也无益于公司为恢复形象作出的努力。摩根士丹利的网站虽然明确的把衍生产品列为公司的特长之一,却没有提及公司在法律诉讼中同样显著的地位。尽管我茫然不知,监管当局掌握的材料却显示,1995 年 3 月,就在我考虑离开公司的同时,七个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