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 -史蒂芬.霍金-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姑娘定婚。
我邂逅她之时大约便是诊断得了运动神经细胞病前后。这就使我有了一些活头。
但是为了结婚,我需要一个工作,为了得到工作,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此在我的一生中首次开始用功。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喜欢研究。也许把它称作工作是不公平的。有人说道:科学家和妓女都为他们喜爱的职业得到报酬。
我向龚维尔和凯尔斯(发音作基斯)学院申请研究奖金。我希望简能为我的申请表打字,可是当她来剑桥看望我时,她的手臂因为骨折打上石膏。我必须承认,我应对她更为体贴才对。还好,她是伤了左臂,所以她还能按照我的口授填好该表,我再请另外的一个人打字。
我在申请时列入两个人的名字作为我的推荐人。我的导师建议我请赫曼·邦迪作为其中之一。邦迪那时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学教授,他是一名广义相对论专家。我见过他两回,他还为我提交过要在《皇家学会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他有一次在剑桥演讲后要求此事,他以迷惑的眼神凝视我,然后答应说可以。他显然遗忘了我,因为当学院写信问他时,他回答说没有听说过我。现在,有这么多人申请学院的研究奖金,如果候选人的推荐人中有一人说对他不了解,他也就不会有机会了。但是那时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学院写信通知我这推荐人的难堪的答复,而我的导师到邦迪那儿去使他回想起我来。邦迪后来为我写了一封也许溢美的推荐信。我如愿得到了研究奖金,从此以后一直是凯尔斯学院的研究员。
我在得到了研究奖金后才得以和简在1965年7月完婚。我们在苏福克渡了一周蜜月,这是我们仅能负担的。后来我们去了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举行的广义相对论暑期班。这是一项错误。我们住的宿舍充满了带着哭闹小孩的夫妻,这使我们的婚姻生活不甚愉快。但在,这个暑期班在其他方面对我们非常有益,因为我结识了许多在该领域的头面人物。
直至1970年止我的研究集中于宇宙论,也就是在大尺度上研究宇宙。这个时期我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奇性。对遥远星系的观测表明它们正远离我们而去:宇宙正在膨胀。这说明在过去这些星系必然更加相近。这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是否有过产个日寸刻,所有星系都相互重叠在一起,而宇宙的密度是无限的?或者早先是否存在一个收缩相,那时在这个收缩相中这些星系想法避免相互对撞?也许它们相互穿越,然而再相互离开。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数学技巧。这些就是在1965年和1970年之间主要由罗杰·彭罗斯和我自己所发展的。彭罗斯那时在伦敦的比尔贝克学院,现在他在牛津。我们用这些技巧来证明,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话,则在过去必然存在过一个无限密度的状态。
这个无限密度的状态被叫作大爆炸奇性。它意味着,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则科学不能预言宇宙是如何启始的。然而,我更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人们考虑到量子物理理论,这个有关非常小尺度的理论,则可能预言宇宙是如何启始的。
广义相对论还预言,当大质量恒星耗尽其核燃料时将会向自身坍缩。彭罗斯和我证明了,它们会继续坍缩直至达到具有无限密度的奇点。至少对于该恒星以及在它上面的一切,这个奇点即是时间的终点。奇点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甚至光线都不能从围绕它的区域逃逸,它被引力场拉回去。不可能从该处逃逸的区域就叫做黑洞,黑洞的边界叫做事件视界。任何通过事件视界掉进黑洞的东西或人都在奇点达到其时间的终结。
1970年的一个晚上,当我要上床之时思考黑洞的问题,那是我的女儿露西诞生不久的事。我忽然意识到,彭罗斯和我发展的用于证明奇性的技巧可以适用于黑洞。特别是,黑洞的边界,即事件视界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小。而且当两颗黑洞碰撞并合并成一颗单独的黑洞时,最终黑洞的视界面积比原先两颗黑洞的视界面积的和更大。这就为黑洞碰撞时可能发射的能量立下了一个重要的限制。那个晚上我激动得难以入眠。
从1970年到1974年我主要研究黑洞。但是在1974年我也许做了毕生最令人吃惊的发现:黑洞不是完全黑的!当人们顾及物质的小尺度行为时,粒子和辐射可以从黑洞漏出来。黑洞正如同一个热体似地发射辐射。
1974年之后,我从事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合并成一个协调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结果便是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他巴巴拉分校的詹姆·哈特尔在1983年提出的一个设想: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范围上都是有限的,但是它们没有任何边界。它们像是地球的表面,只不过多了两维。地球表面具有有限的面积,但是没有任何边界。在我的所有旅行中,我从未落到世界的边缘外去。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就不存在奇性,科学定律就处处有效,包括宇宙的开端在内。宇宙启始的方式就完全由科学定律所确定。我也就实现了发现宇宙如何启始的抱负。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启始。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 三、我的病历“2”
人们经常问我:运动神经细胞病对你有多大的影响?我的回答是,不很大。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 “2”作者注:这是1987年10月在伯明翰召开的英国运动神经细胞病协会会议上的发言稿。
我被发现患了运动神经细胞病,这对我无疑是晴天霹雳。我在童年时动作一直不能自如。我对球类都不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在乎体育运动。但是,我进牛津后情形似乎有所改变。我参与掌舵和划船。我虽然没有达到赛船的标准,但是达到了学院间比赛的水平。
但是在牛津上第三年时,我注意到自己变得更笨拙了,有一两回没有任何原因地跌倒。直到第二年到剑桥后,我母亲才注意到并把我送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他又把我介绍给一名专家,在我的二十一岁生日后不久即入院检查。我住了两周医院,其间进行各式各样的检查。他们从我的手臂上取下了肌肉样品,把电极插在我身上,把一些放射性不透明流体注入我的脊柱中,一面使床倾斜,一面用X光来观察这流体上上下下流动。做过了这一切以后,除了告诉我说这不是多发性硬化,并且是非典型的情形外,什么也没说。然而,我合计出,他们估计病情还会继续恶化,除了给我一些维他命外束手无策。我能看出他们预料维他命无济于事。这种病况显然不很妙,所以我也就不寻根究底。
意识到我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并在几年内要结束我的性命,对我真是致命打击。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地夭折呢?然而,住院期间我目睹在我对面床上一个我稍微认识的男孩死于肺炎。这是个令人伤心的场合。很清楚,有些人比我还更悲惨。我的病情至少没有使我觉得生病。只要我觉得自哀自怜,就会想到那个男孩。
不知什么灾难还在前头,也不知病情恶化的速率,我不知所措。医生告诉我回剑桥去继续我刚开始的在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我的数学背景不够,所以进展缓慢,而且无论如何,我也许活不到完成博士论文。我感到十分倒楣。我就去听维格纳的音乐。但是杂志上说我酗酒是过于夸张了。麻烦在于,一旦有一篇文章这么说,另外的文章就照抄,这样可以起耸动效应。似乎在印刷物上出现多次的东西部必定是真的。
那时我的梦想甚受困扰。在我的病况诊断之前,我就已经对生活非常厌倦了。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我出院后不久,即做了一场自己被处死的梦。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被赦免的话,我还能做许多有价值的事。另一场我做了好几次的梦是,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其他人。毕竟,如果我总是要死去,做点善事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没死。事实上,虽然我的将来总是笼罩在阴云之下,我惊讶地发现,我现在比过去更加享受生活。我在研究上取得进展。我定婚并且结婚,我还从剑桥的凯尔斯学院得到一份研究奖金。
凯尔斯学院的研究奖金及时解决了我的生计问题。选择理论物理作为研究领域是我的好运气,因为这是我的病情不会成为很严重阻碍的少数领域之一。而且幸运的是,在我的残废越来越严重的同时,我的科学声望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人们准备给我许多职务,我只要作研究,不必讲课。
我们在住房方面也很走运。我们结婚的时候,简仍然是伦敦的威斯特费尔德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所以她周中必须上伦敦去。因为我不能走很远。这就表明我要找到位于中心的能够料理自己的地方。我向学院求助过,但是当时的财务长告诉我,学院不替研究员找住房。我们就以自己的名义预租正在市场建造的一组新公寓中的一间。(几年后,我发现这些公寓是学院所有的,但是他们没有告知我这些。)当我们在美国过完夏天返回剑桥之时,这些公寓还未就绪。这位财务长作了一个巨大的让步,让我们住进研究生宿舍的一个房间。他说:“这个房间一个晚上我们正常收费十二先令六便士。但是,由于你们两个人住在这个房间,所以收费二十五先令。”
我们只在那里住了三夜。然后我们在离我大学的系大约一百码的地方找到一幢小房子。它属于另一间学院的,并租给了它的一位研究员。他最近搬到郊区的一幢房子里,把他租约还余下的三个月分租给我们。在那三个月里,我们在同一条街上找到另一幢空置的房子。一位邻居从多塞特找到房东并告诉她,当年轻人还在为住宿苦恼时让她的房子空置是太不像话。这样她就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年后,就想把它买下并作装修,我们向学院申请分期贷款。学院进行了一下估算,认为风险较大。这样最后我们从建筑社得到分期贷款,而我的父母给了我装修的钱。
我们在那儿又住了四年,直到我无法攀登楼梯为止。这时候,学院更加赏识我并且换了一个财务长。因此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学院拥有的一幢房子的底层公寓。它有大房间和宽的门,对我很合适。它的位置足够中心,我就能够驾驶电动轮椅到我的大学的系去。它还为学院园丁照管的一个花园所环绕,对我们的三个孩子也十分惬意。
直到1974年我还能自己喂饭并且上下床。简设法帮助我并在没有外助的情形下带大两个孩子。然而此后情形变得更困难,这样我们开始让我的一名研究生和我们同住。作为报酬是免费住宿和我对他研究的大量注意,他们帮助我起床和上床。1980年我们变成一个小团体,其中私人护士早晚来照应一两小时。这样子一直持续到1985年我得了肺炎为止。我必须采取穿气管手术,从此我便需要全天候护理。能够做到这样是受惠于好几种基金。
我的言语在手术前已经越来越不清楚,只有少数熟悉我的人能理解。但是我至少能够交流。我依靠对秘书口授来写论文,我通过一名翻译来作学术报告,他能更清楚地重复我的话。然而,穿气管手术一下子把我的讲话能力全部剥夺了。有一阵子我唯一的交流手段是,当有人在我面前指对拼写板上我所要的字母时,我就扬起眉毛,就这样把词汇拼写出来。像这种样子交流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写科学论文了。还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名叫瓦特·沃尔托兹的电脑专家听说我的困境。他寄给我他写的一段叫做平等器的电脑程序。这就使我可以从屏幕上一系列的目录中选择词汇,只要我按手中的开关即可。这个程序也可以由头部或眼睛的动作来控制。当我积累够了我要说的,就可以把它送到语言合成器中去。
最初我只在台式计算机上跑平等器的程序。后来,剑桥调节通讯公司的大卫·梅森把一台很小的个人电脑以及语言合成器装在我的轮椅上。我用这个系统交流得比过去好得多,每分钟我可造出十五个词。我可以要么把写过的说出来,要么把它存在磁碟里。我可以把它打印出来,或者把它召来一句一句地说出来。我已经使用这个系统写了两部书和一些科学论文。我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和普及的讲演。听众的效果很好。我想,这要大大地归功于语言合成器的质量,它是由语言加公司制造的。一个人的声音很重要。如果你的声音含糊,人们很可能以为你有智能缺陷。我的合成器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最好的,因为它会抑扬顿挫,并不像一台机器在讲话。唯一的问题是它使我说话带有美国口音。然而,现在我已经和它的声音相认同。甚至如果有人要提供我英国口音,我也不想更换。否则的话,我会觉得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我实际上在运动神经细胞病中度过了整个成年。但是它并未能够阻碍我有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我要十分感谢从我的妻子、孩子以及大量的朋友和组织得到的帮助。很幸运的是,我的病况比通常情形恶化得更缓慢。这表明一个人永远不要绝望。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 四、公众的科学观“3”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过去一百年间遭受到剧烈的变化,看来在下个世纪这种变化还要更厉害。有些人宁愿停止这些变化,回到他们认为是更纯洁单纯的年代。但是,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过去并非那么美好。过去对于少数特权者而言是不坏,尽管甚至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医药,妇女生育是高度危险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肮脏、野蛮而短暂的。 “3”作者注:这是1989年10月在西班牙奥维多接受阿斯特里乌斯王子协和奖金时的讲演。此文作过修订。
无论如何,即便人们向往也不可能把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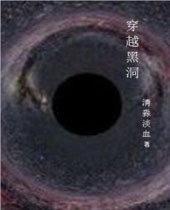
![[绿杨] 黑洞之吻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