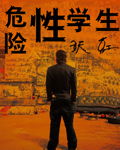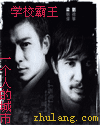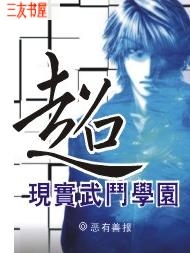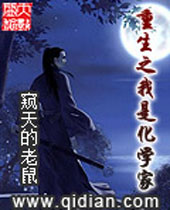逝去的大学-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让你顿增光彩。”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地,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
他本来应该一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的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5、6月的一个下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作者简介:
陈远,1978年生。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近年来关注于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化生态。现供职于某报社。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1)
文/《陆志韦传》编写小组
陆志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心理学开创者之一。1894年2月6日,陆志韦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旧称乌程县)南浔小镇,1937年“七七事变”后,研究心理学的条件受到限制,他转而从事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1952年后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研究语言学,成
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
陆志韦先生为人正派、学识渊博,为教育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才干无法充分发挥,身心受到损害,1970年不幸去世。1979年,党和国家为其恢复了名誉。
1926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正担任着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路过南京时看望陆志韦先生。在陆家,他们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而且特别谈到了燕京大学的发展鸿图。那时,燕京大学刚从北京城里的盔甲厂迁到西郊的海淀,学校的局面亟待展开。司徒雷登发现陆志韦先生正是他办学事业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流露出拟邀请陆先生北上燕京大学执教的想法。
1927年4月5日,陆志韦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时年33岁。
那时燕京大学校园还在大兴土木。建筑师们在未名湖西南岸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校园主体建筑群的模型,供有关人士参观提意见。贝公楼、穆楼和睿楼已建成,而适楼、姊妹楼(也就是甘德阁和麦风阁)还在施工中,燕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水塔已建成(那时叫博雅塔),它采用了中国密檐式佛塔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一座供水用的高位储水塔。塔影倒映在未名湖宁静的水面上,堪称京西一景。钟亭也修成了,一口明代的大铜钟悬挂在亭中央,每隔半小时敲响一次的钟声,总是那么深沉而浑厚。校工周大爷每到该打钟前的5分钟,就拎着个马蹄表从贝公楼东门出来走到钟亭,看着表,差几秒钟就举起锤来,准时敲下去。燕园的生活就像这钟声那么稳重、准时,似乎人们所称道的燕大效率,就是由这位和蔼认真的老校工掌握着的。
陆先生来到燕园时,燕园的建设方兴未艾,燕京的教育事业前景开阔。对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说,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燕京大学的心理学系尚在初创阶段,基础较为薄弱。陆志韦先生到校之后,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系里拥有一个有上千册心理学专业书籍的图书室、两间心理实验室、一个实验动物饲养间、一间暗房和一间隔音室。这些都是讲授科学心理学所必须的,在当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先进科学水平装备的系科了。
现代心理学是现代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脱离哲学的母体只有几十年短暂的时光。人们常常误认为现代心理学是神秘的、唯心的或不科学的,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如此。陆志韦先生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西方的现代心理科学引进到我国的教学中来的。
陆志韦先生到了燕京大学之后,除了为创建心理学系而努力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校园内的其他社会活动,深受燕京大学教职员同事们的爱戴。1928年他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的主席,曾多次为谋求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而仗义执言,与校方力争。
陆志韦先生是一位涉猎面极广的学者。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知识面甚广。到燕京大学执教之际,他已经是一位在心理学方面有不少著述、在学术界知名度相当高的学者了,故在当时心理学界,有“南潘①北陆”之誉。30年代他所讲授的“系统心理学”课程,被认为是在国内仅有的。他在国际心理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地位。
陆志韦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庄重严肃,其实,他也常常十分幽默。在心理学系的实验室里,饲养着几十只小白鼠。这是供研究实验用的,饲养费用由哈佛燕京学社供给。白鼠是舶来品,它们的饲料也是舶来品,其中就有美国的克宁奶粉。沈道璋先生曾在做实验时说:“这小东西比人还贵族!”说着用小匙舀了点奶粉放进自己嘴里。陆先生笑着说:“你也是小耗子了!”还有一次,心理系的师生在用迷路箱(Maze)测试小白鼠的学习曲线。从下午2点开始,一般的情况只需6小时左右小白鼠就能到达终点。可是这次到了晚上7点钟,它还没走完一半路程。陆先生来看时,笑着对参加实验的几个人说:“可能这小耗子不够饿,没兴趣找东西吃!”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家里拿来几张葱油饼给没有吃饭、坚持做实验的人吃,说这是对他们忍饥的诱奖(Incentive)。
陆先生对打桥牌十分感兴趣,从500分、拍卖桥牌到定约桥牌都能玩,而且能耐心地教给初学者,经常约一些教师和同学到他家去玩。
1933年,陆志韦先生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心理学(主要内容是神经学技术),时年39岁。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里优越的实验室条件,他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紧张的研究与学习,1934年完成进修归国。
主持校务
陆志韦先生从美国途经上海抵达北平,才到家就听朋友说,司徒雷登已准备推举他当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
司徒雷登之所以要推举陆先生作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是因为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那年春天,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与司徒雷登在办学方面有不同意见,已经辞去了校长职务。这就需要物色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选,于是乎就遴选到陆志韦头上了。其原因,笔者估计大概有几点:第一,陆志韦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他是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的人,因此受政治上的动荡的影响会小些。第三,当时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常有派系之争,而陆志韦没有介入任何派系,一直处于超然地位。此外,他受的是美国的教育,是美国托事部或基金组织易于同意的人选;同时,他在洋人面前能替中国教职员工说话,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也能够被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所接受。就这样,1934年夏,陆志韦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时年40岁。
燕京大学当时由校长与校务长双重领导。校长之设立完全是为了应付国民政府关于教会学校要由中国人当校长的规定。而校务长的职务,则是为了向美国托事部和基金组织负责。校务长的英文名称叫President,校长的英文名称叫Chanellor。这两个字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大学的一校之长。不过在当时的燕大,学校实权主要掌握在校长手里。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2)
陆志韦先生答应只代理1年,可是事实上一代理就是3年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了北平后,他才中止了代理校长的职务,而由司徒雷登担任校务长和校长两个职务,以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扰。但是陆先生仍然要协助司徒雷登处理学校很多行政事务。
1934年陆志韦先生从美国进修回国后,本来打算继续深入生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学校经费短缺,无法创造条件来进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工作,他就只
好转而研究语言学方面有关心理学的问题了。正如他在所著《古音说略》一书的自序中说的:“由生理心理以知语言学之大要,由语言而旁涉音理,初亦无志于古音……”他对于儿童语言的研究、拼音文字的探索,以及对古诗音韵的研究等,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认为“两只耳朵一支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必跟着仪器走”。
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从陆志韦先生到燕京大学执教到1937年夏天为止的11年间,中国大地上始终战火连绵。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再以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块安静的乐土来供学者们致力于学术研究。
陆志韦先生代理燕京大学校长期间,日寇侵华日甚一日,政局多变,环境恶劣。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先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一贯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十分不满。他利用代理校长身份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