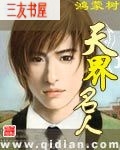名人演讲在清华-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使然,造成中国从土改,然后互助、合作、集体化,这几个步骤和中国追求工业化这个宏观环境的巨大改变有直接原因,什么原因?为什么陈云同志当年主张搞统购统销?是因为咱们土改之后,尽管农业生产有了很好的增长,你看那个曲线是这样的,陡着往上走的,农业产量在增加,但是供给在下降。这里边有个什么道理呢?你知道过去,解放前,没有搞土改之前,咱们说地主这个阶级是万恶的,他是剥削阶级,但他客观上起了什么作用呢?他收租,收了租他自己并吃不了那么多租,地主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他收的租,大体上能占到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地主消费只消费百分之七、百分之八,那他至少要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租子变成对市场直接供给的商品,所以他主客观上自发地起了一个规模供给者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和平年代,你靠谁来解决跟四亿高度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呢?所以当你的交易对象大到一个这么大的,数以亿万计的量的时候,交易成本空前推高,因此(粮食)供给上不去,尽管产量上去了,所以到1953年秋天的时候,陈云同志当时主管财经,他向毛主席、周恩来报告说是咱们粮食连过冬都难以保证,更别提春荒了,怎么办?当时考虑了八种到十几种的方法,最后选定了统购统销。你(搞)统购统销对的还是四亿农民,怎么解决呢?所以毛主席就发出号召组织起来,组织成四百多万个合作社,这个统购统销就跟合作社交易,交易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最初搞合作化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农业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当时工业化加速,你知道,1952年一上“一五计划”,咱们多少人进城吗?当时是二千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这一进城,因为大量需要挖土方、需要修马路、需要盖房子,工业化初期的那个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增加了二千万劳动力进城,而当时城市总人口才五千多万,所以突然增加了一大块对粮食的需求,当然就导致得解决(与分散农民)没法交易的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这么来的,绝对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造成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经济问题,我们就经济谈经济,把意识形态的那些解释,咱们先放一边儿,我们会看到很多当时的领导人,他们绝不比现在我们提问题的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说,我们要看当时的问题是什么,我是把那个时候的文件全部清理过来,发现我们所有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逐步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都)和工业化高度相关,尤其当你开始生产拖拉机的时候,你的拖拉机给谁?连这四百多万个合作社都不可能成为接受拖拉机的那种主体,对不对?我当队长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机来耕地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咱们又倒霉了。为什么呢?它得要多少麦子。我们其实使我们自己的牲口完全能耕得了那个地,为什么要拖拉机呢?我们农民当时是不需要的,是国家强迫给我拖拉机,那你没拖拉机行吗,没拖拉机没坦克,拖拉机摘掉上头放上炮塔就是坦克,你能不生产拖拉机吗?懂这个道理,其实不是毛泽东他不明白,他那么聪明的人,他能不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实事求是的去看当时的情况,更何况1956年开始中苏交恶,不会再有后续投资,你从哪儿来投资?重工业追加投资的比重是相当相当高的,每年没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的积累,中国能上得去吗?“两弹一星”怎么上天?靠重工业基础,中华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玩意儿,全世界都靠这些玩意儿在那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能免得了吗?你说靠我们农民就使锄头、镰刀,我们不使拖拉机,没你农民买拖拉机,就没有坦克,他得用卖拖拉机的钱去顶坦克,所以那个时候这套体制,自上而下的这么贯下来,让农民做出牺牲,要我们说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半代人,因为我们至少干了几年活儿,我们的牺牲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亏,我们应该是为民族做了牺牲,我们是骄傲的。
主持人:好,最后主持人阿忆要问您一个问题,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世纪之交谈三农问题,到底有怎样的重要性?
温铁军:我说中国是中国,它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变成一个特别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还得眼光向内,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话。
温铁军:对不起,太复杂,所以我没法儿一句话说完。
主持人:好,咱们就五句话结束。好,谢谢温铁军博士、谢谢现场观众。
致北京的年轻人
大江健三郎
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得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亚洲三位获奖者之一。也是继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之后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来中国访问的世界级文学大师。
“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天在清华向清华、北大师生发表正式演讲前,模仿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神态,用夹生的汉语说。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随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专程拜访曹禺。大江对曹禺说:“你写《雷雨》时在读大学,我也是在大学开始小说创作的。”
大江年轻时非常喜爱的《雷雨》,是曹禺在清华读书时创作的。创作地点正是大江今天演讲的地方――清华图书馆。
大江说,在曹禺当年创作《雷雨》的地方,与“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
大江以其“存在主义本土化”小说创作而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性的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学上的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此次访华前,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和随笔集。
大江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以及“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他正关心着三个问题: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三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存共生”的问题。他对日本“国家主义”倾向,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屠杀罪行的不忏悔,抱有警惕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是东京都市民的耻辱。”
他在清华图书馆的演讲题目是“致北京年轻人”:
致北京的年轻人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到了自己的小说中。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注点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足球》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