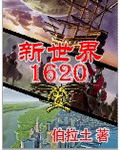16岁少女-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将近拂晓,我正水淋淋地在井底挣扎,突然被争吵声惊醒。外婆压低的嗓音在夜幕中显得苍老和可怖,像一只阴森的怪鸟;我顿时惊出一头汗。她在骂母亲,骂母亲心硬,容不得亲生女儿,把女儿推到不长五谷的地方去;母亲无力地争辩着,最后竟啜泣起来。她们两个为我大动干戈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次,我十分骄傲,由于那个决定,我一跃成为家庭明星。
外婆打开窗,匍匐在地,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她祷告的样子格外虔诚,满脸满身的月色使她显得圣洁。此刻,她刚烈精明的脸部突然充满慈爱。
外婆完全像个旧式妇女,可骨子里的冷傲却令她如一个女权主义者。外婆说过她父母爱她爱得发痴,一直养到三十岁方让外公续弦了去。外婆的婚姻先天畸形,她为早早歇了顶的外公生儿育女,烙守妇道;可她在心里蔑视这婚姻,仇恨女人的路。外公是个骄傲而又暴躁的人,容不得女人冷傲习性。母亲回忆过,说那时外公常疯了一般掀翻桌面,外婆则在一片稀里哗拉声中冷笑数声。我喜欢有这样悍泼的上代,我猜想那是冗长的闺房生涯带给她的烙印。后来外公一命呜呼,外婆据说没滴一点泪。丈夫之死造成了外婆的辉煌,她炒了盐炒豆,腌了萝卜,制成红丝绿丝,做起小本生意;抗战时这个小脚女人居然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干起贩米的勾当;一次正逢日本人搜捕,许多五尺高的汉子束手待毙,她竟跳人灭顶深的水池,并且泅出那鬼地方安全回到家,那里,她的儿女们正饥肠辘辘地盼望着她。
我欠起身子看那个匍匐着的前辈,她脑后那个紧巴巴的发誓滑散开,满肩是枯燥的乱发。我低声唤她一声,她不应,仿佛熟睡在清纯的月光中。我等了好久,她仍纹丝不动。我突然有点恐惧,怕她就这般宁馨地死去。我迅速地平躺在床上。许久,没有发生想象中可能发生的怪响:一个庞然大物发出僵硬的倒地声,随后,死神指使黑云遮住明月……
等我醒来,外婆已经带着漱口家什回南市了。我走到窗前,蹲在外婆祷告的地上。这样望天,天空又高又深奥。
那张户口迁移证明并没带给我多少震动,只是一纸抽象的印章;然而到了车运行李那天,我的衣物用具种种东西都被弄走,我才有一种拔掉老根的感觉。
、那天,郑闯的母亲搞来一部大卡车替她独子运行李,不知她是从什么渠道打听到我的,就跑上门来说把我的行李一起带上。这样,我跟郑闯头一次当着双方父母的面站在一起。郑闯有点腼腆,话不多,光用手摸头;其实母亲那天心清坏到极点,根本不会在意这个乳臭未干的男孩。我知道她将女儿高高捧着,择婿的要求必定极严,这样更好,能使我为爱情多绕些暗礁,反正早晚会扳回来的。
我原来见过郑闯母亲几面,那是个能干的胖妇人,有点咋唬。此刻,她显然是得到了什么暗示,对着我亲切微笑,并且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完全像个好脾气的婆婆。她又亲手在我一个大塑料包上加了几道麻绳,那个松松垮垮的行李霎间就变得坚挺多了。
郑闯的行李件件都是四四方方,而且一律新崭崭的。美妹说他家收入不高,但较有家底,这次卖掉一只罗莱克斯手表,用这笔钱将郑闯武装到牙齿。郑闯家的慷慨以及对他的重视,让我间接地感到温暖。
行李送至另外一所中学,待到安放好,司机率先走了。郑闯的母亲突然用胳膊挽住我,我推不得也让不得,只好别别扭扭地随她去。她老练地说东道西,仿佛已经默认了这门亲事。路过一家点心店,她强行拉我进去,郑闯立即心领神会地在边上找定三只座位。她买了馄饨和小笼包,殷勤地往我碗里送,我窘得不敢抬头,心里却窝足了怒气。
从点心店出来,她借口有事就先跑了。做得那么明显,简直像个职业媒婆,我想着。郑闯站在我对面,一味说,我敢发誓,我没把秘密说出去过。我说他妈妈真是精灵透顶天呵,我怎么像个碎嘴的小媳妇,竟不恭敬地议论别人的母亲!还好,男孩很粗心地一笑,说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么?我心惊肉跳。他说她觉得你是个强角色,又说真的,听说你扳回了通知单,我们简直晕倒你真是有一套,将来定不会吃亏。
事实会证明我与那精灵女人无缘,但她的话无论当初还是如今都对我形成辛辣的刺激。事业顺畅无阻时,我总感激她的慧眼识人。假如有朝一日我能如此被一个人念念不忘,那我会死而无憾。
我离开郑闯回到家,天色已晚。母亲在暗头里坐着,家里突然显大起来,空得像个殿堂。我很想跟她谈谈郑闯的话,刚提了他的名字,她就问,刚才哪个男孩叫郑闯?我兴趣索然,想着离家是上策,到了外头我会像个成人那样吃香,大展鸿图。母亲摸黑过来,衣服窸窣作响,我忽然很怕她像平素那样拍我的脸,这太过时。我已到了引人注目的年龄,郑闯的母亲给了我这种信心。
我神圣地坐得端端正正,母亲犹豫一下,没有贸然伸手。我觉得滑稽,原来母女间也存在着哪个占上风。母亲显然有话要讲,我既想听又怕听,怕那话跟我的主张不吻合,从此会扰烦我的行动;但又极想得到些立刻能用上的经验,处世方面,爱情方面都好。况且,自从通知单下达,母亲一句惜别的话都没说过,我渴望她能表达几句,否则过去的十六年将一片惨淡。我早已想好,在那伤感的场合大哭一场,作为辞旧迎新的纪念。
我渴望的平等倾诉母女之情被人搅了。搅得如此彻底,以致于这以后我跟人再相对无言地静坐,总会默默地等待那阵拼足老命的擂门声。那成为一种障碍。
来者是张之道,我头一个念头就想踢他出去。但人家有本事假装迟钝,火速笑成一朵花,况且,双手掣着一尊毛主席去安源的石膏像,我们那时称之为宝像。我想不出这鬼东西是怎么腾出手来擂门的,后来别人说他有软功夫,他跷高脚来擂门可以乱真。
张之道说他是代表两个老师来送宝像,本来张晴观要亲自来,但这几天她前夫的儿女找她麻烦,她脱不开身。我没问为何诸嘉运不上门,因为张之道并不十分可靠,通过他,任何细微末节都可能曲曲折折地传到诸嘉运耳里。
张之道是班上另有一功的男生。家里住着一幢洋房,拦个大铁栅栏,有点监狱的意思;他本人自恃清高,在革命化的年代里还时常把些出典深奥的诗句挂在嘴边。后来有同学搜集他的语录送到工宣队那儿,工宣队确认此为封建糟粕,当小毒草狠批了一通。张之道从此丢弃清高,说话中硬性夹进些粗语,可惜腔调仍不像。张之道毕竟开了悟性,这点聪明劲一发不可收拾:先把工宣队以及两个班主任捧成佛,接着又趁分配未开始大造舆论,说自己有癫痛,有偏头痛,总之是集中了五六种死无查证的病。分配时,他没费周折就被列入待分配,这意味着他只要在家吃一阵老米饭,待外农的人全走干净,他就可在叫生产组其实是手工小作坊的地方谋职。
他的那套花样大家都能一眼看透,可班里没人仿效他。这也许是做人的一种觉悟,看来张之道是丢弃了全部清高,甘愿降为可怜只。
他放下宝像,坐在那儿东问西问。母亲注意地观察他,我怕她把此人当作郑闯,哪怕只误会一分钟都会成为我的耻辱。所以我一遍遍地叫他的名字。后来母亲走开去,张之道从裤袋里摸出一本塑料面笔记本递给我,才手掌大小,带着男孩的体温。
他说这送你。又让我看扉页上的题词。我发现上头很花哨地写着天涯飓尺四个字,我懂得这有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的意思,只是多了一层情意绵绵。
张之道原来很让我害怕,他人并不凶狠,但细腻有余,只要我换一根发带,他就会追着说,等下,等下,让我仔细欣赏欣赏。有时他会在半路上突然闪现在我面前,问我今天为什么特别高兴?其实连我本人可能也没感觉出高兴。我说他管得太宽,只隔了一天,他就给我留条,没有文字,只一个愤怒的大问号。对凶恶的男孩我曾胆战心惊过,但一旦躲远威胁也就消除;然而张之道那样的诞皮厚脸我倒是很深地担忧过。
他絮絮地叮嘱我,出门千万谨慎,坏心的男孩多如牛毛,万万不要多跟他们搭讪。我差点笑出声,头一回想到要捉弄他这个不识趣的。我说女孩出门总要依靠人,你不去,我只能另找了男孩帮忙。他怔了怔,突然像羊那样忧伤地看着我,说他没办法,没有力气,去那儿他会死的,不像别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他真像一只孤羊,在寒冷的黄昏中瑟瑟颤抖。我很内疚,竟逼他说出这番话,这对一个男孩是太残酷的事。于是我真心诚意地祝他早日分配。他交替着把两手关节摁得咋咋响,说他正在悄悄地研究无线电,已装成了一个简易对讲机,他说有了本事总会派上用场,等运动结束,技术会吃香。我相信眼下才是真正的张之道,一个既狡猾又善良,脑子好又极有目光的男孩,这跟印象中的他完全是两码事。我庆幸自己在走上社会之前具备了识人的基础。
张之道心满意足而归,走路肩那儿轻飘飘的。直至我走,他再没露面。可能是怕刚树立起来的形象倒坍。
事后母亲却屡次提到张之道,对他印象极佳,说他将来必有出息。母亲那少有的热情形成一种玄妙的反差,踏上征途前的满腔热血毁掉不少。将来,我确实没怎么想过,而张之道不仅想而且还牢握手中;我恍惚预感到,他比我和郑闯老练得多。认识到恋人居然有不足,我觉得门得要死,决计不再考虑此事。但母亲不罢休,她问郑闯会些什么。我恼羞成怒地说他样样会;我不能说他只会蹬黄鱼车,我说他想学无线电的话,肯定也会学出师。不过母亲已把阴影斜在我跟郑闯中间,它再也驱除不掉。犹如一个斑疵,一个难看的疤。
再想到郑闯,张之道那羊一般的眼睛就会幽幽地闪出来。一直延续许久。我曾悄悄地买了一回镇定药,差点以为自己是疯掉了。
十六岁是我一生最骄傲的年龄。骄傲是我一贯向往的,只是那之前一个丑兮兮的瘦弱女孩毫无引人注目的资本。此刻,一纸户口迁移证让我成为浪潮中的强者,时时有做主角的感觉。美妹正相反,一面遭受小多的责备,另一面,大受阿司匹林的怒气。人就是如此,退了一步,就可能再退第二步。活灵活现的美妹突然成了个惟停的泪人儿。她买来半打月牙边的花手绢送我,刚说了半句惜别的话就泪如泉涌,结果擦湿了其中的两块。美妹还说她没勇气去学校退那张通知单,怕见人脸色。我说我可代她去。说到这里我甚至怕她改变主意,不由分说地把那通知单捏在手里。
我想当年如此骄傲和自信,除了处境突变,还因为那骄傲如新萌发的嫩叶,没有虫伤和薄灰显得生机勃勃。我真的去了学校,张晴观仍在家与她自找的冤家们巧周旋。我径直走到诸嘉运办公桌前,他脸上显得疑惑不解。近一年中,我没跟他说过一个字。现在我成了个独立的外路人,不受其管辖。所以我就打破常规,随意地问他好,宛如一位主宰人的女神。
他坐着,只要不行走,就成了个像样的男人。如今他自然不能看轻我,于是就一点不怠慢地说他本打算去看我的。他还笨拙地拖过椅子让我坐。我想男人的伸缩性太大了,我倒希望他气哼哼地显露自己的失算。
我把美妹的通知单交他,他说她就是那样出尔反尔。我用平起平坐的口吻说,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他吃惊地看看我。我想这辈子他就得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端起茶来喝水,突然问,是不是张晴观怂恿你去招工办的。我笑起来,笑得他像牛一样瞪我。我说世上总有愿意成全别人的好人;这下轮到他笑了,他说有些人看来是好人。我问这话什么意思,他摇摇头做了个很洋派的耸肩动作。
走出校门,我才觉得对这个城市的挂念全部解脱,一切恩怨都统统摆平,就像一个濒死的老太婆安排好了后事。原先那个稚嫩的我已经死去;活着的是个连我自己都敬佩的精明少女。居然她能够压垮一个过去望而生畏的男人,在他的盛气被摧残后,他对她就完全不重要了。但他那最后一句话,仿佛一个伏笔,一个横在两段文字间的省略符号。
后来我再也没遇上诸嘉运,这是天意。每次回家探亲我都去拜访张晴观,她是提前退休的,没有再婚的迹象,但是头发总是染得绝对黑。她问起我当地的情况,眼光总是对着窗外,仿佛不忍面对一派惨象。弄得我每回都是急匆匆告退,逃一般奔回家。
我有幸赶上她的葬礼,购得一鲜花制成的花圈。漂亮女人她若在天有灵,定会中意的。我在临时租下的灵堂遇见了张晴观最得意的门生。当年她与我境况相仿,我远去林场后不久,她却进了市郊一家工厂,据说那是全班唯一的保留名额。她用本地人的客气与我寒暄,接着又面露难色地把我拉到厅外。我没想到她会劝我尽快离开,她说这样对她的恩师更好些。我冷笑数声。她说料到我会来这儿闹一闹,因为当年诸嘉运本想把那保留名额留给我,但张晴观在中间插了一杠,完成了对得意门生的一番心愿。
哀乐四起。我跑进厅堂,去瞻仰张晴观的遗容。我发觉我仍爱她,一个人只有将对方的苦衷都包容在一起,才称得上爱得尽心。我面对那遗体,仍旧觉察其将目光移至窗外。带着难言之隐去死简直悲惨。我极愧疚,这多年来每每去扰烦那颗善良之心。
命运本有自身的秩序,它就是面对一连串抉择。既然我已将一大片空白留给初恋,一旦不如愿,定会像剪下的花,早早枯萎。
我是清晨离家的,头夜睡得晚,所以昏昏沉沉,梦境随时会突然冒了头,闯出一两个片断。光听见美妹风风火火地叫要迟到了,接着又出馊主意,让我洗一遍冷水脸。离家的悲壮我试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