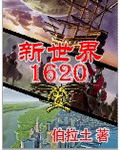16岁少女-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倪娜说不信,知青头突然急得说话像打连珠炮,说是这儿冬天河面冰冻九尺,连装甲车都能在河上开着抄近路;当地风又紧又密,窗缝纸贴在内仍会钻风;山上井冻住了,只能用麻袋装回冰块来化水。
远远的看见我们的帐篷,门开了半尺多宽,有人哗地倒出半盆水。知青头连声喊糟糕,说水倒在外旋即就结冰,踩上去就打滑。他像个卫士一般寸步不离倪娜,哈着腰找那打滑处,亮光移来移去,好不繁忙。
〃小倪,你慢一点,慢〃他话音未落,突然一个趔趄扑倒在地,电筒飞出去一路滚向前,神枪手的称号也弃置一边:扑在那儿抓瞎似的到处寻眼镜。倪娜赶紧蹲下去帮他找回眼镜,还伸手拉他,我看见他紧紧地攥着她的手,好半天才松开。
我们两个进了帐篷,我往铺上坐,想着知青头的狼狈相,就解气地说:〃真好笑!〃
倪娜严肃地说:〃我看不出哪点好笑!〃然后也闷闷不乐地坐下。至少十分钟才开口说,〃你好点了吗?让我摸摸发烧吗?〃
我躲开她的手,那手与知青头握过,我神经兮兮地怕知青头的手气会间接地按在我额上。我小声说:〃我看见他拉你的手。〃
〃他摔倒了,需要我扶一把,〃倪娜的脸红红紫紫的一片,〃难道你没看见吗?〃
〃可他是个男的,况且你不拉他也能爬起的。我觉得他巴不得你对他好。〃
〃你真让我难堪。〃她双眼厉害地盯得我不自在,〃女孩让人瞧不起就因为小心眼存得太多!男的就不该受尊重?不能当哥哥或者弟弟那么对待?!〃
她是我头一个遇见的那种心宽宽的女孩,有主见,却没有心计,不会把自己深深地藏起来,而是很明朗地裸露心地,想的比美妹要浪漫十倍!我喜欢她那磊落的口吻。可心里接受不了那一说:太不谨慎了,弄得知青头差点要以未婚夫自居,她都听之任之;等人家将她团团围住,那就为时过晚!我把这意思一说,她干脆更占起上风来:
〃假如真有人有办法围住我,我就不突围,高高兴兴投降。〃她说,〃我不怕,我能把握自己。〃
我担心横亘在眼前的差异会影响友谊。女孩子间是容易谈崩的,甚至好端端的朋友变为冤家对头。我不喜欢那种对恨对爱随随便便换来换去的人,我想忠实待人,是那种掏出心的好。即使她冷淡我,我仍爱她,捧着她,因为要命的好感已经笼罩我,喜欢她和喜欢自己已经难解难分。
十六岁时的一片痴情总想贡献给什么人。没给郑闯,因为一上车我们的缘分就浅了。我惊奇,我们宛如一对陌生人,只由着那些小秘密牵住,那像红线,细微得若有若无。我渴望的是个知心朋友,一个亲同手足的人,好像并不是情人。我准备去牺牲,用以换取倪娜的真挚感情。我真的愿意去为她受伤吃苦。哪怕她再用手摸我的额头都在所不借。
〃倪娜,我十分难受。〃我说。
那个大度的女孩真腾出手摸摸我的额。这回我根本没想到该死的知青头,她的手能净化一切杂念。她说;〃要命,你在发烧!〃
我看清她好看的眉优雅地往下弯弯着。霎间,她像被气浪推出老远,我想扑出去追赶却坠了下去。只听到她急切的声音:靠着我,靠紧点。可我停不住,仿佛一只劳碌的陀螺在疯狂地旋转,
J旋转……
我就此一蹶不振。头昏、呕吐,不思茶饭。贮木场的医生来过两回,扎了一针,扔下点药,末了还摊摊手,说行医至今未见过这等怪病。
隔了一天,我吐得更凶,全是些绿色的胆汁,肚里竟装着这些玩意,真使我羞愧。一帐篷人坐在一块参加集训,我时不时奔出去大吐一通;知青头见这情势,便通知我不必参加集训。这其实是罚我陷进孤独的泥潭,漫长的白天,我可做的就是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望那蝙蝠色的篷顶。
不久,我颈脖那儿长出一圈密匝匝的疹子,大小如绿豆,宛如一长串饱满的珍珠项链。倪娜慌慌张张跑去请医生,我猜想她奔的如同苗条的鹿。可我已不信任那医生,他绝医不好我的病;他之所以不断推出些药是因为想碰上好运气,但好运气与他无缘。
我拒绝与医生合作,但随着我双脚也开始肿胀,妥协就重新出现。医生在我额上脖子上拔火罐,很残酷地把我的额头烫得发紫,他说是把邪气抽出来;中医从此在我眼里变成一种巫术。以前我最不屑一顾的职业要数体育教师,此后就变成中医师。我对接触人体有关职业的偏见延续了许多年,直至有了一点博爱精神才消除。
翌日,我的脸和整个头部全肿胀起来。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在他的瞳仁里见到奄奄一息的自己;这一刻,我才相信那个病重的女孩就是我本人。邪气攻她心,厄运降她身,它们要为难她、冒犯她。这些都是注定的,像已经过去多年的事又倏地冒了尖,轮回过来。我对他说,我熟悉它,我以为他会懂,却见他如影子那般飞速撤后去,吟唱似的说:〃没治了。〃
贮木场的医生是本地一个大拿,他说没治,自然就不再有医生上门。而我的病情却一天天加重,头肿成个木瓜,面目可憎。倪娜早把心形镜子撤得无影无踪。每当她端着搪瓷茶缸去烧乌梅汤,我就撑起身,在帐篷玻璃上照自己的脸。对着我的帐篷窗口是一棵枯树,死去多年,枝桠成精般地岔得开开的。有一段正映照在那块窗玻璃上,与那憔悴的脸构成落泊景象。
倪娜端着乌梅杨进来。她带到此地的吃食一样样都拿出来试过。唯有喝乌梅汤我才不原封不动地吐出来。她鼓着腮吹那热气,神态像个小母亲,十分神圣。不一会儿,知青头来了,一个劲说:是万林强要收她!是他做的主!现在麻烦来了,他却留在上海迟迟不归。
我猜到他会一脸怨恨,每一个细胞都将我当成废品,因为预料到的,所以不值得愤怒。我的思维格外清晰,那个新出现的名字迅速地传播开来,那就是他,他在走近来。走近来,挥舞着激情的胳膊,可我无力迎他,肉体疲惫到极点,仿佛死掉了,冬眠了。
〃我跟你谈的事你考虑了吗?〃倪娜说。
〃当然,当然,〃知青头说,〃我去找过邢指导员,他说哪天先来见见人。〃
〃哪天呢?〃
〃还没定。他是个忙人,一时抽不开身。小倪,千万别急。东北佬火上房顶了,还得把烟袋拍完呢。等他见了人,会答应的。〃
我不知他们背着我商量什么,只知与我有关。我立即体会出自己与健康人的天差地别。当晚,倪娜神秘地失踪了,大家昏昏沉沉入睡时她才带着一身寒气归来。她绞了一把热水毛巾递我,我擦了脸,就欠起身来看她做事。她把毛巾放在盆里搓着,忽然直起身忧郁地瞧着我,仿佛要把我印进记忆。我发现那水仍是清寡寡的,原来我已病得连污浊也没了,此刻,任何正常的机能都令我仰慕,可它们在逃避我,抛弃我。我简直羞于伸出手来,因为指甲苍白如纸,已无一丝血色。这改变了我十六年来的审美观:管脸蛋红扑扑的女孩叫阿乡;将脸色苍白的女孩看作白雪公主。我忽然不要那书卷气的病态美,想往当一个村姑,有火烫的血气。
当夜,我做了个苍白的梦。出现个老翁,貌似舅公但绝不是他,我想那舅公的形象不过是个幌子,除他之外我没关注过其他老翁的脸,所以只得由他的五官显现。他问道:你死在此地如何?我说好。然后就惊醒,悄悄坐起,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已经死去了。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我望着窗外,枯树在冷寂中站立。我想我死后,它仍会那么站立,将一枝的枯影斜射在窗上。我突然想挥动斧子将它截掉,让它先于我死,先于我倒在那儿,否则太不公平,否则我就死不瞑目。我要用最后的残忍杀掉那棵枯树,就如抹掉一个痕迹;找一个同归于尽的伙伴。那之后,再见到听到溺水者不顾一切抓住某件物品,我都会涌出悲悯。人怕的是两手空空去死,与其说是贪婪,还是归结于懦弱的天性。人的最大敌人便是孤独。
〃小姑娘!〃倪娜转过脸来,〃你想什么?〃
〃有点冷。〃
她那儿窸窣地响起来,一下子钻进我的被子,她的上衣像是柞丝的,老是响着。她用裸着的胳膊拢住我的肩,我紧挨着她健壮美丽的身体,把脸埋在她胸前。她的热量暖烘烘地熏着我。我感觉那是一片温柔的云,是没有边际的温泉。在那里,我变成个婴孩,一个粉嘟嘟的女婴。
〃小姑娘,〃她挨着我的耳际,〃好好睡,明天就能决定命运。〃
倪娜差点领我上了歧途。
一早,倪娜就把我拽起来,并把我全副武装起来。她说命运,我无动于衷。那份玄已失却魅力,它只对圈外人产生诱惑。我顺从她,是由于能讨她喜欢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出了门,她搀着我,顺着铁轨一直向前。
〃去指导员家。〃她说,〃昨晚我去过,基本上已讲妥。你坚持一下呵。〃
没走多远,我就虚汗直淌。于倪娜无关的事我都觉得索然无味,此时我想着的只是昨晚她走夜路的寒冷,但愿知青头没再来接应。我怕那甜腻腻的声音会让她坠入陷阱。大意的女孩周围会徘徊一些阴险的男人。
倪娜领我进入一个雄壮的门垛,在周围这是相当考究的,有土财主的气势。指导员是个大个子,身板挺得精薄;脸松松垮垮,像个瘪口袋。背影像小伙,脸像大爷,让人不知怎么就生出感慨!
〃炕上坐。〃他就说了三个字,就找了个墙角倚着,蹲得低低的抽烟。
那个炕有文把长,五六尺宽,像中学里的小戏台。坐上去,居然是温热的。炕头那儿坐着个黑擦擦的女人,奶奶模样,满脸是辛酸的皱纹,却敞着怀奶孩子。
〃是个小子!〃她把孩子的腿扒开让我们过目,〃生了四个丫头,才得这小子。隔几天就满月了。〃
说话间,外面涌入四个小丫,拖鼻涕,小狼般地看着我们。指导员挥挥手,她们就全蹿出去。他说:〃隔几天她出了月子,我就去区里场里说说。她病得挺邪,〃他用下颏点点我,表示已转过话锋,〃不过,得让她落个白纸黑字,要不显出咱这块不仁义,将个病包子打发走,落个话柄。〃
我感觉钻进个圈套,指导员跟倪娜已组成起联盟,要不是他用了一番农民的精明算计,倪娜也许会一直瞒我大红宫印盖下来。我拼命喊:〃我绝不写申请,别打算退我回去。〃
倪娜仓惶地说:〃退回去你就能留在上海。〃
〃要走我也不能这么走!〃我说,〃你想到我的心情吗?做一个走回头路的废人我情愿死。〃
〃我讨厌你说死!〃她对着我咬牙切齿。
〃我恨你那么逼我!〃我笨拙地转了个身,用整个脊背对住她,样子很凶恶。
我们说的上海话,然而指导员全都领悟,就如我们观赏哑剧小品,因为人的喜怒不分地域全球通用。他兴奋地说:〃不走也中,咱这块养人。嘿,那地有灵气!〃
他比划着,如女人在炫耀娘家的富庶。他说当年日本鬼子有心闯这儿来掠夺木材,可天突然奇寒,大雪没人头顶,日本孬种吓得屁滚尿流。说话间,他带着对当地的爱以及对外来者的抵触。他甚至口口声声称这块儿养得起更多的知青娃,仿佛我们都成了靠他抚养的小丫。
后来我才得知他原是从山东盲流过来的,这块肥沃的土地是他的恩主,因为爱得深,他才巴不得永久占有它。对于后来者,他深藏底细,跻身于当地人之列。他是农民,他的子孙万代都靠这片土地,那大概是他尽心尽力的动力。因此,我从不相信他会欢迎我们,任何托词不过都是些言不由衷的官样文章。
有关外来人的观念在那个早晨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了。不想走,是因为不能一无所获地走。那时我太年轻,满脑子功利思想,殊不知任何所获都会伴随着所失。
默默地跟倪娜走回程路,她仍搀我。我穿得像个桶,而她身材高挑,使我自惭形秽。大概是这种自卑提醒我克服本性的狂妄,纵观下来,我能与之常相识不相疑的女友个个如花似玉,美不胜收。我很高兴自己凭着智慧和忠诚蒙住了她们讲究外貌的眼睛。
风凄凉地吹。我对倪娜说起那株枯树,并且扬善避恶,只说怕那树。倪娜说请个男生帮忙砍一下。她确实已成了个一呼百应的人。我安下心,仿佛宿愿已了清。
当天下午,倪娜真约了两个男生来砍树。其中一个英俊少年,天然卷毛发,他先爬上去砍那巨大的枯桠。然而就在枝桠落地的刹那间,他欣喜地叫道:〃它还活着!〃他们几个举起那大桠,说截断处木质是青白色,还有树浆渗出。看来它真活着,它有生命我就奈它不得。那棵活树因为我成了独臂将军,在它眼里,我是个该死的魔王。
我的病情继续加剧,病魔能使人变得多愁善感:别人敲着铝盒去食堂,我会像聆听哀乐一般郁郁寡欢。钱小曼带着哭相看我,我便想到将来瞻仰遗容她会悲痛欲狂。郑间来过几次,垂着手呆站,不停地伸出舌头舔嘴唇,我怜惜他小姑娘般的腼腆,是我打击了他,让他空欢喜一场。我极想说些道歉的话,留在那个人伤痕累累的心底。可每逢我欠起身来,他就如惊弓之鸟,报出个离去的借口,让人不忍不允。
我预感到死亡紧跟在生命之后,可我以为死是个郑重其事的杀手,它总会在下手前给点暗示。我想往的死其实也带着生的光彩,就如那个诡秘的旧梦轮回往来,生与死构成了浑圆,时空间连成了古朴的线。我不相信那个我会死,会真正死得没了灵魂。我只相信除我以外的人会先后长眠,他们难以长生不老。
一个阴惨惨的下午,我孤独地安睡在黑擦擦的帐篷内,仿佛置身于乌青色恶云之下。天旋地转的头晕早已过去,我分不清是昏睡还是半昏迷。我见到舅公,这回他没与我讨论生死,而是紧闭宽阔的嘴。他向我伸出手,脸色格外肃穆。我觉得周身轻得像插遍羽毛,我微笑着想伸过手去……
〃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