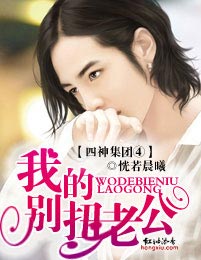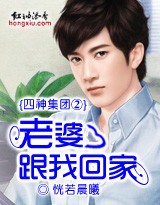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必将导致痛苦的审阅,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可能迅速。所罗门美邦提供的资料包括与我为格鲁曼在AT&T总部安排的会面有关,以及显示杰克向我报告对该公司研究进展的电子邮件和备忘录。另外,我们研究主管的讲话记录也被公布,这份文件显示我们的管理委员会讨论过我们的投资银行家是否不正当地影响了研究评级。在调查的开始,监管者着重于这些文件,试图弄清它们是否能够说明我损害了研究过程的诚实性。
最初,我被这种想法吓了一跳,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看到这些文件中的一些被泄露给媒体也使我深深地苦恼。尤其是我不记得参加过一个讨论银行家与分析师关系的会议。大量工作之后,我们实际上证明了我没有参加过这一讨论,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公司管理委员会上进行,而是在卡彭特的一次部门会议中进行的。至于我鼓励格鲁曼对AT&T保持开放的观点,我从不否认我提出过这一建议以及我与杰克一起访问过这家公司。这些事情是任何CEO履行职责时都可能做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的顾问同意了。
秋天,我们开始感到风向的变动,并认识到或许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公共沟通策略。9月中旬,我同意在一次由美林主持的机构投资者会议上演讲,详细陈述了我们进行的改革。在正常情况下,投资者会听到我谈论收入增长、成本控制和资本效率;但现在,他们发现我在强调建立行业最佳执业行为的个人责任。其所发出的信息简单明了:“我明白大势所趋。”我承认斯皮策让我很难过,并展开大大的笑容开玩笑说,我已下决心最好地利用这一逆境。“看看我的腰围,”我说:“我聘请了一名私人教练,并采用了一种我命名为‘斯皮策节食疗法’的减肥方法,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与监管当局的问题,我都不会再喝最喜欢的马蒂尼酒。”
几天后,《商业周刊》报道了我的演讲,进行了几个星期以来媒体的第一次正面报道。除了宣传我减少的腰围外,它还报道了我们整改商业模式的严肃性。同时,查克·普林斯和我们的外部律师开始与各种监管者举行会谈,讨论和解条件。最后,我们以为终于瞥见了隧道尽头的亮光。
监管者的报复(5)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不幸的是,我们还不会被赐予和解的机会,因为这段不幸经历最折磨人的章节刚刚开始。10月初前后,我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请来为我们收集发给监管者的电子邮件的公司发现了一个软件漏洞,突然,另一些与调查有关的文件被曝光。我接下来得知的消息令我震惊、愤怒和绝望。这些电子邮件包括杰克·格鲁曼和一名女性客户卡罗尔·卡特勒(Carol Cutler)的通信,他们之间有性关系。
在他们之间的一些充满甜言蜜语的交流信件中,我们的分析师解释了为什么他对AT&T的股票给予重新评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吹嘘说他推荐这支股票是为了帮助我获得迈克·阿姆斯特朗(当时是花旗集团董事会成员)的支持,好在约翰·里德离开前我们在董事会越演越烈的争夺中对里德进行“核打击”。格鲁曼还夸耀说我利用我的影响力把他的双胞胎孩子送入了92nd Street Y学校的幼儿园,而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改变评级。
这些完全是胡说;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电子邮件看出,格鲁曼编造了这些故事来打动他的女朋友。大部分邮件都很反常,因为它们要么在幻想格鲁曼为了卡特勒离开妻子,要么是关于想象中的性交的生动描写。这两个人对描述人体器官有强烈的爱好。从始至终,卡特勒都称格鲁曼为“国王”和“大家伙”。
看过这些材料之后,我得出结论,那就是杰克有严重的自我问题和心理缺陷,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卡特勒的一封信竟长达20页,包含了怪异的想象,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两个人的心智。
看这些东西让我恶心。我对没能早些发现这些文件感到恼火,因为我知道调查者会对这些相对无关紧要的电子邮件给予高于正当水平的关注。虽然确实是由错误导致,但它们的推迟曝光会使我们非常难看。最糟糕的是,这些电子邮件毫无疑问会使监管者进一步增加调查,把一切推向可笑的边缘。
我利用我们的分析师打败里德,和我帮助格鲁曼的孩子进入某家幼儿园以换取他改变对AT&T股票看法的说法既奇怪又荒唐。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信件有可能被利用,使我看上去真的指使格鲁曼发表了富有争议的研究结果。我再一次对无法控制局面和解决问题感到绝望。
几乎在一瞬间,一切都乱了。斯皮策的人开始调查格鲁曼声称的事实,找大量人员谈话,包括我们的董事、员工和朋友。这些质询显然高度涉及到我个人,并损害了我的声誉。几乎在同时,查克·普林斯告诉我他接到斯皮策的电话,后者暗示花旗集团董事会应该考虑我的利益是否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查克说斯皮策措辞非常谨慎,他强调他的观点是朝前看的,而不是直白地说我的CEO职位已经受到威胁。查克告诉我,他回答斯皮策说格鲁曼的电子邮件是不可信的,明显是假话,但斯皮策拒绝接受查克的观点。按照查克的转述,斯皮策只是说“这些信息必须被公布。”
我对这一消息感到愤怒而绝望,也对这些新发现的电子邮件将被怎样无耻地扭曲和利用感到恐惧。“利益冲突”的说法让我惊慌。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名员工在与第三方的暧昧通信中所说的毫无根据的话能够被用来伤害一家重要公司的CEO了?
实际上,说我在与里德的斗争中利用格鲁曼取得迈克·阿姆斯特朗的支持没有任何根据。它显然与事实不符。我让我们的分析师重新评估AT&T是在那次决定性的董事会议之前一年多,而他最终改变评级也是在影响董事会在我和约翰·里德之间做出选择的诸多事件发生之前好几个星期。我与迈克·阿姆斯特朗之间有长期紧密的事业关系,如果他在我与里德的对决中不支持我,那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最后,假如我担心董事会对决结果的话,为什么我要在里德离开之前几个月主动聘请鲍勃·鲁宾?他与里德的关系可比与我亲密得多。
说我利用我的影响力帮助格鲁曼的孩子进入幼儿园是为了诱使他改变对AT&T的评级也是胡说。确实,杰克在改变评级前一个月曾向我抱怨,他频繁的出差使他很难有精力管让孩子上私立学校的事情。他问我是否认识92nd Street Y学校的人,并拿出了这所学校董事会的名单。我发现我妻子的朋友琼·蒂施(Joan Tisch)在名单上,便提出可以试试。其实,多年来我帮助过数不清的员工解决个人问题,包括医疗推荐(通过我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关系)和为员工的小孩写大学推荐信。
我本性乐于助人,把帮助有价值的员工当作职责的一部分和锁住他们对公司的忠诚的方式。虽然格鲁曼是在10月底找到我,但我是在12月中旬给琼·蒂施打电话,也就是他发表对AT&T研究报告之后三个星期。花旗集团的基金最后承诺向92nd Street Y学校捐赠100万美元,五年内付清,但这一捐赠是在几个月后达成的,格鲁曼的孩子早已被接收了。
人们必须明白,这一捐赠与花旗集团的整体慈善计划是一致的。提供各种讲座和艺术表演?92nd Street Y学校是纽约市的文化象征。我认为把花旗集团的名字与这个受到高度尊敬的机构联系起来是很有商业意义的事。
不幸的是,11月初,格鲁曼在一份向我报告他对AT&T的研究进展的备忘录结尾处提醒我他的帮助请求,这份文件后来成为调查的焦点。虽然它把92nd Street Y学校称为“另一件事”,但这份备忘录不幸地模糊了关于92nd Street Y学校的请求和格鲁曼对AT&T的研究工作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我没有做过任何承诺,这从杰克恳求和谦卑的请求帮助的语句中可以看出来。格鲁曼还找过肯尼·比亚尔金和鲍勃·鲁宾在92nd Street Y学校的事情上帮忙,这进一步驳斥了他依赖于我的帮助的说法。最后,杰克的帮助请求是在他完成了对AT&T的大部分工作之后提出的,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的研究与92nd Street Y学校的事有任何关系。
斯皮策对查克说的“利益冲突”使我更加沮丧是因为,这一暗示意味着总检察长正在玩双重打击,或许他希望在彻底审查格鲁曼的诽谤言论之前就让董事会和我之间产生嫌隙。而且,即使在调查者威胁他有牢狱之灾的情况下,格鲁曼仍然反复否认他对卡罗尔·拉特勒说过的话,他的反复无常使得这一新“证据”的可信度降低了。
如果说斯皮策与查克的对话还不够糟的话,那么避无可避的打击很快就会到来。由于一些选择性的消息泄漏,《华尔街日报》的一名叫做查尔斯·加斯帕里诺(Charles Gasparino)的记者发表了一篇封面报道,称斯皮策找到了新证据并透露“此次调查中公司的利益和韦尔先生的利益或许有冲突。”
这篇报道造成了明显的市场影响,使花旗集团的股票跌至27美元的新低(全年截至当时的跌幅达43%),并打击了我的团队。我们怎么会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仍在进行中的调查的实时报道呢?过去,当证券业监管者不在公众聚光灯下进行调查时,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但消息泄漏不止于此。缓慢而残忍的折磨开始了,我们将面临一次又一次选择性的信息公开。我进入了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
几个星期前,我们曾约定我将在监管者面前作证,并安排了两次10月底的听证会。我能肯定,不管是谁泄漏了“利益冲突”的消息,都是把这当作让我在提供证词前失去勇气的手段。如果这就是他的动机,他成功了。虽然在那些新邮件被发现之前我对调查充满信心,但现在压力和不确定感让我疲惫不堪。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消息曝出来。尽管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和我一样相信我与公司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马蒂·利普顿还是派他的两名骨干律师拉里·佩德威兹(Larry Pedowitz)和约翰·萨瓦利斯(John Savarese)专门负责我的个人情况,直到让监管者确信我没有过失。10月的大部分时间,这两名经验丰富的律师都在帮我准备证词,我们一遍遍地温习发生过的事件,进行模拟提问。
我讨厌我的职业道德和人格受到怀疑,不得不花费宝贵时间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专心管理花旗集团让我很恼火。我大概让佩德威兹和萨瓦利斯发狂了。为了获得一些控制感,我最初对这两名律师采取抵制态度,不满他们令人不快和过度严肃的提问。把佩德威兹改名为“世界末日先生”之后,我终于投入到证词准备工作中。
监管者的报复(6)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我最初出现在监管者面前是在华盛顿遭遇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虽然我们知道将有一名速记员做现场记录,但从来没有得到关于会议的官方记录。回到纽约,我在几天后接受了第二次审查,律师把它称为“访问”,是斯皮策办公室牵头的。这一次斯皮策给了我一些礼遇:他允许把审查安排在沃切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不是强迫我去市中心,那样我将不得不躲避守候的摄影师,成为媒体杂耍的一部分。
我把马蒂的办公室看作友好的环境,它稍稍减轻了我的紧张。斯皮策没有参加这次审查,但我想所有其他有关的律师都在场了。在佩德威兹和萨瓦利斯的左右陪同下,我在一个巨大的会议桌旁坐了下来,面对斯皮策的一帮人。我们在上午9点30分开始。米歇尔·赫希曼(Michelle Hirschman)领导这次审查,她曾经是检察官,也是斯皮策调查的领导人。赫希曼的几名同事坚持用一种评判式的方式提问,但我认为总体来说这次问讯是比较公平的。
我已经做好长时间作战的准备,因此努力大方地满足我的提问者,希望他们回之以礼。中间休息时,我试图以玩笑舒缓气氛。斯皮策的团队很专业,我很欣赏他们的公事公办,虽然我内心对事情本不该到这个地步感到很气愤。晚上6点左右,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结束。没有任何值得惊奇的事出现,这次审查看上去很沉闷。我感觉我掌握了局面,佩德威兹体贴地证实了我的感觉。我充满希望的离开,但仍然紧张得要命。回到家里,我完全不愿再回想这一天;但琼妮还是不停地询问细节。令她失望的是,我拒绝回答。我已经彻底崩溃了。
尽管我做出了坚定的表现,令人始料不及的事还是接踵而至。我作证两周之后,《华尔街日报》根据最新泄漏的错误消息重新发起攻击。一连三天,查尔斯·加斯帕里诺喋喋不休地报道了格鲁曼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电子邮件中听起来最有伤害力的部分。第一篇报道出现在11月13日星期三,提到格鲁曼说他改变对AT&T的评级是为了帮我对约翰·里德进行“核打击”。
这篇完全没有依据的报道明显打击了投资者,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这天下跌了4%。星期四,加斯帕里诺报道格鲁曼否认了电子邮件的内容,但这名故意只提供与他所要的故事相吻合的信息的记者现在说,我们的分析师在我同意运用我的影响力让他的孩子进入92nd Street Y学校时改变了评级。最后,星期五,《华尔街日报》引用了那篇格鲁曼向我汇报他的研究进展并请求我帮助他的孩子入学的备忘录。
这篇报道提到了花旗集团做出的五年捐款100万美元的承诺,但没有提这一捐赠是在格鲁曼改变评级后才进入讨论,并在他的孩子入学后几个月才达成的。它也没有提这笔捐赠对我们的基金每年1亿美元的捐赠预算来说微不足道,而且92nd 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