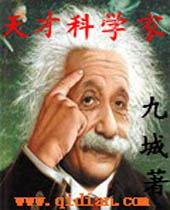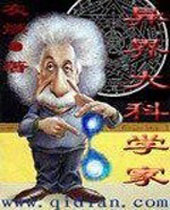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一个危机时期,是有些什么错了的时期,这个时期只是随着波动力学的发展而告终的,并且证明了光是自相一致的实体,既不同于波也不同于粒子。因此,在科学中,如果知觉转换伴随着规范改变,我们就不可以期望科学家们直接证明这些改变。这位皈依于哥白尼主义的人在看月亮时不会说,“我习惯于看见一个行星,但是我现在看见的是一个人造卫星。”那种说法含有托勒密体系从前曾经是正确的这种意思。一位皈依于新天文学的人则说,“我从前认为这个月亮是(或者把这个月亮着成是)一个行星,但是我错了。”那种陈述在科学革命的后果中确实重新出现了。如果它通常用同样的效应来隐瞒科学眼光的转变或其他一些精神上的转化,我们也许不能期望直接证明那种转变。倒不如说我们必须寻求简接的行为证据证明有新规范的科学家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他以前看问题的方法。
于是,让我们回到这种资料,并且相信有这样一些改变的史学家在科学界中能发现哪几种转变。威廉·赫舍尔爵士发现天王星提供了第一个例子,而且与不规则的纸牌实验很相适应。在 1690年到1781年间,至少有十七个不同场合,许多科学家,包括几位欧洲最著名的观察者,在我们现在猜想那时必然由天王星占领的位置上看到了一颗星。这个集团中一位最好的观察者在1769年事实上已经连续四夜看到了这颗星,但没有注意到这种运动能提出另一种鉴别。十二年后,赫舍尔用他自己制造的一架大大改进了的望远镜这样做时,他第一次观察到了同样的对象。结果,他已能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圆盘大小的东西,至少对恒星来说是异乎寻常的。什么东西搞错了,因而,他把鉴别推迟到进一步考查以后。那种考查揭示了天王星在恒星之间的运动,因此,赫舍尔宣布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新的彗星!只是在几个月以后,在试图把观察到的运动纳入一个彗星轨道毫无成效以后,莱克塞尔才提出,这轨道可能是行星的轨道。①当这个建议被接受以后,在专业天文学家的世界里已经有少数几个恒星和又一个行星。一个天体已经连续不断地被观察了将近一个世纪,在1781年以后,又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到了,因为,象一张不规则的纸牌一样,它不再能适应由以前流行的规范提供的知觉范畴(恒星或彗星)了。
目光的转移使天文学家们去观察天王星,可是,这个行星似乎不仅影响到对以前观察到的对象的了解。它的后果是更为深远的。也许,尽管证据不可靠,由赫舍尔逼出来的比较不重要的规范改变,在 1801年以后,帮助天文学家们准备好迅速发现大量小行星或小游星。因为它们很小,这些小行星就没有显示出使赫舍尔留心的反常的放大率。可是,准备要发现外加行星的天文学家们在十九世纪前五十年中用标准的仪器是可以认出其中二十个的。②天文学史提供了科学知觉中由规范引起的改变的其他许多例子,其中有些例子不那么模棱两可,例如,西方天文学家们在哥白尼的新规范第一次提出以后的半个世纪期间,首先看到了以前不可变的天空中的变化,能认为这是偶然事件吗?中国人的宇宙信念并不“排除天上的变化,在早得多的时代里已记录了天上出现的许多新星。即使没有望远镜的帮助,中国人在伽利略和他的同时代人看到这些现象前几个世纪也已经系统地记录了太阳黑子的出现。③紧接在哥白尼以后西方天文学的天空中出现的天象变化的仅有例证也是太阳黑子和一个新星。十六世纪未的天文学家们,用某些象一段线那么简单的传统工具,发现了替星通过以前留给不变的行星和恒星的空间在任意漫游。 ④ 当天文学家们用古老的工具观察古老的对象时迅速而又毫不费力地看到了新东西,会使我们想要说,在哥白尼以后,天文学家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总之,他们的研究所作的回答好象就是那么回事。
①彼特·多阿;《天文简史》〔伦敦, 1950年,英文版),第115~116页。
②鲁道夫·沃尔夫:《天文学史》(慕尼黑, 1877年,德文版),第513~515,683~693页。特别要注意沃尔夫的叙述使它多么难以说明这些发现是波德定律的结果。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剑桥, 1959年,英文版);第423~429,434~436页。
④ T·S·库恩;《哥白尼革命》(剑桥,麻省,1957年,英文版),第2O6~209页。
前面的例子是从天文学中选出来的,因为天象观测报告经常是用一种由比较纯粹的观测术语组成的词汇表达的。只有在这样的报告中我们才能希望发现科学家的观测和心理学家的实验主体之间的完全对应。但是我们不需要坚持这样完全的对应,只要放松我们的标准,我们就有许多东西可以获得。如果我们能同意“看到”这个动词的日常应用,我们就可以很快地认识到,我们已经遇到了其他许多科学知觉中发生转变的例子,它们都是伴随着规范改变而来的。“知觉”和“看”的引伸的用法,需要简短明确的答辩,但是让我们首先说明它在实践中的应用。
再看一看我们前面从电学史引用的两个例子。在十七世纪期间,当电学研究是受一种以太理论指导时,电学家们反复地看到了细袜子从吸引它们的带电物体上反跳出来或跌落下来。至少那是十七世纪的观察家们说过他们看到了的事情,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已的知觉报告一样也不能怀疑他们的知觉报告。在同样的仪器面前,现代的观察者会看到静电排斥(而不是机械的或引力的反跳),但是在历史上,有一种普遍忽略了的例外,直到豪克斯比的大规模装置已经大大地放大了它的效应为止,静电排斥本身并没有被看到。可是,在接触超电以后的排斥是豪克斯比所看到的许多新的排斥效应中的唯一的一个。通过他的研究,更确切地说,就象在形态转换中一样,排斥突然成为超电的基本表现形式,于是吸引就需要说明了。②十八世纪初期可以看到的电现象比十七世纪的观察者们所看到的那些电现象更难以捉摸、更变化多端。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在吸收了弗兰克林的规范以后,有一个莱顿瓶的电学家们就看到了某种不同于他以前看到的东西。这种装置是一个电容器,既不需要瓶的形状,也不需要玻璃。而是突出地出现了两片导电的云层,其中一片已经不是原来装置的组成部分。就象各种成文的讨论和图象表示逐渐表明的,两片金属片中间夹一个非导体已经成为这类装置的典型。①同时,其他感应效应得到了新的描述,还有其他~些效应则第一次受到注意。
②杜恩·罗勒和社恩,H.D.罗勒:《电荷概念的发展》(剑桥,麻省,1954年,英文版),第21~29页。
①参看第七章中的讨沦以及该章注 9中引用的参考文献。
这种转变并不限于天文学和电学。我们已经评述了某些类似的可以从化学史中抽提出来的洞察力的转变。我们说过,拉瓦锡在普里斯特利看到去燃素空气的地方和其他人根本什么也没有看到的地方看到了氧。可是,拉瓦锡在学会看到氧的过程中,也必须改变他对其他许多更熟悉的实物的观点。例如,在普里斯特利和他的同时代人看到一种原始的土的地方,拉瓦锡却看到了化合物矿石,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这样的改变。至少,作为发现氧的一种结果,拉瓦锡是以不同的方式看自然界的。同时在不求助于他以不同方式去看的被假定为不变的自然界时,经济原理会极力要求我们说,在发现氧以后,拉瓦锡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
我立刻想问一下避免这种古怪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一个外加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从伽利略的著作的最著名的部分得来的。从远古以来许多人都已经看到一个重物体在一根绳子或链条上来回摆动直到它最终静止为止。对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来说,他相信,一个重物体是靠它自已的本性,从较高的位置运动到较低的位置上的一种自然静止状态。这个摆动的物体只不过降落有困难。它受到这根链条的约束,只有在一段曲折的运动和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在它的低点上达到静止。另一方面,伽利略观察这个摆动的物体时,却看到了一个摆,这个物体,几乎是连续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运动,一次又一次以至于无穷。伽利略在看到这个重要事物的同时,也考察了摆的其他各种性质,围绕着它们建立了他的新力学的许多最著名的和有独到见解的部分。例如,伽利略从摆的性质为重量和降落速度的独立性,以及为斜面上向下运动的垂直高度和终点速度之间的关系,导出了他的唯一充分而又完备的论据。①所有这些自然现象,他都是以不同于他们以前已经看到的方式去看待的。
洞察力的转移为什么会发生呢?当然是由于伽利略的个人天才。但是要注意,在这里,那种天才并不是以对摆动物体的更准确或客观的观察来显示自己的。形象地说,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感觉一样准确。当伽利略报告了摆的周期不依赖于振幅,因为振幅是 90度。他对摆的观点使他看得比我们现在在那里能发现的更有规律得多。②不如说这里已经涉及的似乎是天才利用知觉的可能性使一个中世纪的规范转变有了价值。伽利略不是完全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出现的。相反,他是被培养为用原动力理论去分析运动的,这是一种中世纪末期的规范,这种规范认为,一个重物体的连续运动是由发动这种运动的发起人注入其中的一种内在力量引起的。琼·布里坦和尼古拉·奥斯姆,这两位十四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使原动力理论具有最完备的形式,他们是已知已经看到伽利略所看到的那部分摆动运动的第一批人。布里坦把一根摆动的绳的运动描写为当这根绳受冲击时原动力首先被注入其中的一种运动,其次,在这根绳对着它的张力的阻力转移时,这种原动力就被消耗了;然后张力把这根绳带回,直到到达运动的中点,注入增加的原动力;此后,这种原动力使这根绳向相反方向转移,重新对着这根绳的张力等等,这个对称的过程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后来,奥斯姆在这个世纪里对摆动的石块作了类似的分析,现在看来是这种摆的最初的探讨。③他的观点显然很接近伽利略最初探讨摆的观点。至少,在奥斯姆的情况下,而且在伽利略的情况下几乎也—样,是从原来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运动规范转变到经院哲学的原动力规范所可能有的一种观点。直到经院哲学的规范被发现以前,科学家看到的并没有摆,而只有摆动的石块。摆的产生很象一种规范引起的形态变换。
①伽利略:《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 H.克鲁和A·德·塞尔维欧译(伊文斯顿,伊利诺斯州,1946年,英文版),第8O~81,162~166页。
② 同上,第 91~94,244页。
③ M.克拉吉特:《中世纪的力学科学》(麦迪逊·威斯康辛,1959年;英文版),第537~538页,570页。
可是,我们真的 需要把区分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或者把区分拉瓦锡和普里斯特利的描述为洞察力的转变吗?当这些人在观察同类对象时真的看到不同的东西吗?有没有任何合理的观念使我们能说,他们是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他们的研究呢?这些问题不能再推迟了,因为显然有另一种普通得多的方法去描述上面略述过的所有历史上的例子。许多读者一定会想要说,有规范的改变仅仅是科学家对观察的解释,它本身是由环境和感觉装置一劳永逸地确定的。按照这种观点,普里斯特利和拉瓦锡两人都看到了氧,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观察有不同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两人都看到了摆,但是他们对他们两人已经看到的东西的解释不同。
让我们立刻说明,当科学家们改变他们关于基本物质的见解时所发生的这种最普通的观点既不是完全不适当的,也不仅是一种错误。不如说这是笛卡儿提出的一种哲学规范的主要部分,同时已发展成为牛顿力学。那种规范为科学和哲学两者都服务得很好。利用那种规范,象力学本身一样在基本理解方面已经是富有成效的,这种基本理解用另一种方法也许不能获得。但是正如牛顿力学这个例子也指出,甚至过去最惊人的成就也不能保证,危机能无期地被推迟。今天,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艺术史等部门中的研究,全都集中到使人想起传统的规范是不知怎么地歪了。科学史研究也使这种不适应日益明显,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在这里必然指向这个问题。
这些引起危机的问题还没有为传统的认识论规范产生一个可行的代替方案,但是,这些问题确实开始使人想起那种规范所会有的某些特征。例如,我尖锐地意识到,说什么当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着摆动的石块时,前者看到了受约束的降落,而后者看到了一个摆所造成的困难。这一章开头几句话甚至以更基本的形式提出了同样的困难:虽然这个世界并没有随着规范的改变而改变,此后科学家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不过,我确信,我们至少必须学会弄懂类似这些陈述的意思。在一次科学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以完全归结为重新解释个别的和不变的资料的。首先,这种资料并不是明确不变的。一个摆并不是一块降落的石块,氧也不是排除了燃素的空气。因此,正如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科学家们从形形色色的对象中收集的这种资料本身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造成的从受约束的降落到摆,或者从排除了燃素的空气到氧的转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类似解释的过程。在没有确定的资料可供科学家作解释的情况下,怎么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