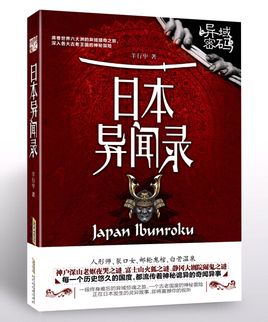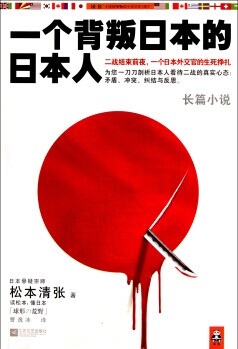�ձ��ֻ�����ʵ¼-��4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1944��1�£��վ�չ���Կ��ո��ݵصĴ�����ɨ����ɨ���У��վ�ɱ����3000���·�����ϰ��գ�����1000�����������ж�������������
���������˺���ģ�ġ���١�����ɨ������δ���أ����Ǹ�����Ŀ���ַ����Ѳ顢�߷����ж���δֹͣ����ÿ�ζ���һЩ�����ߡ���
����������ͳ�ƣ���1942�굽1944���3��䣬���վ�ʵʩ�����������Ĺ����У���1��54���˱�ɱ�����ﲻ�����������������������ˣ���1��5���˱������й�����ȥ������7�������գ�3����ͷ�������ߡ�1941��ͳ��ȫ�����˿�16���ձ�ս�ܺ��ٵ�10���ˡ����������������¡��ί��ʷ�칫�ҵĵ��顢�о����ϣ��й������ѽ��˵�����ϻ����顣�ܶ���֮���վ���ҲӦ����α����������У��������¡���ھ�ɱ�����Ⱥ�������11���ˡ����ѵ������ձ����Ƶ���ν�����ǹ���Ȧ���ġ��������𣿡�
�����������������ϯ�C�Ĺ�����������һ���ָ壬��������д�ģ���1���֣��������ԭ�ĵ�һ���֡����ָ��dz�ƽ�ṩ���ҵĸ�ӡ����ֻ��ӡ���й���¡�ء�����������һ���֡���
��������д��ƪ���µ��˽к�ϯ�C���վ�ռ��ʱ����������¡�ؾ���ơ�Э�ͻᣨЭ���վ��Ŀ�����֯���ĸ����ˡ����ڴ�֮ǰ����һֱ�ھ��������صĶ������з��ۡ���Э���վ��㡰���١�������ɨ����������Э���������Ⱥӽ���ͳ�Ρ��л������������Ժ�����ͨ����1951�걻����1954�꾭��¡�ط�ͥ�д�����ͽ�̡����ָ����������������������Լ���������������д�µĹ��ʡ����ݽ��ܣ���ϯ�C����1960����ͣ���ס������������������������������ν������ֲ����Ľ���ɡ���
����������ϯ�Cд�Ĺ��ʣ���һ�ݺ��������ϡ�ͨ�������Խ�һ��Ū���վ�����¡��ʵʩ������������������ݺ�ϯ�C�Ĺ�����1942����ǰ���վ��㿪ʼ����С��ģ�ġ����ҡ�����Ҫ�ɵ��ص�α�����ַ�����ʵʩ������˷�ʽδ�ܷ�ֹ��·���Ļ�����ԣ���1943�괺��7�£��վ���ȫ�������˴��ģ�ġ�����������������ס�����ش����͡����Ҳ��塪�����Ų��䡱��Ϊ�����조�������������Ƕ�Ա����¡�صĿ������������ӡ����졢Э�ͻ�ĸ����쵼�ˡ�����峤�Լ��վ��ܱ��ӣ�����Ҳ�ᵽ��ǰ����˵��ľ������֣����������Ϲ����߷��ر��ӣ���α������������������¡�ص�ȫ���վ��������ӽ����조������������
����������ϯ������Ĺ��ʡ�
��������1943��3����6�½��С�ȫ�ظ��弯�ҡ������ڼ��ڸ��������ɡ����ҡ������з����ߺ��������ڲ�����ߣ����Է����վ��۴�����Ȼ��ʱ��ֵ����ʱ�ڣ���ũ���Dz��ò���ȫ���Ͷ���������ɡ����ҡ�������ûʱ���ֵأ��ɴ˵�������̻ġ���
��������ũ�������Σ�ֻ�����ű�ʹ�������Լ��ķ��ݣ�ÿ���˶����żҾ�֮��Ķ���ȥָ���ġ����Ų��䡱������ǣ������Ų��䡱��û�н����ݣ������Ķ���ֻ��ɢ���ڿյ��ϣ�������Ů���ٶ��ڿյ����ס��1943��4����Ѯ����ָ�����ҵĸ���ũ����Ů��������װ�������ʹ��ȥ�������Χǽ����¥��ͬʱ����Ҫ��ʱ���֡�ʩ�ʣ�������ơ���ˣ������ʱ��ũ���ֱæ�ò��ɿ�������
������������7�£���һ�ڼ��������������ˡ�ȫ��19����壨��һ��������Χ���м���С�壩��ÿ�������Χ������10����20�����Ų��䣬����200�����ӦΪ207����������У������
���IJ��֣���һ����������ս��
ˮȪ���ġ�ͯ��ϱ�����Ӣ��6��
���������㼯�ҵ�ͬʱ���վ��ְѰ�·�����ɽ��һ����Ϊ����ס�����ش����������ﲻ�����ϰ��ճ��롢��ס�Ͳ���ũ������ڡ���ȫ��ס�����ش���������������Ҳ�������档������Ҳ���˼�ֲ�ȥ���Ų��䣬������ɽ����ֶ������ⲿ���˶����Ǿ�ס������ɽ������������һ����ũ��
���������վ�����¡�ؽ��дҵ�ͬʱ�����ڳ��������ϵļ������غ���¡�����ڵĵ���ʵ���ˡ����Ҳ��塱�������ڳ�������15��ĵط�����ǿ��ũ�����ˡ���������������������ʱ�ձ��˴���˵���������Ĺ��̼�������ͬ���ﳤ��һ�㣬�Ժ�Ϳ������������·������
����������¡�صĴ�������ɺ�200��������Ų��䡱�ﶼפ����α����������װ���졢�ط����·�ӡ�����Ҫ�ľݵ㲿�仹���йض�����α�������������ַ��ӡ������ס�������������������������������
����������ϯ�C������֤ʵ�ġ����Ų��䡱״��ֻ��һ�ٲ��֣���ƽ����������������ϸ�ظ�����������Щ���ϡ����ԣ������罫��ƽ�����ĺ�����������������������ô������һ���̶��϶�ȫ�ص�״���и�ȫ����ʶ�����潫���н�����¡�صļ�����������
�����������Ѹ��塱���ҵõ��IJ��ָ�ӡ���У�����һ�ݺ�ϯ�C�������漰1943�괺��ʱ�ڡ���Ȧ���и㡰���١���ɱ�¼��IJ��ϡ����¼���������¡������Ӫ�塣��
������������Ӫ��ġ����Ų��䡱��������Ȧ����������¡�سǶ���Լ70����ĵط���1943�괺�ڣ��վ�����¡�؝��Ӵ�50�������Ȧ���ڸ㡰���١�������2000���˱����������н���ñ����ľ������200���˱�����������Ӫ���һ�Ҵ�լԺ��վ������������������������ڱ���ĵ��ϡ�����Ѳ�ӵĺ���������������ĸ�����վ���������ù�����������3���ʱ�������û��û�ȣ�ÿ���˶��ܵ������̿��ʡ����ʵ������С���·�����Ķ���������˭�ǰ�·����˭����·�������ţ���·���ռ��Ĺ�������Ϊ˰��Ķ��������Ķ��������˭˵��֪�����ͱ�ȻҪ�ܵ����̡�����ˮ���̷����ر�ͥ�������ձ������Խ�����Ѷ���ɴ˿�֪������һ������Ԥı�ġ����١���Ŀ�ľ���Ҫ��������������������ٳ����ĺͱ�ɱ���Ĵ��Ǵ�ñ���ˣ�����һЩ�ǡ����١�֮ǰ�ͱ������ϵĴ�����֮�⣬�����ط����˺��١���
����������ñ��������Ӫ������Լ1��5�����ɽ�����ɽ���е�һ����С�ġ���Ȧ������ס��67���˼ҡ��������ʵʩ�����١���ҪԱ�����������ʱ������ҪԱ������ڴ���İ�·�����Ա���У�����¡�ص�ʷ���ŵ��飬��������Ϊ�����ռӢ������ɽ����ռӢ�ڿ�����������ʱ������·�����Ա����»��У�����ɽ���ܡ�������У��������·�������ˣ�������ȴ��ǰ���������ձ��ܱ��;����ַ��Ӱ�Χ�������73�����Ӻ���ץ�ߴ���������Ӫ�塣�վ��Դ�ñ���˵Ŀ������������ģ�����Ҳ����п�ġ���ϯ�C�Ĺ���������д�������վ��ú�ī֭�ڴ�ñ���˵ı��������˼Ǻţ��ú�īˮ�������������ı��������˼Ǻš����Ǻŵ�����ζ��ʲô����ʱ����֪�������˾������³��ˣ�����2��12�գ����磬��������ÿ�˶��õ������ࡣ�˺��ձ��ܱ��ӽ�Ժ˵�Ѵ�ñ�����˶������ͷš��÷��DZǼ��ϴ���ī֭�Ǻŵ��ˣ�����Ǻŵĺ���Ҳ���٣�Լ��120���ˣ���վ�������ܱ����ַ��Ӱ����Ǵ�������Ӫ��ġ����Ų��䡱��ߵ�һ�����ǰ��������ͦ��ǹ����ɨ�䣬���������ߴ�120���ˡ����г��˴�ñ����֮�⣨����¡�ص�ʷ���ŵ��飬�ڴ˴μ�����ɱ���д�ñ����30���ˣ��ڱ�����73���У�����30���˱�Ѻ��ȥ����¡�سǣ��ô������������Ӫ����صĹ�69�ˣ���9����ɱ����30��û�������ˡ���ˣ�����Ϊ���Ѹ��塱��������У�����������ӹ���20�����ˣ���Ȧ���Ϲ�10�����ˡ�Ժ��ʣ�µ��ˣ��ڶ���ȫ�������سǡ���α�ɱ����120�����У�ֻ��3����������������
����������ñ�������ï�־��ǵ�����3���Ҵ���֮һ������������ʱ����30�������ų�һ�ӣ�Ȼ������һ���µ�����ȥ�ġ�120���˲���һ��ɱ�ģ����Ƿֳ�3����еġ���������ï������ǰ���һ�飬�������Ž������뻢�ڡ���˵������Ѷʱ��װ�ưͣ�������Ҳ����˵��������˵�����������û���ܵ���Ѷ�������°����磬���DZ����˳�������������ѩ�������ţ���Χ������Ȧ��һ��Ȧ����������̧ͷ��̧ͷ���˶����˹��������˸������ط�����ÿ��һ������ˣ���ñ������ÿ�˸��������ࡣ��ñ�����˺��ţ�������Ҫ�ؼң�����ʱ���ӹ���˾�����ĸ���Ҳ�����ñ����֮�С�����ҹ�ﱻ������¡����֮�⣬��������ʣ�µ�30�����ų���һ�ӣ����ܵ���Ѻ�ţ������ǴӲ�������˳�������������ǰͷ���˴��š���ʱ������������������t��̨��ȥ�����������¿ӵ�ʱ�������Ⱦ��ܡ����������������������δ����ҵ�ͷ�ϣ��ְ���һǹ���ӵ����ҵ���紩��ȥ�����ǣ��һ���ƴ�������ţ�������ɽ�����������˻��ڡ�����
����������ñ���������ܵ��Ⱥ�������������Щ���ⳡ���緢��֮�����ڡ����Ų��䡱�Ĵ������ֱ�ӿ��������վ�����������ʡ���һ������8�˱�����������62�������������������������¡�ص�ʷ���ŵ���֤ʵ������βҰ����ձ�Ͷ������ñ���屻��α���ݲ�����139�ˣ�ռ���˿ڵ�57��7����������У����ʣ�µ�102�˶������˺ͺ��ӡ����˺Ѹ�����¡�����ѽ���Щ��¼��������ϣ�������Ϊ���Ѹ��塱��������������1942����ǰ�Ĵ�ñ��������Ӫ��Ѫ��߰ߵ���ʷ�����Ҽ�������¡������13��������������֮�������ʷ����
���IJ��֣���һ����������ս��
ˮȪ���ġ�ͯ��ϱ�����Ӣ��7��
����������ο���ɱ����¼������ֻ�dz�����������¡�ص���Ҫ����Լ��˻ᴩ����ʱ���������ߵ�һЩ�������û��ʵ��ȥ������ɽ���ո��ݵغ��ũ�塣��֤ʵ���վ��ڸ��زп�������ˡ�����������ͬʱ��ɱ���������ϰ��գ��������ﱻ�������¼�����ġ���ʵ˵������д��ʵ�ص��鱨��Ϊ���ĵ�һ��ʱ������������Ϊû�ܵ���¡��ʵ�ؿ�������µIJ���������й������ܿ��Ÿ��أ���ʱ���������ҲҪȥ������ʡ���
������������������һ���潲��������¡�ر����Ĵ������Ϻ͵����¼������˳���ؿ������˽��¡�����ڸ��ص�������е�ֻ��һ�����ձ���һ֪���ص�������У��������Ҳ����˵����������Լ��������ġ����ǡ��л�����̵�˵������Թ��֮���ģ��Դ���������һ����֫���������Ŀ־�к������С����ձ����������У�����Ҳ�������������������ͬ���ĸ����𣿶�����������ԪԪ�꣬Ҳ�����˻�Ա��������ҷ����˿���������Ѫͳ����������ָ�𡣡�
���������������꣬��ʷѧ�����ѵ��ġ�ϲ�����Լ��ij����Ŀӳ�ڴ��¾������Ϊ�����ࡣ��ʷѧ�Ҿ���Ҫ�������ձ�����ÿ����������ij��Ķ������DZ��ʵĶ�������һʱ�ģ�������Ҳ��ۣ����ر�¶��������Ϊ�Ҽ��ţ�ֻ��������������ȫ��ؿ����ձ�����ʷ����
����������Щѧ�����ң�����ʷѧ�����˻����������ϻش𣺡�������߱ؾ���һ����ֻ����Ϊ���������ȷ�����ͻᳳ������������Σ���Ԫ��������Ǹ��ġ����������ȥ���й������δ������ȥ����Ҳ��֪�����˻��Dz����ˡ����Ҳ���ӱ��濴�ձ������ȥ����˵���ڰ���������Ѻ�ʷ�������ﲻԸ���ձ����Ե���һ������ʷ���������Ҳ�Ǹ����ˣ������뵽�Լ����ձ���ʱ�����й��Ҵ��֤����ǰ��û��̸Ц�������ˡ���
�����������ǣ�����ع�ͷ���ٿ�����ʵ�����÷ֱ棬�Ҿ���һ����С�����ڸ���ѹ����ǰ���ֵ�ʮ���������ˡ�д������Ͳ��ɵظе��Լ�����ƣ����ʵ���ϣ�����Ԫ�����Ѿ�ȥ���˱��������֮��Ŀ��ո��ݵء�����ɽ�������Ǵ���н�������������ʤ�أ���һ��������ɽ��ɫ��һ����ͬ�еij�ƽ��̣�ʹ�������dz��˵������ʵ�ص��鲻��������ƣ�������һ�����е���һ����ʷ�о��ߵĵ��鷶Χ���о����ԡ���һ����Ҫԭ���ǿ��˱����β��õġ��ֻ��վ�����¼���ڶ��������ݣ�ʵ�����ǿ��˵�һ�����嶯֮�б���Ȼ��������Ϊ�����ĩ��¼�Ͽ��ǵ��Ƿݡ�����ս��ʱ�ںӱ��Ұ�ͳ�Ʊ����������ң���е������·�ͬС�ɡ�����
�����������м����źӱ�ʡ������ʵʩ�����������ij������Ա����Ⱥ�ʡ�������֣��������Ž�һ�ξ�ɱ��10�����������յİ�������Ȼ�����Ҳ������·��սʿ���ڡ����磬����ÿ����п���ʱ�������������˱�ɱ���Լ�Ů���ڰ�·�ϱ�ǿ�����ɱ�����¡���Щ���ֻ���������Щ������ǿ��ץ���������������䲻���ߡ�����ͳ��һ��������е����ֿ�֪���������˾ߴ�8��1���ˡ���֪�����������������ֺ����кθ����أ���
������������֮����˵�����¡�������Ϊ������Щ�����뱾�����ϵ��������в�ͬ�����磺³��������������Ͱ���һЩ��·���˲�Ա����֮���й������Ժ��ھ��÷�չ��ͳ�ƺ��˿�ͳ����Ҳ������ЩǷ��ѧ�ԡ���
����������ô����Щ���ֿ����𣿻ش��ǻ�����ȷ�ġ���Ȼ������ֱ����Ͼ�����ɱ���������������࣬�����Զ�������ֳֿ϶�̬�ȣ���������Ϊ8��1���������̫������Щ����Ϊ������ս������������ˮȪ����4��6���ʬ���⣬�����ڵ��������Ϳ���������֤�Լ�ͳ�����ϡ����⣬�������൱��ũ���վ�ǿ��Ѻ�͵����������������䲻����Ӧ�ó��ϣ�����ͳ�Ʒ�����ͳ���˿ڵķ�ʽ���źܴ���죬��Ϊͳ�ƾ����˿�ʱ����Ҫ���յ����˿ڵ�ÿ��ÿʱ�ı仯�������
���������ڡ��Ͼ�����ɱ���������ϣ�һЩ����ɱ���ձ��˼���ڮ���з���ͳ�����֣�˵���й�������ȱ�����ݣ����ɿ����ȵȡ���ʵ����Щ������������ij�ʶ�����������ܺ���һ����ͳ������Ҫ�ȼӺ���һ�������ס���ȷ���ѵ��ǵ�����Щ��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