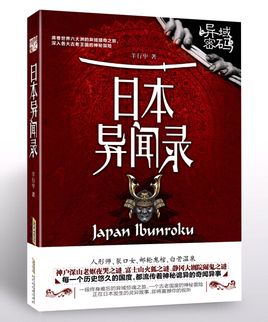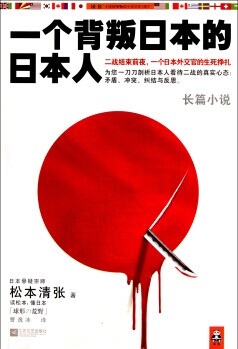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5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方的上述说法是否有待考证暂且不论。不过,日本战败时刚晋升为中将的铃木,却在战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阶下囚,他在军事法庭受审时的情景也已被胶片记录了下来。面对法官的询问,铃木回答道:“当时是我命令部下去执行‘三光作战’的……因为只有通过‘三光作战’才能确保日军的势力范围。联队长也是按照我的意图才对中国人施加了暴行,我所到之处都命令部下实行‘三光政策’。”(《又一个三光作战》)铃木为此受到了有罪判决,法庭指控他应对长城线以南的“无人区”及“无人区化”政策的实施负有全部责任。
庆幸的是,铃木在服刑近十年后被释放回国了。据说因他是给中方留下证言后,才允许返回乡的人,所以,此后他也以平静的生活方式渡过了余生。几年前,我会见了一位据说是当年曾给铃木当过副官的人,他告诉我说,铃木是一位沉默寡言,且又具有古代武士性格的人。
按道理说,冈村大将和原田师团长都应在“无人区”问题上负有责任。但想不到的是,铃木却将上司和属下的责任全部尽量地承担了下来。回国后,他对此既无怨言也不做任何解释,始终保持着沉默。在这点上,冈村与铃木确实有着本质的差别。另外,在比铃木级别更低的下级军官中,原承德宪兵队的木村光明也受到了有罪判决。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应对长城北侧的屠杀负有责任(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因顾及本人的名誉,故而做了留姓隐名的处理。但横山光彦的《望乡》及岛村三郎的《从中国返回的战犯》著作中,在描述审判情景时,已将木村的全名公开了)。另外,在这一问题上,陈平先生曾指出:“1942年8月上旬召开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兵团长会议上,冈村宁次总司令官亲自策划部署了设置‘无人区’的具体计划。”对此,中方的调查报告中也明确地指出:制造“无人区”的最高责任者就是冈村宁次。
据说,除了长城南北地带之外,日军还在山东省与河北省西部的边境地带设置了“无人区”。对于那里的受害情况,也只能是按照每个事例进行详细调查后,才可得出结论来,而此次着重调查的只是长城线北侧一带。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3)
在兴隆县的调查中,娄平先生说过:“在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中,被日军屠杀或非正常死亡的就有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若将此数统计在内,那么8年间全县被杀害者则高达11万人。
在其相邻的宽城县,“在‘无人区’内遭检举者达21 750人,其中被杀害的有 13 400 人。另外,在‘人圈’(集团部落)中被冻、饿、病死的又有8500人。”(《宽城县党史资料》)据陈平统计,仅在热河省一侧,日军烧毁民房380余万间,掠夺粮食96亿斤,抢走家畜24万头。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我曾介绍了“水泉沟万人坑”的情景,据说,被日军杀害后扔在那里的遗体就有46 000具。其中多数中国人是因反抗“无人区化”而被关进了承德监狱。其后,他们或在狱中遭杀害,或被押往水泉沟处死。
以上就是日军在“无人区”实行“三光作战”的部分实况。对于日军的这些暴行,中方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对此笔者已在第一章中做了介绍。我认为在中方选编的文献中,其侧重点大都是记述抵抗作战的内容。其实,在日方的文献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华北治安战》也好,还是其他的回忆资料也好,以至连本书所撰写的内容中,也都大量记述了双方作战的情节。不仅日本军方,就连日本政府也深知,他们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抵抗。例如,“伪满洲国治安概况”第8号(1944年7月4日)上就登载了许多这样的内参报告:
“4—(4)、关于兴隆县内地方武装民众之状况——去年6月,与我方设置无人区的同时,敌方也做出了相应对策。他们以无人区为中心,将武器分发给了部分民众,巧妙地开展起了武装组织工作……目前,共军已在22个村庄内,设立了民兵武装自卫队,队员人数达76名……有迹象表明,这些民兵自卫队在配合共军作战的同时,将可能发展成一支地方的作战部队。”
“5—(2)、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冀热中共迁滦丰联合县政府设立了‘对敌粮食斗争委员会’。同时,为了解决粮食不足问题,该县政府又制定了新征税法,以此来限制粮食、物资等向辖区外流出。”(外务省资料馆所藏)
虽然日本政府深知中国人进行了抵抗,但它能否理解中国人内心的感情及抵抗精神,这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说,这种理解上的差距不仅持续到日本的战败,而且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仅如此,它将继续影响着早已对战争失去了责任感的国民。
后记战争的受害与施害
归根结底,“三光”或“三光作战”这类用语是中国人命名的。它们的含义是指在日中战争(中方称为抗日战争,而对我等历史研究者来说,则可称为对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对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有计划、有系统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等作战的总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人一提起日中战争及日本人当年的行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光”及“三光”政策这类用语。不言而喻,如果当年日本人不特意去中国干下这些野蛮行为的话,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出这类用语了。日本人之所以照搬使用,是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那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对此,我倒丝毫未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尽管有人指责说,为了追随中国人,日本人竟无意识、无条件地使用起别国的语言了,简直是岂有此理!但我却并不那么去理解,因为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原封不动地照搬使用从中国传来的用语及字句之事,早已是不胜枚举了。与此相反,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词汇立即变成中文固定用语的事例也极为普遍。用语上的争论暂且不提,但日中战争中,日本究竟使中国蒙受了多大损失呢?对此问题,我已在《世界》(1994年2月号)一书中做过了介绍。即中方统计的数字是:中方人员损失为“2100多万人死伤,1000多万人被日军杀害”;中方经济损失为“直接损失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权白皮书》1991年10月版)。另外,1995年5月,时值苏俄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胜利50周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应邀出席莫斯科举办的庆祝仪式上发表的讲演中说,日中战争期间,中方的受害者为3500万人。但因他未提及此数字的根据,所以笔者仍沿用前述的中国官方数字为依据。
如前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者总数为1000多万人,其中战斗人员牺牲总数为321万人(包括八路军的112 245人在内),两者相减后,剩余的600多万人则属于无辜百姓了。另外,假如把被强行抓走的人员也计算在“死伤者”之中,则东北满洲就有200万人(《伪满洲国史》),而华北又有250万人。仅两地区合计就高达450万人。如此计算的话,牺牲者人数还会更多。
但事实却是,在1992年提交给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议案中,中方又对日中战争期间的损失数字重新做了更正。其中,被日军杀害的“非战斗人员为1000万人”,“被强行抓走的为300万人”,“整个战争中,中方的经济损失为1兆美元”。由此可知,在有关“被强行抓走的”的人数问题上,今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另外,华北地区因“三光”政策而受害的人数就有250万人,这一数字几乎占了被杀害者总数1000万人的四分之一。如此看来,有时甚至觉得在日中战争中,“三光”问题所象征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及“从军慰安妇”等问题。尽管如此,除了一部分日本人外,像“三光”或“三光作战”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竟没有成为日本人深刻反思的话题,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不仅如此,人们还淡忘了对那场战争的责任感。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4)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尽管“三光作战”下的每一个受害者事例都令人发指,骇人听闻,但所涉及的对象及范围都过于庞大,给人一种无法掌握问题核心的感觉。因此,人们便对这种施害事实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
原因之二,尽管以冈村大将为首的一批人确实是“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剔抉”的作战指挥策划者及当事人,但他们在战后却诡称:既不清楚“三光作战”,也没进行过这种战争。况且,战败后又由于未能受到战争责任的追究,故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嚣张气势。
原因之三,在日本人的心中,很多人既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同胞会犯下那种残酷而又非人道的行为,也不希望这些人因此而受到惩罚。而那些追随冈村仍坚持对屠杀和虐待行为持否定论的人,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才更加提高了他们的反对调门,因而也就逐步淡化了人们对战争责任感的认识,我想原因大致如此吧。
因此我认为,负战争责任的首先应是日本政府。笔者在文章中也曾屡屡提及,正是由于御前会议及日军大本营确定了这一基本方针,当地驻军最高司令部才进行了“三光作战”指挥和部署,其下级部队才进行了具体实施。这种组织命令系统的结构理应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此外,从铃木启久少将承认对“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中可知,虽然他个人已承担下了全部责任,但铃木的直接上司原田师团长以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将,难道说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吗?我想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逃脱这一干系的。
然而战争结束后,铃木碰巧被中共方面逮捕。在受到了军事审判后,他坦率地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勇敢地承担了战争责任;与此相反,冈村在被国民党方面逮捕,又被无罪释放后,不但否定了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拒绝承担其战争责任。作为日本人,我们应如何去评价这两者的态度呢?这不仅仅是日本人如何反思过去的历史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日本今后要走哪条路的重要问题。
总之,现实状况是,那些施害的日本人——我们的同胞,有的正在销毁当年的证据,有的则极力去否认受害者的证言。而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日本人来说,却不得不洗耳恭听那些受害者们的倾诉。一旦中方幸存者提出某种证言,日本人必然会连连摇头批评说:“那只不过是中国人夸大其词的惯用手法而已。”只要受害一方没提出新的指正,这些日本人也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了。此外,还有很多当年曾亲临其境的老军人们,也都默默地将事实真相深藏在内心,直至最后死去。我非常理解这些人的沉默心理,但更应该想到的是,受害者一方也是有兄弟、娇妻、恋人及子孙后代的,他们也是辛勤地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啊!“既然中日两国已恢复了交往,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是我此次走访大屯村时,一位老婆婆向我诉说的话语。如果稍去体会一些她的心情,我们日本人难道不应该坦诚地说出过去曾加害过中国人的事实真相吗?难道就不能在赔礼认罪的同时,发誓再不去干当年那种愚蠢的行为吗?
笔者在前言中曾讲过,人类最悲惨的境地莫过于战争了。虽然人们都希望日常生活中不必刻意去努力也能消灭战争,但这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罢了。应该承认,如果没有集团式的发狂,自然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但暗藏在人们心中的仇恨、偏见、欲望一旦被利用或被煽动起来后,人们的善良及平和心也就变成了盲目的服从,由此也就爆发了战争。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认为,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日本人决不能忘却过去那段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长城线上的大屠杀
——兴隆惨案(节选)
(日)仁木富美子
横河行——“无人区”是如何建造起来的
仁木富美子1995年3月22日摄于金山岭长城离开兴隆县城后,汽车一直向东驶去。道路两旁是悬崖峭壁,汽车在弯曲的山道中疾驶。
这条山道也是当年日军战败后,向遵化、唐山逃跑的惟一之路。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的深山之中,它一直穿过兴隆的中部向东流去,出了龙井关后与黑河汇合,然后一并汇入滦河。獐猖山地处八品叶以东,石庙子以北,它也是横河的发源地。横河在此向北迂回,后在半壁山一带与潵河汇合。五指山在横河的东北部,而车河则流经于五指山与西北的五凤楼之间。柳河从发源地八品叶流向南部的六里坪林场,然后通过兴隆县城向北,绕个大弯后南下。流经八卦岭以北,它与车河同时汇入从承德来的滦河,并注入潘家口水库。
所有这些河流都在东北方划了个同心圆,而且河与河之间,都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来作为它们的天然屏障。
羊羔峪
半壁山镇地处兴隆县的东部,镇里设有公安分局。公路由此南下与唐山地区的遵化相通。
从半壁山沿横河北上,绕过老虎沟水库后,便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山路。右边的河套中,到处都是被夏季洪水从山上冲积下来的鹅卵石,而且水流很浅。这条山路通往羊羔峪、水泉子、马架沟。这一带也是当年在集家并屯的名义下,最先实行“无人区”的地方。
张福廷(76岁)的口述,采访时间:1995年3月22日
这里的集家并屯实行的最早。1939年11月警察来到这里,说是让天桥峪、羊羔峪及厂沟这三处的百姓,在两天以内,全部迁移到安子岭和双炉台去。第二天的上午,十几名警察又来督促搬家,并拿走了值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