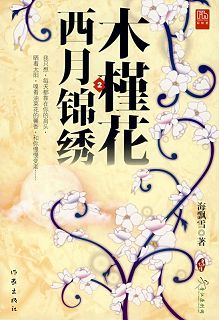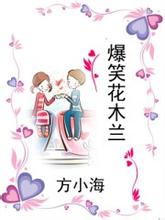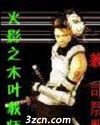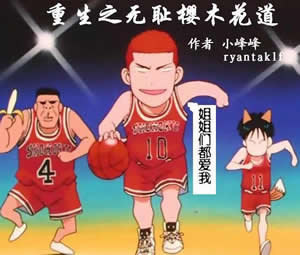金克木_书读完了-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仍有不变者在。这不能说是“继承”。这是在变化中传下来的,不随任何个人意志决定要继承或抛弃的。至于断了的就很难说。已经断了,早已没有了,还说什么?那也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意志而断的。要肯定过去而否定现在,或者要否定过去而肯定现在,都是徒劳无功的,历史已经再三证明了。
传统思想要古今互相印证。今人思想可以凭言语行为推断,古人思想只有凭文献和文物。可以由今溯古,也可以由古见今,将古籍排个图式以见现代思想传统之根。我想来试一试。
想看清自己的可以先对照别人的。有个参照系可以比较明白。那就先从国外当代思潮谈起。
二十世纪,再短些说是从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的五十年间,国外的文化思想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便是对语言各方面的再认识。向来大家以为语言只是工具,思维的工具,思想交流或通讯即互通信息的工具,手段,是载体,容器,外壳。
现在认识到语言不仅是工具,它本身又是思想,又是行为。语言不止有一种形式。
口语、书面语以外不仅有手势语、艺术语言、科学符号语言,还有非语言。语言还原到逻各斯。这个希腊字在《新约。约翰福音》开头译作汉语的“道”:“太初有道。”恰好,汉语的道字是说话,又是道理,又是道路。道和逻各斯一样,兼有语言、思想、行为三义,是言、思、行,也是闻、思、修。由此,对语言分析出了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和道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二是语言思维和非思维,或说潜在的意识。前一条是通过语言学的认识。后一条是通过心理学的认识。这也可以用从逻各斯衍化出来的另一个字来表示:逻辑。那就是逻辑结构的,或说是理性的;以及非逻辑结构的,或说是非理性的。这样较易理解,但不如用逻各斯包孕较全。就我前些年见到不多的外国有关新书原文说,平常所谓人文科学或思想文化或文化思想中争论的问题,核心就在这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文化上到处是两套思想和说法好像水火互不相容。我看这可以和我们的传统思想的坐标轴通连起来观察。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两种道:常道,非常道。孔子说:“天下有道”,“天下无道”,也是两种道:有道的道和无道时行的另一种道,或说是无道的道。他们说的是不是逻辑的和非逻辑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结构性的和非结构性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确切说,彼此大有不同,但概括说,是不是穿长袍马褂和穿西服的不同?是不是中国话和外国话的不同?我看中国和外国的思想的不同不能笼统说是上述两套道的不同。中外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各自有这两套道。外国的,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前后有不同,或说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不同。后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不论怎么大,仍属于逻各斯一类,不属于非逻各斯。前苏格拉底的毕达哥拉斯却能把勾股定理看成是神秘的原理,逻辑的仿佛成为非逻辑的,数学变成非数学。赫拉克利特论逻各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同,而和印度有些佛经中说的惊人相似。
基督教神学采纳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好像又回到了苏格拉底以前。我们震惊于外国的科学发达,常忘记或不注意他们的神学也比中国发达。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都通晓神学。
现在回到中国的坐标轴。孔子和老子的道是在一条线上各讲两种道,彼此不是两极端,所以当出现另一条线上的异端的道时就混乱了。那一端不叫道而叫法:佛法。汉代开始在西域流行,汉以后迅速扩展到中原以至全中国。这法和原来的道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是“势不两立”的。这是不是逻各斯和非逻各斯的对立?
有一些,但不全是,因为佛法本身也包含了这两种的对立。佛法内部的争吵和斗争以及对外的努力一致,比中国原来的孔子之道和老子之道的对立更激烈得多。
仔细看看,孔、老两家的道,也像佛家的法一样,本来也包含着这种对立。因此异端来后可以由斗争而合并。说中国和外国的思想对立不是确切的说法。说有两种思想的对立,在中国和外国的表现不同,主从不同,比较合乎实际。
从以上所说看来,很明显,我是站在逻各斯或道或逻辑或结构一边说话的,因为我要用语言说话。若是要我从另一边说话,那我只好不说话,无法说话,或者只有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用非结构性语言说话,或者用形象的或非形象的艺术语言说话,可惜连艺术语言中也避免不了这种对立。
现在我把上面想讲出的意思缩小到文献范围以内,再缩小到中国的汉语文献,包括翻译文献,试试看能不能理出一个系统来。凡是系统都有漏洞。没有网眼不能成为网。但是有建构就容易看清楚。当然这是“但观大略”,好比格式塔心理学的看法,一眼望去看那张脸,不必仔细分辨眉毛眼睛鼻子嘴的几何图形,就立刻能看出是美人西施还是丑女嫫母,不论她是微笑着还是皱眉毛。这样一眼望去其实并不是模糊笼统,而是积累了无数经验,包含着经过分析综合成立的不自知觉不必想到的“先识”的,否则就下不了格式塔(完形)的判断。婴儿初生,可以认识乳,但要分辨出乳以外的母亲和其他女性还需要积累。他不会说话,用的是非语言思维。我这样用心理学比喻,正像国际上近几十年不少人试从逻各斯去说非逻各斯那样。其实这也是中国从前人用语言说明非语言那样的。以上我所说得太简略,不能再展开,对于已知近几十年中外有关情况的读者来说,不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怎样,都会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每人心中都有自觉和不自觉的自己的思维线路,网络系统。我所说的可能对别人有参照的价值。
简单说,我想从文献中追中国传统思想之根,追到佛“法”的“六经”和孔、老的“道”的“六经”。先说“法”,后说“道”。文献中只列出“经”,因为这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是思想的根。蔡伯喈的《郭有道碑》文中说:“匪唯摭华,乃寻厥根。”可见现在常用的“寻根”一词在文献中也是有根的。莫看枝叶茂盛四方八面,追到根只是一小撮。人人知道的才是根,但是彼此题目相同,作的文章不一样。
先说外来的佛法的根,只看译出来又流行的经中六部。
一、《妙法莲华经》。这是一部文丛。思想中心是信仰。任何宗教离不开信仰,没有信仰的不是宗教。有信仰,不叫宗教也是宗教。信仰属于非逻各斯或非“道”,不能讲道理。讲道理无论讲多少,出发点和归宿处都是信仰。有理也信,无理也信。信的是什么?不用说也说不清楚。讲道理的方式多是譬喻或圣谕。对一个名字,一句话,一个符号,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这就是力量的源泉。这部经从种种方面讲说种种对佛法的信仰,不是讲佛法本身。信仰是不能分析的。信仰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这就是非结构性语言。妙法或正法如莲花,也就是莲花。经中有大量譬喻。通行鸠摩罗什译本。读任何一品都可见其妙。有原文本,但不一定是鸠摩罗什依据的本子。这类文献在古时都是口传和抄写流通的。
二、《华严经》。这是更大规模的文丛。思想中心是修行。仅有信仰还不成为宗教,必须有修行。修行法门多种多样。修行有步骤。经中说明“十地”、“十迥”、“十行”、“十无尽藏”,“十定”、“十通”、“十忍”、“十身"以及”五十三参“、”人法界“等等境界、层次、程序。不管怎么说,切实修行才知道。空口说信仰不能算数,要见于行动。没有行为,一切都是白说。修行境界如何美妙,那就请看”华严世界“。”华严“就是用华(花)庄严(装饰)。
汉译有八十卷本流行。还有六十卷本、四十卷本。部分有原文本。
三、《入楞伽经》。这也是文丛。和前两部经的兼有对外宣传作用不同,这部经好像是内部高级读物,还没有整理出定本。思想中心是教理,要求信解,本身也是解析一切,所谓“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宗教也要讲道理,佛教徒尤其喜欢讲道理,甚至分析再分析,但不离信仰和修行。这是逻各斯,又是非逻各斯,是神学中的哲学,所以难懂。不是入门书,不是宣传品,仅供内部参考。讲信仰的,讲修行的,道理比较好懂,然而“佛法无边”,所以讲宗教道理深入又扩大到非宗教,其中包孕了种种逻各斯和非逻各斯道理,可以用现代语言解说,也就是说很有当代新义,几乎是超前的预测。对比另一部同样专讲道理的《解深密经》,就可以看出,那经后半排列三大菩萨说教,是整理过的著作。《楞伽经》的涵量广大,辨别佛法与外道的理论同异,更可显示佛法要讲的道理的特殊性。经中少“中观”的破而多唯识的立,又有脱离语言的“不可说”,在中国曾有很大影响,出现过“楞伽师”。译文有四卷本、七卷本、十卷本。有原文本,不是译文所依据的本子。各传本互有歧异,详略不同,可见原始面貌尚未确定。鸠摩罗什、真谛、玄奘都没有译,若为更多读者需要,应有一个现代依据文整理并加解说的本子。
四、《金刚经》(《能断金刚》)。这像是一篇文章,是对话记录体。思想中心是“智慧”,要求悟。这种智慧是佛法特有的,或说是其他宗教含有而未发挥的。讲的是逻各斯和非逻各斯的同一性,用现代话说,仿佛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这与《楞伽经》的分别层次不同。经中一半讲深奥的道理,一半宣传信仰本经。所说的道理不是一项而统一于所谓智慧即般若。本经编在更大的结集《大般若经》中,有玄奘译本。另有几种译本。通行鸠摩罗什译本。有原文本,不一定是翻译依据本,但歧异不大。《楞伽》、《金刚》都说要脱离语言文字,而语言越说越繁、术语越多。
五、《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心经》,或《般若神咒》。这是一篇短短的咒语体的文章。思想中心是“秘密”,或用现代话说是神秘主义。经中网罗了佛法从简单到复杂的基本思想术语而归结于神咒,或般若,即“智慧”。这本来是六波罗密多即到彼岸法门之一,现已成为独立大国包罗一切。这可以说是佛法道理的总结本而出以咒语形式。不仅末尾几句不可译,全文都是咒语。咒语就是口中念念有词,把几句神谕不断重复以产生无边法力。我们对此并不生疏。不过真正咒语读法是要有传授的。“心”,是核心,不是“唯心”的心。有多种译本,包括音译本。通行玄奘译本。有原文本。音译本也就是用汉字写的原文本,或说咒语本。
六、《维摩诘所说经》。这是一部完整的书,可以说是教理哲理文学作品。
《心经》是密,对内;这经是显,对外。看来这是供非出家人读的。思想中心是融通。中心人物是一位居士维摩诘。他为种种人以种种方式说法。说法的还有散花的天女。经中故事和道理都可以为普通人所了解接受。若说前面五经都是内部读物,《法华》、《金刚》不过是包括了对外宜传,这经就是对外意义大于对内。
有三种译本,通行鸠摩罗什本,文体特似中国六朝文。玄奘译本未流行。未见原文本,有藏译本。我不知道近年有无原文发现。
以上佛法六经,分别着重信、修、解、悟、密、显,又可互相联系结合成一系统。这里不是介绍佛典,只是查考深入并散播于本土传统思想之根中的外来成分。伏于思想根中,现于言语行动,不必多说,读者自知。
现在再说中国本土自己思想在文献中的根,也是六部经。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只需要约略提一提。书本情况和佛典的原来情况类似。传授非一,解说多端,影响极大,寻根实难。
一、《周易》。这是核心,是思想之体,不必远溯殷商,从东周起一直传到如今。这是一部非常复杂而又有相当严密的程序或体系的书。有累积的层次,又可说是一个统一体。累积上去的有同一性。思想中心能不能说是乾坤即天地的对立统一?统一于什么?统一于人。人也就是自然。统一中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有序又有变。“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真妙!这一思想成立之后就绵绵不绝持续下来,或隐,或显。“《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优患乎?”
(《系辞》)这话好极了,千言万语说不尽。
二、《老子》。《易》是体,《老》是用。这在两汉是不成问题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讲得很明白。汉文帝好“黄、老”之术。所谓汉武帝崇儒术不过是太学中博士的专业设置,是士人的做官途径,与帝王官吏无大关系。皇帝喜欢的照旧是神仙。《易》、《老》都是符号的书。《易》密,《老》显,所用的代码系统不同。两者都是一条一条的竹简书,不过《易》可以有序排列,而《老》似乎无序。两书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两面,都是上供帝王下供世人用的。如果古人不通密码,也像现在的人一样连文字都看得那么难懂,怎么能传下来?早就亡了。古人当然也是各傲其所懂,不懂就尊为神圣。由《易》、《老》发展出两翼:记言,记事。
三、《尚书》。西汉初的伏胜是秦朝的博士官。主要由他口传的《尚书》二十八篇是政府原有的和增加的和构拟的档案,自然有缺失。这是甲骨钟鼎刻石以外的官府文告集,也就是统治思想大全,是《易》、《老》的具体发展验证。这是记言的书,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还有和《易》的序列思维同类的《禹贡》九州,《洪范》九畴、五行等等。
四、《春秋》。《公羊传》本,参照《毂梁传》本。《左传》本另案办理。
这本来是鲁国记政事的竹简书,一条一条的,依年排列,是有序的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