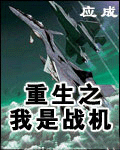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豆腐,不是渣-赤焰冷-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非一会儿就出来了,受伤的手被长长的袖子盖着,若无其事地对我笑。我却一上去就抓住他受伤的手,将他被纱布包着的手指捂在脸上,“疼不疼?”
他怔了怔,摇头,笑着道:“不疼。”
两人坐车回家,无言地依偎着。好几次我想问方非,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太累?是不是很困扰?但几次话到嘴边,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好沉默不言。
半途时,方非忽然伸手过来拥紧我,手靠在我肩上。我回头吻他的额头,他笑着问我:“你在想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脸贴在他柔软的发间,“非非……”
手机却响了起来,我拿起来看,是钱律。方非离我很近,应该也看到了我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我看看他,他坐直了身体,道:“接吧。”
《疯狂青蛙》的铃声让人抓狂,我看着电话闪了许久才接起来。
“喂。”我很轻的一声。
那边很急切的样子,“我在你家楼下,你在哪里?我有急事找你。”
我看了下车外,道:“快到了,你有什么事?”
“有件事让你帮忙,等你回来见了面再说。”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看着电话发怔,觉得电话那头的钱律是从未有过的焦虑,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也许是看到我的脸色不对,方非问我。
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只能摇摇头,“不知道,好像有急事。”
几站路很快就到了,从车站到小区的路,我下意识地走得快了些,方非跟在我后面,不发一语。
小区门口,钱律的车停在那里,靠着车门一口口地抽烟,头发有些乱,眼睛不住地朝我的方向张望着。看到我,便一扔烟头几步上来,然而看到我身后的方非时,下意识地停了停。
“什么事?”我看到他发红的眼睛,先开口问道。
钱律看看方非,伸手想拉我,可能是想将我拉到边上谈,我却缩了缩,道:“你有话直接说。”
他愣了愣,无奈地点点头,道:“你跟我去次大连。”
我一怔,“干什么?”
他似乎有些受不了我疏远的口气,用力吸了口气道:“几小时前我姐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她想见见你。”他说这句话时带着无比的疲累与伤痛,有些恳求地盯着我,“我帮你订了机票,现在就出发,晚了我怕见不到了。”
我完全反应不过来,感觉身后的方非忽然握住了我的手。我下意识地回头看看他,他正面无表情地看着钱律。
“你妈,为什么想见我?”钱律的话与口气让我明确地知道那会是一场生离死别,只是为什么要见我?难道他妈一直知道我的存在,但即使知道也已经是以前的事了啊。
“我以前跟她说过要把你带回家给她看,她很高兴,以后每次和她打电话时她都会提到你,所以我一直没忍心告诉她我们分手了。”钱律的声音放低,从未有过的卑微,连他求我与他复合时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口气,“跟我回去,见一面就好,了了她的心愿,算我求你。”
他说完抿紧了嘴,让我感觉到他在强忍着什么,只是方非在我旁边,他一直没有爆发。那样的眼神与神情,我不可能不心软,何况是他母亲病危,那是临终的愿望,我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个“不”字。但是方非呢,我分明在跟他谈着恋爱啊,我跟另外一个男人回去又算是怎么回事?
我沉默不语,只感觉方非握着我的那只手越来越用力,然后又猛地放开,“跟他去大连吧。”方非说。
我一怔,回头看他。
“跟他回大连去,不要做让你后悔的事。”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动,只是盯着他,道:“我可以不去的。”只要他说不行,我就不会跟着钱律走。你知道我摇摆不定,方非,如果我一去不回,那又该如何?就像是毒瘾,虽然戒除,心里却让存着羁绊。为了某种原因你劝我再吸一口,却不知再吸一口的后果很有可能是万劫不复。
“去吧。”方非却说,眼睛有些空洞地看着我,似乎很疲惫,“如果有一天你又回到他身边,你会为今天的没有去遗憾不已,所以去吧。”
“方非?”那个“他”明显是指钱律,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放手吗?他那种疲惫的表情是说明他累了吗?还是只是不想让我做后悔的事?我想起医务室吴亮劝他的话,也许他真的累了吧?
我看着他那只受伤的手好半天,点点头道:“好,我去。”
42、没有你的日子很想你
连夜乘坐飞机赶往大连,我不觉得疲惫。钱律一直不说话,我也不曾开过口,为什么我有种像死了一样的感觉。
赶到医院时,我一路被钱律扯着爬了五层的楼梯,在走道里狂奔,但还是没来得及,钱律的母亲一个小时前已经去了。钱律一下子跪倒在冷硬的水泥地上,没有哭,只是一下下的用自己的头用力撞他母亲躺着的铁床,几下就磕出血来想拉开他,可是他固执得吓人。
我知道他是想哭,眼睛已经被逼到血红,但就算是满额头的血了,却一滴泪也没掉下来。我木然地站着,有些不知所措,在他再往床上撞时,我扑过去一把抱住他的头,他那一下撞在我的胸口,很用力的一下,我胸口被撞得生疼却不敢放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死命地抱住他。
他没有再动,只是人抖得厉害,也听不到他的呼吸声。我以为他是不是被我抱得太紧呼吸不过来,却骤然听到他用力的一记吸气声,然后是一声沉闷的近乎吼叫的声音,我感觉他忽然拥紧我,然后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将我的眼泪瞬间逼落,我跪着,任他将我抱得死紧,手下意识地抚着他的后背,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晌,看到他姐姐也跪下来抱着他哭,几个人哭成一团。
钱律在之后的几天一直发高烧,保持着近四十度的高烧始终不退,除了去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就一直没离开过病床。他睡睡醒醒,我就一直陪着,看着大连这几天骤降的大雨,心情差到极点。我恨大连。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来的时候没有带充电器,现在已经快要自动关机了。曾经收到过几条消息,却没有一条是方非的。方非,你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等我发消息给你?
身旁传来轻轻的一记叹息声,我转过头去,钱律醒了,看着我。我摸摸他的额头,每次他醒来烧就会退,但过了一会儿又会升上去,现在又是很正常的体温。
看着他嘴唇发干,我用纱布沾了点水,擦他的嘴唇,道:“你饿不饿?我帮你弄点吃的来。”
他没有打点滴的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看向天花板,答非所问地说道:“你说,这是不是我妈在惩罚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我缩回手,道:“你别胡说,哪有父母这样惩罚子女的?”
他又看向我,道:“杨娟娟,没你的事了,你怎么还不走?”
我瞪他,道:“我没钱买机票。”
他嘴角往上扬了扬,道:“如果是这样,那我绝不会借钱给你买票的,最好……”他停了停,“将你永远囚在这个城市里。”
他后面半句让我愣了愣,我却故意忽略,道:“不是借钱给我买,是你帮我买。”
“那我就永远不帮你买。”他接着我的话说。
他有些执着地强调这一点,不过是想看我的反应,也许只要我点头,他真会囚着我让我永远无法离开这里。
那天离开方非来这里时,我曾经想过,我很可能控制不住自己,会跟着心的方向回不了头了。但不知为何,钱律在说这些话时,我却并没有想的那样心动。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牵着,我可能想往钱律的方向去,却因为被牵着,所以没有移动半步。
我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紧握的手机,心想,也许我该买个万能充电器试试。
“他没有给你发过信息吗?”看我盯着手机,钱律忽然问我。
我“嗯”了一声,点点头。其实那天方非也很需要安慰,可我却连夜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
“看得出,他的确很爱你,那天换了是我,我不一定会放你走。”
这句话让我微微地疑惑,肯放我走,就是爱吗?我怔怔地看着他,他似乎看出我的不解,道:“放你走,是因为他站在你的立场,不想让你做以后会后悔的事。如果不放你走,那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己的私心无法接受你跟着另一个男人离开。杨娟娟,我绝没有他那样大度。”
听他这样说,我忽然想到方非空洞而疲惫的眼神,却又想起医务室里吴亮的话,有些固执地说道:“也许他也累了,所以才想放开手。”
钱律一直看着我,眼睛里是属于他特有的神采与自信,即使现在发着高烧,这种神采始终未退。但不知为何,听到我这句话时他的那股神采淡下来,然后迅速地闭上眼,道:“有时,你真的很迟钝。”然后再也不说话。
钱律的体温终于恢复到正常,并且稳定下来。本来是要回上海了,但他母亲的头七就在后天,所以决定过完头七再走。
钱律的姐姐似乎很喜欢我,她怕钱律忙他母亲的事没空陪我,就让她十二岁的女儿带我到外面四处逛逛。我看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便跟着人小鬼大的孩子出去走走。
“以前我很怕我舅舅的,整天绷着张脸,好像我欠他十万八万似的。”小朋友边走边嘀咕,学起钱律的那张铁板脸。因为长得有点像的缘故,学起来很是相似,我不由笑起来。
“阿姨,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我喜欢你才告诉你的,不是闷死就会被他这张脸吓死。”小朋友继续快人快语。
我差点喷出来,才十二岁,这种逻辑哪来的?我蹲下来看着她,道:“那你觉得阿姨应该跟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
“唔……”小朋友很认真地想了下,道,“飞轮海的吴尊好了。”
我当场被雷倒,你也不先问问人家要不要我?我不由又庆幸,还好,我三十高龄还知道什么是飞轮海,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与小朋友沟通。
小朋友带我去看海,说外地人都喜欢看海,她不停地跟我讲班里的某个男生怎样欺负她,她又怎样报复回来,里面的某些细节让我想到方非,不过大部分都是我在欺负他,而他从没有报复回来。
方非,你现在在干什么?为什么连消息也不发一条?我拿出充好电的手机,一张张拍着眼前的海。
“杨娟娟,我爱你。”他如此肯定地说过。
“也许吧,也许只是我的执念而已。”他如此不确定地说过。
“如果有一天你又回到他身边,你会为今天的没有去遗憾不已,所以去吧。”那是他满眼疲惫时说的。
他曾经那样急切地想抓住我,即使那时我和钱律在一起,他也不曾放手。然而那晚却又如此轻易,“所以去吧”这四个字竟让我辗转难眠。
“阿姨,你为什么哭了?”有只小小的手轻轻地抚过我的脸,我怔了怔,回过神,用力地抹过自己的脸,竟然真的在哭,为什么?
“风太大,阿姨的眼睛一被风吹就会流泪。”我解释着。
小朋友似懂非懂,道:“既然这里风大,那我们回去吧。”
晚上吃饭的时候,钱律的姐姐问我和钱律什么时候结婚,还说因为钱律母亲的过世,可能这一年都不能办喜事,问我在不在意?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含糊地应着。转头看钱律,他只是低着头吃饭,丝毫没有要帮我解围的意思。
钱律母亲的头七一过,我就和他一起回上海。上海与大连如同两个世界,夹着咸味的清新气息,转眼被混浊的带着汽油味的空气代替。我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扑面而来的温热气息让我有些失神。
钱律开车送我回家,我一路心神不宁。出机场时给方非发的消息始终没有回复,我不敢打电话,我怕他同样也不接,到时我不知又该纠结到什么程度。
钱律绷着脸,我的心神不宁让他始终没有好脸色。很奇怪是不是?以为自己这一去就再也回不了头,然而却是什么事也没发生,怎样去的又怎样回来了。
钱律并不像前段时间那般步步紧逼,大连的日子除了生病、忙他母亲的后事,他几乎很少与我说话。
出租车上高架时,司机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就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开头的钢琴曲如流水一般泻下来,让我瞬间安静下来。然后是冗长的歌词,开始听这首歌时只觉得那歌词语病太多,但听习惯了,又觉得这样写没什么不好。
我跟着唱,却总是唱不对歌词,来来回回。然后感觉钱律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我停下来,却没有回头看他。
“别回家,留下来陪我好吗?”他说。
我没回答,不是完全没有犹豫,但最后却轻轻地抽回了手。即使不看他,我也能感觉到他的失望,所以我更不敢看他。
“再回答我一次,杨娟娟,你爱他吗?”他紧跟着又是一句。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收音机里轻轻唱着,我定在那里。
我爱他吗?我爱他吗?我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方非的身影在我眼前闪过,都是在笑的,都是在温和地叫着“娟娟”,叫了二十多年,以为已经麻木,此时却忽然想听他这样叫我。爱吗?我不知道,但至少是喜欢的,很喜欢。
我几乎是冲进家里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急切。冲进屋里,推开方非房间的门,他的东西都还在,然后觉得心里有块石头落地了,我整个人腿一软,靠着门跪坐在地上。还好,他没有离开。
冰箱是空的,这让我忽然又有不好的预感,因为有他在时,冰箱总是满的。我不想想太多,拿了钱包到菜场买了一堆菜回来,有些神经质地塞满整个冰箱,然后开始做饭。
方非在时我不下厨房,但并不表示我不会做饭。我连烧了五个菜,弄得一水池的菜叶、一脸的油腻,抬头看墙上的钟,已经八点半了。也许是上晚班吧,我这样对自己说,却呆呆地看着钟,半天没有动。
也许吧,也许只是执念。方非的话又在耳边。所谓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