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及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作-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领会达尔文所提出的证据的,都还是乐于听从进化论。
可是,就连某些博物学家也对这个新观念有抵触。大解剖学家欧文(Richard Owen)爵士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很凶猛的反驳文章,他的许多同事也附和他的意见。但胡克立刻表示赞同达尔文的意见,赫胥黎、格雷、拉伯克(Lubbock)与卡本特尔(W.B.Carpenter)接着也都表示赞同,赖尔也于1864年秋天在皇家学会的聚餐会上,宣布他接受这个信念。
从一开始,赫胥黎就是进化论者阵营的主角。他自称是“达尔文的看家狗”。他凭着极大的勇气、能力和明晰解说的本领,首当其冲地抵抗各方面对达尔文的著作的攻击,而且时时带头对狼狈的敌人展开成功的反击。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于1825年生于伊林(Ealing),但其祖宗居住在考文垂(Coventry)及韦尔斯沼泽地区,所以他具有真正边境民族的斗争气质。他告诉我们:《物种起源》出版,对于当时科学家,好象黑暗中的一道电光。他写道:
“我们不愿相信这种或那种空想,而要抓住可以和事实对照、经过考验正确无误的明白确定的概念。《物种起源》把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假设给予了我们。不但如此,它还有一个极大用处,那就是使我们脱离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你不愿承认上帝创造世界的假设,可是你又能提出什么学说,让任何小心慎思的人都能接受呢?1857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相信有什么人能够回答。一年以后,我们责怪自己为这样的问题难倒真是太愚蠢了。我记得当最初我把《物种起源》的中心思想抓住的时候,我的感想是‘真笨,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1860年,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主教在英国科学协会牛津会议中展开的有名的争论是人们常常引述的。威尔伯福斯青年时代在牛津数学院得过头等奖,他的大学认为他对自然知识的各个部门无不精通,所以选定他来维护正统的教义。这位主教对于这个问题并无真正的了解,企图用讥笑来摧毁进化观念。赫胥黎对于地的论点给予有效的答辩之后,更对于他的愚昧的干涉给与严厉的抨击;同时拉伯克,即后来的艾夫伯里勋爵(LordAvebury),则说明了胚胎学上的进化证据。
到辩论与讥评不能阻止达尔文学说传播的时候,他的对手就采取了平常的步骤,说这个学说并不是他的创见。但对于这个问题最有裁判资格的人却有不同的见解。牛津会议之后两年,赫胥黎写信给赖尔说:
如果达尔文的内然选择说是对的,在我看来,这个“真实因”的发现,就使他处在和他一切先辈完全不同的地位。我不能说他的理论是拉马克的理论的修正,犹如我不能说牛顿的天体运动理论是托勒密的体系的修正一样。托勒密解释这些运动的办法是空想出来的。牛顿却根据定律和显然起作用的力来证明天体运动的必然性。我想,如其达尔文是对的,他将与哈维那样的人立于同等的地位,即使他错了,他的清醒而精确的思想也使拉马克不能和他同日而语。
赫胥黎指出了证据方面的一个缺陷。积累变异而成新种的观念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血缘相近而不同的物种杂交后往往在某种程度上生殖不蕃。如果物种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我们便看不出为什么竟有这样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找不到明显的例证,说明确实生殖不蕃的杂种是在实验中从共同祖先传下来的多产亲体所养育出来的。
把自然选择当作主要决定力量的主张的确当姓,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最有问题。“适者生存”,用来说明进化的轮廓是可称赞的,但应用在种的差异上就不行了。达尔文的哲学告诉我们:每一物种如要生存,必需在自然里繁盛起来,但没有人能说出我们所说的种的差异(常常是十分显著固定的)在事实上怎样使物种能够繁盛起来。
赫胥黎虽然指出这个困难,但当时没有人感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以为进一步的研究会弄清楚这个问题,直到二十世纪大规模地进行科学的育种实验时,人们才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那时的生物学家,在最初的奇异感消除之后,便接受了进化论,并且认为自然选择是真实而充足的原因。
大陆上最有名的人种学家微耳和没有接受达尔文的理论,但进化通过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进行的学说在德国得到极热烈的欢迎。海克尔与其他博物学家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条顿哲学家与政论家一块创立了所谓达尔文主义,使他们的许多信徒比达尔文自己还要达尔文些。
可是达尔文研究变异与遗传所用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反陷于中止的状态。人们同意自然选择是进化与物种来源的经过证明的充分的原因。达尔文主义不再是初步的科学学说,而成了一种哲学,甚至一种宗教。实验生物学把注意力转向形态学与比较胚胎学,特别是鲍尔弗(F.M.Balfour)和赫特维希(O.Hertwig)所创立的形态学和比较胚胎学。由梅克尔提出,经海克尔加以发挥的一个假说,认为个体的发育追随、并表现种族的历史。这样一来,胚胎学就具有进化意义,迟缓而费力的研究方法也就更为人所忽视了。
在田野里系统地研究动植物的博物学家,在园圃农场上培育新植物和动物的育种家,日益扩大他们对于物种及品种的正确知识。在博物学家与育种家看来,物种的界限依然是分明的,新种不是由于感觉不到的逐渐变化而形成的,而是由于忽然的、常常是很大的突变而形成的;而且一开始就成了纯粹的种。但实验室里的形态学家并不征求实际工作者的意见,也不对他们的经验知识给予足够重视。贝特森(Bateson)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进化论者极其肯定地以为物种是分类学家胸中的一种虚构,不值得识者注意。”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在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学家,在大陆上以德·弗里斯(de Vries)为领袖,在英国以贝特森为领袖,重新回去研究变异与遗传。
达尔文自己虽然相信自然选择是进化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排斥拉马克的意见,即由于用进废退的长期作用而获得的特性可以遗传。当时拥有的证据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十九世纪快结束的时候,韦斯曼(August Weismann)在这个问题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指出体细胞与体内的生殖细胞必须截然分清。体细胞只能产生与自己相同的细胞,但生殖细胞不但产生新个体的生殖细胞,而且产生体内一切无数类型的细胞。因此组成生殖细胞的单元必须有足够多的数目,在种类与排列上必须有足够的差别,以形成自然界里的无数机体。生殖细胞由细胞质一脉相传,复制生殖细胞,但体细胞总是溯源于生殖细胞。因此,每一个体的身体,不过是亲体生殖细胞的比较不重要的副产品;它可以死去而不留下后裔。主要的传统是细胞质,它由细胞传到细胞,有一个不断的历史。
从这个观点看,身体所遭到的改变不大可能影响生殖细胞的产物。这样的影响好象一个人的伯叔父身上的改变,对他本人的影响那样。包含生殖细胞的身体可以损害生殖细胞,但却不能改变它的性质。于是韦斯曼就去严格地研究后天获得性质的遗传的证据,但他认为每个证据都不够充分而加以抛弃。自那时以后,人们通过观察与实验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环境的长期的改变,可以产生一些效果,但这些好象都是例外,没有得到博物学家一致的承认。
在韦斯曼宣布他的结果以后,人们一度有些惊谔。因为,生物学家一直是用“用进废退”来解释没有解决的适应之谜的。进化论的哲学家,特别是斯宾塞,一直是把后天获得性质的遗传当做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而慈善家、教育家与政治家则默认这种说法为真理,而且将它看做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基础。生物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的见解;斯宾塞却一直到死还和韦斯曼辩论;政治改革家就是到现在,还对和他们的先入之见相反的理论熟现无睹。如果承认后天获得性不能遗传,即等于说‘天性”(nature)重于“教养”(nurture),遗传重于环境。改善生活条件,个体当然会得到好处,但除了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选择的间接过程之外,这丝毫不能提高一个种族的天赋性质。
韦斯曼为了解释遗传而设想出来的特殊类型的机制,也许是一些聪明的交想,但足以指导他的许多追随者的研究工作,促使他们去考察生殖细胞究竟是通过什么过程形成的,体细胞又是通过什么过程从生殖细胞中发展出来的。这些新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但最显著的结果到后来才出现,所以这个问题留在第九章里讨论比较合适。
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另一场围绕着新知识的争论。纯粹达尔文主义的维护者如韦斯曼,开始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可以充分解释适应和进化的原因。而且他们还以为自然选择所形成的变异是很微小的变异,例如人体身长便有一序列连续的差异。在相当多的数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平均数的两边相当宽广的范围内,各人的身长相差不过百分之一英寸。他们以为,选择就在这样细微差异中进行,而且只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便可以产生新的品种和新种。
但在新世纪开始以前,有些博物学家,主要是德·弗里斯与贝特森,把育种家、饲鸟人与园艺家积累的经验当作起点而进行实验,发现以上的设想不符合事实。大的突变常常发生,特别是在杂交以后;新的品种可以立刻出现。到了1900年,久被遗忘的孟德尔的研究成果重新发现,因而又展开了新的一页。即令微小变异的选择不能解释进化,这些新的观念好象还可以解释。这个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人类学
在由于达尔文的缘故而恢复生气的各种学术中,人类学,即人类的比较研究,得益最大。事实上,即使说现代人类学从《物种起源》而来也不为过。赫胥黎关于人类头骨的经典研究著作,是从达尔文学说的争论得到启发的,也是精确度量人体特点的开始。这种度量现在成为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自然选择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则成为后来的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
在其他方面,创立人类学的条件也成熟了。爱好新奇的心理,热切的好奇心和收藏家的搜集癖好不但为欧洲的园圃与博物馆带来了异域的动物和植物,也带来了发展阶段不同的其他民族的美术、工艺产品以及其他宗教的法物祭器。
当人类学家开始工作的时候,大部分必要的材料已经齐备了、熟悉了或部分地分好类了,只待有人出来重新加以解释,以揭示其内在意义的另一方面。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没有详细地研究人类,可是他指出他的关于一般物种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有明显的关系。1863年,在彻底地研究了解剖学的证据之后,赫胥黎说人在身体与大脑方面与某些猿猴的差异比猿猴与猿猴间的差异还要小些。因此,他回到林耐的分类法,将人类列为灵长目的第一科。在心理方面,人与猿猴的距离要大些,但脊椎动物的心理过程与人类的心理过程是对应的,虽然不及人类的有力与复杂。布雷姆(Brehm)在其《动物的生命》中和达尔文在其较晚的著作中都指出了这一点。可是华莱士仍然认为不应当把人类与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因为“他不但是生物大系的首领与进化过程的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纲目”。
人类学把人类分为几个种族或人种时,主要是根据身体特点,不过,人们也始终认为身体特点和心理待点是相互关联着的。通常都按照肤色把人类分为白种、黄种、红种和黑种;很明显,这四个人种之间的实际差别不但包括肤色差别,而且也包括其他特点方面的差别,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必要的。在重要性上仅次于肤色的是头骨的形状,一般用雷特修斯(Retsius)的方法来分类。从上面来看头颅时,由前到后的长径作为100。以此为准,短径或横径的长度就叫做“头骨指数”。如果指数小于80,头颅即列为长的一类,大于80,即列为短的一类。
我们可以对欧洲居民加以分析,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些方法及其结果。从身体方面来看,欧洲人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特点上:身长、肤色与头形。按大数目平均来说,当我们由南到北向波罗的海前进时,身长逐渐加高,肤色变淡,如果转向南行,则身长变短,肤色变深。在中间的阿尔派恩区(Alpine),身长与肤色介乎两者之间。但头颅的形状则是另外一回事。北方与南方的人都是长头的,其头骨指数是75到79,而中间山区的人则是扁头的,头骨指数是85到89。
要说明这些事实,我们假定欧洲有三种本原种族:第一种是身高皮白的北方种族,在波罗的海周围可以找到,最为纯粹。第二是身短狭黑的南方种族,生长在地中海沿岸以至大西洋岸边。这两种种族都是长头的。但在地理上介乎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是圆头的阿尔派恩种族,身长与肤色也介乎这两个种族之间,生长在中欧的山岳地带。从一个方面来说,欧洲的历史就是这三个种族的迁徙与互相作用的历史。人们还根据头发的组织等其他特点,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其他大陆上的人类的体质情况。在这些大陆上,可以找到更原始的居民。
自从赖尔描述了人类在地质记录中所留下的遗迹之后,已经发现许多证据,说明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种族。在十九世纪里人们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发现在几万年以前穴居的人已经用相当生动的野牛与野猪的形象来装饰他们的石壁。1856年在尼安德特(Neanderthal)地方,1886年在斯普伊(Spy)地方,发现更古的人骨,说明有更原始的人类存在;1893年杜布瓦(Dubois)在爪哇鲜新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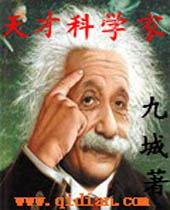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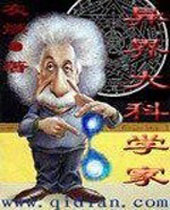



![(科学的超电磁炮同人)[黑琴]末世之我一直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