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及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作-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验。灵魂研究学会的刊物中载有许多精细的研究,但唯灵论的解释是否合理,有资格的人士尚无一致的意见。在获得更多用严格的方法检验过的知识以前,我们最好不下判断。
人是机器吗?
在最近三百年的生物学史上,活力论与机械论互为消长。笛卡尔的二元哲学认为,肉体与灵魂相反,纯粹是机械的,确实是唯物主义的。十八世纪中期和末期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更进了一步。他们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牛顿的动力学基础之上,以为人(肉体与灵魂)不过是一架机器。这种见解,不但受到正统派的神学家的批评,而且受到其他作家的科学上更有力的批评。十八世纪末,主要由于比夏的影响,活力论又复指头。以伯纳德为领袖的十九世纪的生理学,加上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引起一种向决定论方向发展的反动,在德国的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学派与生物学家(如海克尔等)中,这种倾向尤为显著。
诺登许尔德(Nordenskiold)与李约瑟对这场争论的最近历史作了扼要的叙述。实验生理学家与心理学家根据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也适用于有生命物质的含蓄假定,不断地扩大研究范围,以为在这种范围内机械论似乎足以充分解释生命现象。但有些生物学家,感觉未知的境界还很宽广,或者对有生命的机体的表面上的目的性深有所感,因此又以为只有把有生命的物体看做有机的整体,才能解释事实。
在这些研究者之中我们不妨试举几人:冯·于克斯屈尔(VonUexkull),1922年以为有生命的机体的特点,在于它们是时间中的单元,又是空间里的单元;霍尔丹(1913年)以为在外部和内部环境改变的当儿,动物常有守常不变的倾向;杜里舒(Driesch)以为胚胎的早期发展只能以一种非物质的导引力量去解释。他如汤姆生(J.A.Thomson)、罗素(E.S,Russell)与麦克布赖德(WMcBride)等都在生命的复杂现象中,举出了一个或几个无法给予机械解释的事例。
至于哲学家里格纳诺(E.Rignano)认为有生命的物质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性——有一定目的,力求达到一个目标。这种目的性控制了身体与心灵的生长与功用,远不是机械与化学的盲目力量所能及的。例如他说:
有生命的物质从溶解在营养液里的极复杂的化学物质之中,丝毫不差地吸取可以重建其机体、保持其本来面貌的化合物或化学基。正因为是选择,这个过程才有显著的目的性。
新活力论者的许多论据,建立在现今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知识的空白上面。依赖这种暂时的无知是危险的。这些论据已有一些为新近的研究所驳倒。其他论据,如上面所引的里格纳诺的话,在发表时就已经可以加以驳斥。我们只须指出:有生命的物质除了吸取重建其机体的化合物外,也能吸收毒害它的毒物。
洛采认为世界上的机械作用是有绝对普遍性的,也完全是附属性的。只有机械论的看法才为实验者提供了可用的工作假设。这只是“一种观点”,但在它的范围以内,它是至高无上的。物理科学从数与量度的角度去看自然,机械论的思想线索则由心灵的机杼织到它的基本结构中去。目的论的方面同科学是格格不入的,也必然是格格不入的,虽然它也可能是实在的精神方面的一部分或整个过程的意义的一部分。
韩德逊(L.Henderson)提供另外一种解答。他指出环境也象机体一样带有目的论的痕迹。生命,至少是我们所知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是由于碳、氢与氧的特殊化学性质以及水的物理性质的缘故。生命也只能出现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温度、湿度等情况相宜的窄狭的条件范围内。因此,有机目的论当包含于宇宙目的论之中。
尽管生物物理学家与生物化学家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解释生命现象,十分成功,愈来愈成功,作为一种哲学看,机械论也还有错误。从笛卡尔以来,机械论者以为物理科学揭示了实在,其实它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实在的抽象概念。因此,人们才周期性地认识到机械论不是对于实在的完备解释,这就自然要导致活力论,而认为有一种暂时地或永久地与肉体联系着的精神或灵魂,可以控制或甚至停止物理定律,以达到某种预定的目的。
活力论者的谬误,似乎在于他们企图把目的的概念应用于生理学上的有限度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按其性质,只能用物理学的分析方法去解决,至于目的(如果有所谓目的的话)只能在整个机体之中起作用,而且或许只有在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实在时才能把这种目的揭示出来,因为只有这种研究才与存在的全体有关。
我们还必须指出:从1925年开始的物理学的最近的变化,看来很可能削弱了机械决定论的论据。哲学给科学上的决定论找到的最有力的证据,一向是从物理学中得来的,因为人们以为在物理学中,存在着具有数学必然性的体系。但如后章所述,新的波动力学好象说明测不准原理乃是物质的基本单元即电子的基础,因此要同时精密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是绝不可能的事。于是有人说,哲学上的决定论的科学证据已经被打破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测不准原理不过是我们的测量系统无力处理这类实体的表现而已。
体质人类学
正如对于化石记录的不断的研究增强了我们对于动植物进化的一般学说的确切性的信念一样,二十世纪早期的古生物学上的发现,也证实了赖尔、达尔文、赫胥黎诸人关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一般结论的真实性。此外,关于猿人及各类人种的起源的许多新证据也出现了。我们渐渐明白猿与人可能早在第三纪的新生代中期就互相分化出来。同时他们的血液相似的新资料则提供了生理证据,说明他们目前有着密切的亲缘联系。
1901年,安德鲁斯(C.W.Andrews)在埃及法尤姆(Fayum)发现的化石也许可以代表现今哺乳动物的祖先,他还预言早期类型的类人猿也可以在那里发现。这个预言后来在1911年为施洛塞尔(Schlosser)证实。在喜马拉雅山麓,皮耳格林(Pilgrim)寻得猿化石,其结构的特点,说明它们是人科的祖先。1912年,道森(Daw-son)与伍德沃德(Woodward)在英国苏塞克斯郡(Sussex)的辟尔唐(Piltdown)地方发现类人的遗骸,埋藏在新生代第四纪岩石之中,且有粗笨的火石工具。(见书末编者注)
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塔(Neanderthal)山谷中第一次发现了尼安德塔人的骸骨。以后在其他地方又有同样的发现,因而大大增进了我们对尼安德塔人的了解。这些化石说明尼安德塔人头大而扁平,眉峰凸出,面孔粗糙,脑虽大但前部却不完全。尼安德塔人所代表的种类的年代当在包括现有一切种族的所谓智人以前,而且更为凶猛。
尼安德塔人以后,在欧洲有身材高大,头颅椭长的克罗马努(Cro-Magnon)人,实在是智人的一种。这种人的火石工具比较完善,其洞穴壁上的图画,颇有艺术意味。其他同时或继起的人种,和克罗马努人不同,分别命名为索鲁特里安(Solutrian)人,与马格德林尼安(Magdalenian)人等。这以后出现新石器时代的各族人民。他们在游荡中,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伟大文明传播到西欧。
二十世纪初,英法两国的人都普遍地相信相似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各种族里独立发生,这信念反使人对于有启发性的相似之点熟视无睹。另一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德国的学派,为拉策尔(Ratzel)1886年所创立,其后又有施米特(Schmidt,1910年)与格雷布纳(Graebner,1911年)的研究加以支持。这个学派认为相似的艺术文化起源于各民族的混合。里弗斯(W.H.R.Rivers)对太平洋岛屿民族的各种关系、社会组织和语言,进行了足资楷模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见解。里弗斯的早死是人类学上一大损失。他在1911年促请人们注意德国人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后来也为研究他种艺术的人所采用。斯密斯(Elliot Smith)在研究以香料保存尸体的技术时,尤其是这样。事实上,到处都有建立独石碑柱和其他石结构的风俗,它们的方位与太阳和星星既有关系,而且又和埃及的模型相似,可见即使种族不一定同出一源,文化也是同出一源的。
社会人类学
二十世纪内,如果说体质人类学大体上遵循达尔文与赫胥黎所奠定的路线发展的话,那末社会人类学就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象里弗斯那样的人久居于原始民族中,对于原始民族的心理有了更亲切的认识;第二,哈里森(J.E.Harrison)与康福德(F.M Cornford)等人对希腊宗教进行了研究;第三,弗雷泽、里弗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搜集了遍及全世界的大量资料。里弗斯的工作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搜集了不少关于原始生活的事实,而且因为他引起了一场方法上的革命。他发现以前探险家用来发问的概括性的话语,完全不是原始人所能了解的。例如问某人是否可以或为什么可以娶他的亡妻的妹妹,这是无用的话。你得先问;“你能娶那女人么?”然后再问:“你和她与她和你的关系怎样?”一般性的规则必须由个别的例子缓慢地综合而成。根据他在大洋洲的研究,里弗斯断言有一种敬畏和神秘的模糊感觉,一般叫做“马那”(mana),是巫术与宗教的来源,比泰罗所说的精灵崇拜更为原始。
经过长期研究野蛮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的原始形式的宗教,人们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过去,不论是信徒还是怀疑者,都以为宗教是一组教义,如果是他们所信仰的,便叫做神学,如果是其他民族的宗教,则叫做神话。就是在人们把仪式考虑在内的时候,人们也认为仪式只不过是公开表示已经规定和固定下来的信仰的一种形式。而从一个观点来看构成宗教的本质的“内在精神祈祷”却大半受到忽视,或者与教义混为一谈。不但如此,宗教信条,还形成一套完备而不可改异的教义,一劳永逸地照示世人,由一部神圣的经典和一个神圣的教会维护。人们的义务只是接受信条和遵循教规而已。
但哈里森女士说:
宗教总是包含两个因素:第一,理论的因素,即人对于不可见者的看法——他的神学或神话。第二,人对于不可见者的行为——他的宗教仪式。这两个因素很少完全分离,它们是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的。上一世纪的人主要是从理论角度把宗教看做是教义。例如希腊宗教,在多数有教育的人看来,就是希腊神话。但一加粗略的考察,便知希腊人与罗马人都没有任何信条与教条,没有任何硬性的信仰条目。只有在希腊的祭仪里我们才能找到所谓“忏悔式”,可是并不是表白信仰,而是表白自己所举行的仪式。我们研究原始人的宗教时,很快就看到模糊的信仰虽多,确定的信条却几乎没有。仪式占有优势而且是强制性的。
我们是由于研究野蛮人才注意到仪式压倒信条和先于信条的现象,但这种现象马上就同现代心理学不谋而合。一般人的信念以为我思故我行;而现代科学的心理学则以为我行(或者不如说我对外界刺激有所反应)故我思。因此发生一串的循环现象:行动与思想又成为新的行动与新的思想的刺激。
真正“盲目的异教徒”并不向木石叩头,而只忙于施行巫术。他并不向神祈求晴天和阴雨;他跳一次“太阳舞”,或学作蛙鸣,希望大雨来临,因为他已经懂得把大雨和蛙鸣联系起来。在许多图腾信仰中,人认为自己与一种动物有密切的联系,而把它看作是神圣的。有时这种动物被看作“禁物”,而不可接触;有时野蛮人食了它的肉,就觉有勇气与有力量。有节奏的舞蹈,不论是否借助于酒力都可以引人达到狂欢的境界,使意志获得自由,使人觉得自己有一种超越平常限度的力量。野蛮人不知祷告,但有愿望。
巫术对宗教的关系和对科学的关系如何,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巫术企图迫使外界事物服从人的意志。原始形态的宗教想依靠上帝和多神的帮助来影响外界的事物。科学比巫术有更清晰的洞察力,它谦卑地学习自然的法则,通过服从这些法则而取得控制自然的能力,这正是巫术误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的能力。无论这三者的实在关系为何,巫术好象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
野蛮人由于希望实现自己的意志,就创立了一种仪式,然后就利用这种仪式与他们的原始的观念形成一种神话。他们不能分别主观与客观;凡是他所经验之事:感觉、思想、梦幻或甚至记忆,他都以为是实在的、客观的,虽然实在的程度或许有差别。
斯宾塞说野蛮人因为梦见死了的父亲,想加以解释,就创造了一个灵魂世界。可是原始人并没有斯宾塞这种复杂的推理能力。梦境对于他是实在的,也许不象他现在还活着的母亲那样实在,但却不是假的。他并不寻求解释,而把梦境当做实在加以接受,他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还活着。他感觉自身有一种生命力,他虽然摸不到它,它却是实在的,因而他已死的父亲也必定有这种生命力。父亲死后,这种生命力不再寄寓在他的肉体内,但它又在梦中回来:这是一种气息、形象、幻影或鬼魂。这是生命本质与可以分离的幽灵的混合体。
泰罗指出野蛮人力求把常见之物分类,以达到类的概念,因而他们深信同种之物属于一家,有一个部落守护神保护它们,并有一个名称,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包含它们的共同的本质。在野蛮人看来,数也是超感觉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本质上是神秘的,也是宗教的。“我们能接触并看见七个苹果,但七自身是一奇异的东西,由此物移至彼物,赋予物以七的意义,因此,它应是上界的仙人。”
仪式、巫术与有节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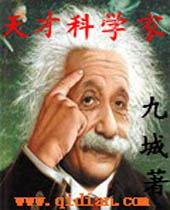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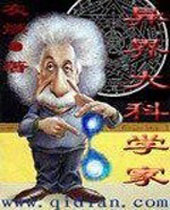



![(科学的超电磁炮同人)[黑琴]末世之我一直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