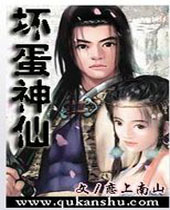杜鹃蛋-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他没有出现。我的警铃调好了,监测器启动了,但是他两周未露面。我在回家的途中,
觉得他可能也有一项紧迫的计划要执行,使他不能来光顾我的计算机。或者他找到了一条新路
进入“军用网络”,完全绕过我设下的圈套?
次日上午,我照例很晚才起床。(感恩节周末临近时,无须很早去上班。)上午l1 时30 分,
我骑车上坡,到了实验所便埋头工怍,准备显示一下我的零点工作的计算机屏幕。但是一旦走
进我的办公室,我又纳闷了,不知黑客为什么没有露面。该是给迈特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了,以
查明他们做了什么。
但是,在噪音大的长途电话中,比尔·钱德勒的话声带着噼啪声。是的,一星期以前,他
切断了他们对外的调制调解器。黑客不再能够以迈特公司的地方网络作跳板。
工作结束了。我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根本没有找到他。由于迈特公司堵住
了他们的洞,黑客不得不寻找进入我的系统的另一条道路。
不大可能。如果有人拴住了我的门,我一定会怀疑他们大概要打我。而我知道这个黑客是
个有病态心理的人。他毫无疑问会消失。
所以我的所有的圈套都白设置了。黑客已走了,我根本没查出他是谁。寻找了三个月,结
果只是个模糊的问号。
我倒不是为此而抱怨。要不是黑客占去了我的时间,有许多值得做的工作等着做,如设计
一台望远镜,或者管理一台计算机,以及制作科学软件。唉——我甚至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
但是我失去了过去的激情:我跑过门厅,飞奔到一台打印机前。涌到一台计算机屏幕前,
试图跟踪通过我的计算机和国内某个地方的联机情况。
我也不再有设置了用于跟踪他的工具后的那种满足心情。现在,我的计划几乎都是立即实
施的。黑客触动了我的计算机后若干秒钟,我的衣袋里的遥呼机就发出了嘟嘟声。它不仅告诉
我黑客在周围,我曾给我的遥呼机编制了用莫尔斯电码呼叫的程序,告诉我黑客盯着的计算机,
他的户名(通常是斯文特克),以及黑客是从那一条线进入的。备用的警报和监测器使这个系统
可以自动排除故障。
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一个陌生人已接近于被捉住。要是我能够再跟踪一次就好了。
只要再跟踪一次。
黑客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有几个还未解决的零星问题:迈特公司的长途电话帐单上显示
向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几十次电话。给各处打电话(这是研究生院通常采用
的办法:不断纠缠)后,我终于查明,黑客曾一直打电话给海军分区自动化数字中心。
嘿,没有人拦阻我,所以我打电话给海军数字中心,同该中心的系统管理人雷·林奇交谈。
雷似乎是开朗的,称职的人,他对工作非常认真。他开动一台电子邮件系统——电子邮件分类
架。
雷报告说,在7 月23 日,从下午3 时44 分到6 时26 分,有人闯入了他的瓦克斯计算机,
使用属于野战勤务工兵的户头,黑客进入他的系统后,开设了名为亨特的新户头。
又出现了那个名字。无疑这是同一个家伙。
这件小事通常是不会引起雷的注意的。由于有300 名海军军官使用他的计算机,他从来没
注意到有人非法增加了一个新的户头。
但是,第二天,他接到了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所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管
理星际航天器的同一个人。一位有警惕的喷气推进实验所业务员在他们的邮件管理计算机上查
到了一个新的系统管理人。这个新的用户是从“军用网络”进来的,来自弗吉尼亚州。
喷气推进实验所打电话给雷·林奇,问他为什么他的野战勤务人员瞎摆弄他们的计算机。
雷没有等到提出问题。他关闭了他的计算机,更改了全部口令。次日,他重新登记了他的各个
用户。
所以我的黑客已闯入了喷气推进实验所和一台海军计算机。我在伯克利查到在以前几个月,
他已经在“军用网络”周围捣鬼。
这些目标对我是新闻。这些目标是黑客所在的地方的线索吗?如果你住在加利福尼亚,那
就没有理由经过弗吉尼亚接触帕萨迪纳的一台计算机。而在弗吉尼亚的某人为什么要通过迈特
公司拨弗吉尼亚的另一个电话呢?
假定这个黑客曾使用迈特公司网络拨他的全部电话,本地的电话除外。这意味着,在米特
尔的电话帐单上列出的任何一个州,不是黑客的家的所在地。排除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亚
拉巴马、得克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另外12 个州。这就没有什么别的地方了,看来很难令人相信。
我给迈特公司的电话帐单上开列的其他一些地方打了电话。黑客曾闯入了佐治亚州亚特兰
大的一所学院的计算机。那里的计算机系统管理人没有查觉,但是他也不大可能查觉。“我们使
用一种很公开的系统。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个系统的口令。完全凭信任。”
那是管理一台计算机的方法。让所有的人都敞开。就象我的物理学教授之一:任何人都可
以漫步走进他的办公室。虽然这没有多大的好处。他用中文记他的记录。
同雷交谈后,我知道了关于黑客的一个新的错误。直到现在,我一直注意到他利用“尤尼
克斯”系统。但是雷的系统是一台“瓦克斯”计算机,运用VMS 工作系统。黑客可能不知道伯
克利有各种型号的“尤尼克斯”,但是他肯定知道怎样闯入“瓦克斯”VMS 系统。
1978 年以来,数字设备公司一直在制造瓦克斯型机,这是该公司的首批32 位计算机。但
是它无法使这种计算机的速度达到足够快的程度。1985 年,售出了5 万多台,每台20 万美元。
这种计算机大多数是使用多用途的、使用方便的VMS 系统,虽然有些人撇开VMS 系统,宁可使
用尤尼克斯。
尤尼克斯和VMS 都是把计算机的设备力量划分开,使每一个使用者都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领
域,有专供这个系统用的领域,还有可供每个人用的共有的领域。
不知为什么,当你打开机器包,第一次接通时,你就能开始为你的用户分派一个领域。如
果机器在你启用时是由口令保护的,那么,我就不能在第一次请求联机。
数字设备公司回答了这个问题,把每一台瓦克斯—VMS 计算机都装入了3 个户头,各有各
的口令。“系统”这个户头的口令是“管理人”。另一个户头名为“域”,口令是“服务”。还有
一个户头“用户”,口令也是“用户”。
由指令要求这个系统开始工作,为用户记新的帐目,然后更改这些口令。启动一台计算机
是有些复杂的,而有些系统管理人从来不更改这些口令。尽管数字设备公司尽最大努力使系统
管理人改变口令,有些人根本不干。结果呢?今天,在一些系统上。你仍可以用“系统”的名
义请求联机,口令是“管理人”。
这个系统的帐户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从这个系统,你能够读任何文件,运用任何程序,更
改任何数据。这个系统没有任何保护,看来倒是奇怪的。
黑客要么知道这些后门口令,要么知道VMS 工作系统里的某个精巧的防盗报警器。不论是
哪一个,他擅长使用尤尼克斯和VMS 这两个工作系统,这一点是无疑的。
一些中学学生是很能干的计算机操作者。但是,既有精湛的技能,又是多面手——有操作
几种计算机的经验——的中学生是罕见的。做到那一步需要长时间实践。通常需要几年。是的,
大多数尤尼克斯系统的使用者一旦了解到格努—埃梅克斯系统的弱点后,能够利用这个系统的
孔洞。而大多数VMS 系统的管理人都知道不太保密的有缺欠的口令。但是每个工作系统须两年
时间才能精通,而技巧不是很容易掌握的。
我拉的那个黑客有使用尤尼克斯两年的经验,还有使用VMS 两年的经验。他大概一直担任
系统管理人。
他不是中学生。
但是他也不是富有经验的奇才。他不懂伯克利尤尼克斯系统。
我曾跟踪一个20 多岁的人,他吸本森和赫奇斯牌纸烟。他闯入了军方计算机,寻找保密的
材料。
但是我还要跟踪他吗?不,实在不必。他不会再露面。
蒂杰伊从中央情报局打来了电话。“我刚刚在检查,了解我们的那个家伙有什么新消息。”
“没有。确实没有。我想,我知道他多大岁数。但是不了解全面情况。”我开始说明海军数
据中心和后门口令,但是那时中央情报局人员插话了。
“得到那些‘对话期’的打印件了吗?”
“嗯,没有。我的直接证据是迈特公司的电话帐单。如果帐单没有说服力,还有其他证据。
他用亨特的名字开了一个帐户。跟安尼斯顿的帐户一样。”
“你在你的记事本上写下了这一点吗?”
“当然。我记下了一切。”
“何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嗯,那是一种不公开的??”蒂杰伊不会把他的报告的打印件送给我。
“得啦,当真的。如果我们曾在‘F’机构点过火的话,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F”机构?我搜寻过去的记忆。是傅立叶变换吗?还是化石?抑或是指画?
“‘F’机构是什么呢?”我问道,感到有些丢脸。
“你知道这是在华盛顿的机构,”蒂杰伊回答,显得有点儿烦恼。“J·埃德加的小伙子们。
那个局。”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联邦调查局呢?
“哦,我明白了,你想要我的记事本,来说服‘F’机构干这些事。”的确是个机构。这是
特工人员用语。
“对。把本子寄给我吧。”
“你的住址呢?”
“就邮寄给蒂杰伊,20505 邮区,那样我就能收到。”
只知道是干什么的。没有姓,没有街名,没有城市名,也没有州名。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收
到这种没头没脑的邮件(通常属三类邮件,有时收件人栏只写“住户”二字——译注)。
在摆脱中央情报局的影响的情况下,我还是重新干点实际工作为妙。我随便试用了一会儿
安东逊的图解计算法,发现它非常容易理解。所有关于这个和目标有关的程序设计的广告不过
是说你不用变量结构和数据结构编制程序;而你是对计算机口授指令。描述一个机器人时,你
不用详细说明它的脚、腿、关节.躯干和头如何如何。不需要谈什么X 的和Y 的。“图解的固有
作用”只意味着机器人的腿移动时,脚和脚趾自动地动起来。你无须编制一个单独的程序以使
各个器官动起来。
好得很。在摆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程序一两天后,这个程序的简便和优越性就显出了。
原来似乎是令人厌烦的编制程序的任务,实际上是容易做的。所以我美化了显示器,增加颜色
和图标。上司要我跳过铁圈;我要演出一个跳钻三铁圈的马戏。
27
感恩节是比较欢快的日子。马莎用她的自行车和背包,把40 磅杂货运到家。她对起床晚的
回房间的人只讲了几句讽刺的话,让我收抬东西,打扫房屋。
“把这些蔬菜收起来,亲爱的”她说。“我要去赛福维商店。”在那里怎么能够买到更多的
食品呢?她看到我面露惊讶的表情,解释说这只是鲜东西,她还得买鹅、面粉、黄油、奶油和
鸡蛋。肯定要过一个比较欢快的节日。
我把这些食品收拾起来,又上了床。我闻着屋里飘荡的饼干和鹅的香味而醒过来。我们期
待马莎的研究生院里那些不能回家的朋友(或者宁愿吃马莎烹调的饭菜而不愿吃妈妈做的食物
的人),两位法学教授,从她的合气道(合气道是日本古柔术的一派——译注)道场来的几位饿
了的练功人,以及她的滑稽的朋友劳里前来作客。我的良心终于对马莎的忙碌做出了反应,我
开动了我们的“胡佛”牌吸尘器。
我在房间里吸尘时,我的同屋人克劳迪娅参加小提琴排练后回来了。“唉呀,别干那事,”
她喊道,“那是我的事。”想想看,一位同屋人以干家务事为乐趣,那有多么好。她唯一的过错
是在深夜演奏莫扎特乐曲。
感恩节快活地度过了,朋友们悠然而至,在厨房里帮忙,聊天,闲荡。整天在吃,开始吃
从旧金山码头弄来的鲜牡蛎,接着从从容容地吃马莎做的野蘑菇汤,然后吃鹅肉。吃罢,我们
象冲上海滩的鲸,躺下来一动不动,直到我们积起了精力,再来进行短途的步行。在吃馅饼喝
草药茶时,话题转向法律,马莎的朋友维基滔滔不绝地讲起环境保护条例,而两位教授则议论
是否应采取断然的措施。
最后,我们大发宏论,妙趣横生,人人心满意足,于是在壁炉前躺下来,烤栗子吃。维基
和克劳迪娅弹钢琴二重奏,劳里唱了一只民歌,而我则想入非非,想到行星和星系。在这个朋
友、食物和音乐的温暖的世界,担心计算机网络和间谍,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在伯克利,过了
一个洋溢着南方风味的感恩节。
在实验室里,我忘记了黑客。他几乎已有一个月不来了。为什么?我不知道。
天文学家们摆弄他们的新图表,研究增强他们望远镜功率的方法。这时,我在考虑怎样激
励影象,以使镜头能够转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并且使影象映在屏幕上。
星期三,我决定向其他系统的人们炫耀一下。我记住了所有的术语,使形成影象不会在最
后的时刻出毛病。
在3 点钟时,12 位计算机专家露面了。显象系统工作完美无缺,加州理工学院的软件运转
顺利。计算机工作人员习惯于数据库和结构程序的令人厌烦的交谈,所以这个三维彩色图象使
他们都感到惊奇。
表演25 分钟后,我回答关于程序语言的一个问题(程序语言不论是什么含意,是有关目标
的??)时,我的衣袋里的遥呼机响了。
响了三声。莫尔斯信号SS 代表斯文特克。黑客把我们的系统连接到斯文特克的户头上了。
28
黑客一个月未露面后,又回到我的系统来。马莎对此很不高兴;她开始把我的袖珍遥呼机
看成她的一个机械对手。“你要等多久之后才能摆脱那个电子玩意的束缚?”
“只要两三个星期。肯定到元旦就结束了。”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