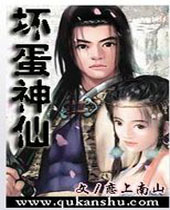杜鹃蛋-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客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是6000 英里,尽管对这一数字我从未给予过多的重视。其实我本应重视这
一数字。德国到伯克利的距离是5200 英里。
我不只是视而不见,我还充耳不闻。
我一直在收集各种事实,却没有理解这些事实。
我独自一人坐在图书馆里,突然问对下述做法深感不安:派我的姐姐去从事一项追逐野鹅
的任务,在弗吉尼亚搜寻一个中学生;派遣几个伯克利的侦探带着左轮手枪在校园里四处搜索。
我茫然不知所措。几个月来我曾把重点放在北美,在那儿寻找黑客。戴夫·克利夫兰不断
告诉我:“黑客不在西海岸。”对,他至少离我们有5200 英里的距离。
有些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但是我已经懂得他是怎样进行活动的了。黑客在德国的某个地方
呼叫德国Datex 网络。他要求接上Tymnet 网络,联邦邮政局经由这个国际记录机构接通了线路。
一旦他的线路通到了美国,便和我的实验所接上了,然后便接通了军用网络,于是在那里胡作
非为。
迈特公司网络一定是他暂时停留的地方。我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连接上的。他进入了德国
Datex 系统,要求接通Tymnet,然后要求使用迈特公司的计算机。一旦接通,他就可以在他有
空时利用它们的计算机。当他对阅读国防部承包商的报告不再感兴趣时,又可以从迈特公司网
络中脱身出来,与北美任何一个地方连接上,而由迈特公司来付帐。
但是由谁来为越洋联机支付费用呢?据史蒂夫说,他的对话每小时要收费50 或100 美元。
在我回到机房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跟踪的是一个很富有的黑客,要不就是个很狡猾的小偷。
现在我认识到为什么迈特公司要为一千次每次长一分钟的电话付费了。黑客会同迈特公司
网络连接上,指示它们的系统用电话通知另一部计算机。当这部计算机作出回答时,他就设法
用假的姓名和口令注册。通常他都遭到失败,于是便继续不断地拨叫另一个电话号码。他一直
在扫描计算机,费用则由迈特公司支付。
可是他却留下了痕迹,那就是迈特公司支付的帐单。
路线又返回到了德国,但并非到那里为止。可以设想,在伯克利的某个人呼叫了柏林,与
Datex 连接上,通过Tymnet 连上后又接回到了伯克利。这条线路的开端可能在蒙古,也可能在
莫斯科。我说不太清楚。就目前而言,我的说得通的假定地点是德国。
他扫描的是军事秘密。我会不会是在跟踪一个间谍?一个为他们服务的货真价实的间谍,
但是他们又是谁呢???唉,我甚至连这些间谍是在为谁工作都还不知道啊!
三个月以前,我曾经看到一只老鼠进入我的会计文件夹中,悄悄地,我又察觉到这只老鼠,
看到它溜进了我们的计算机,穿过一个洞跑出来,然后又钻进了军用网络和计算机。
我终于知道了这只啮齿动物追逐的是什么东西,它是从哪里来的。我把情况估计错了。
它不是只老鼠,它是个密探。
31
星期六傍晚我都用来填写工作日志。现在我可以把一些松开的线头扎紧了。在安尼斯顿搜
寻的结果不会在阿拉巴马找到一个黑客,他们远在5000 英里以外。斯坦福的黑客肯定是另一个
家伙??而我跟踪的黑客会用德文而不是英文写家庭作业。在伯克利到处打电话寻找某个名叫
赫奇斯的人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大概是名字弄错了。肯定是把哪个洲搞错了。
我们的打印机打出的材料足有一英尺厚,我仔细整理了每一张表,并标明了表格的日期。
但是我从来都不是一口气把所有这些表清理完毕的。这些表的大部分都是枯燥无味的档案表,
还有一次只能猜一个的口令。
闯入计算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吗?
我亲爱的沃森,这是要掌握的基本材料。既是基本性的又是乏味单调的东西。
我直到清晨两点才回家。马莎一边在等我一边缝着被子。
我想搂着马莎在星期天早上睡个懒觉。但是,该死的,我的遥呼机在10 点40 分便叫唤起
来了,紧接着一阵刺耳的,连续不断的尖叫声之后,便出现了莫尔斯电码的问候语。黑客又来
光顾了。这次是在我的尤尼克斯——计算机上。
我急匆匆地跑到厨房,打电话到史蒂夫·怀特的家里。在对方的电话铃响的同时打开了麦
金托什计算机。史蒂夫在电话响第五遍时来接电话了。
“史蒂夫,黑客又恢复活动了,”我告诉他。
“好,我将开始跟踪,回头再打电话给你。”
我一挂上电话,马上就操作麦金托什计算机。这家伙由于有调制解调器和一个称之为
RedRyder 的软件,操作起来象是部远程终端机。RedRyder 不可思议地自动拨通了我实验室中的
计算机,接通了瓦克斯计算机,然后向我显示所发生的情况。我所跟踪的黑客出现在显示屏幕
上,慢慢进入军用网络系统。
我也象这样向系统申请注册,看起来就象是个普通的用户,这样一来黑客就有可能看到我,
如果他看的话。因此,我立即中断连接。虽然只有十秒,但是足可以看出我的这位来访者在干
什么。
几分钟以后史蒂夫回话了。线路不是通过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国际记录载波机构接通的。今
天是通过美国无线电公司接通的。
“美国无线电公司不使用西联星卫星”,史蒂夫说,“他们通过通信卫星通话。”他昨天用的
是西联星,今天用的是通信卫星。一个躲躲闪闪的黑客每天都使用不同的通信卫星。
但是我却把事实弄错了,史蒂夫使我了解了真象。
史蒂夫解释道:“你跟踪的黑客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为了提供充足的服务,我们
使用各种不同的国际线路。”
对每一个电话,Tymnet 的通信业务都用不同的越洋线路。而我作为一个用户是永远也不会
注意到这一点的,但是电信来往则是通过四五个卫星和电缆传送的。
“啊,就象放松管制之前的州际卡车运输那样。”
史蒂夫愤怒地说:“不要激起我来同你辩论,你是不会相信国际通信法的。”
“那么,黑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德国,同样的地址,同样的地方。”
不能有更多的作为了。我无法从家里监视黑客,而史蒂夫又结束了他的跟踪工作。我坐在
麦金托什计算机旁有点不寒而栗。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到实验室去,而且越快越好。我写了一张宇条留给马莎(“比赛正在进行中”),穿上牛仔裤,
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我的动作还不够快。黑客在我到达之前5 分钟便消失了。我还不如躺在床上不起来呢。
于是,我便翻阅起星期日上午的一览表,看到他又在玩弄老花招。用猜测明显的口令的办
法,试图挨个闯进军用计算机。无聊乏味,大约就象猜测暗码锁的号码那样。
他既然在上午露过面了,我就不妨等着他,看他会不会再露面。根据我的统计,他会在一
两小时内重新出现。
真是不出所料,他在下午1 点16 分时又露面了。我的遥呼机叫唤起来,我便跑到交换台室。
我发现了他,他正在利用偷来的斯文特克帐户。
象往常一样,他在计算机上四处搜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人。如果我是在家中连接上机器
的话,他是会注意到我的。但是由于我是在交换台室这个制高点,所以我没有被发现。他无法
突破我的电子屏障。
深信没有人在注视他,他便径直从我们的军用网络端口走出来。他用几项指令来搜寻军用
网络的姓名地址录,想靠缩写词“COC”来发现任何地址。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字,他
是不是拼错了某个字?
我再也用不着怀疑了。这个网络的信息计算机开动了一两分钟,然后便打出了五六个军事
司令部作战中心的名字。他继续搜寻其他的关键字,如“夏延”、“洲际弹道导弹”、“战斗”,“五
角大楼”、“科罗拉多’。
坐在这里看着他乱翻军事网络姓名地址录,我感到好象是在看着某人在翻阅电话簿。他会
拨哪个电话号呢?
所有的号码他都想拨叫。每一个关键字都能带出几个计算机地址,在找到30 个这类地址之
后,便与军用网络姓名地址录脱离了接触。然后,他再次有条不紊地试图闯进每一个地点;弗
吉尼亚州阿林顿的空军数据服务中心、陆军弹道研究实验室、设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一个
空军训练中心、设在夏威夷的海军太平洋监视中心以及30 个其他的地方。
但是他再次运气不佳。他偶然挑选了一些没有明显口令的地方。这个傍晚对他来说一定是
一个令人灰心丧气的傍晚。
最后,他试图闯入他昔日常去的地方——安尼斯顿陆军基地。连续尝试了五次,都是时运
不佳。
于是,他放弃了军用网络,回过头来又去摆弄我的尤尼克斯计算机。我眼看着这只杜鹃下
了蛋。他再次巧妙地使用我的计算机内的文件,使自己成为超级用户。他玩的是同样的老花招,
利甩格努—埃梅克斯移动邮件,以其受到污染的程度来取代这个系统的atrun 文件。
现在我必须仔细地注视着他。他可以运用不正当的特权有意无意地破坏我的系统。只需要
用一个象rm 这样的指令就能抹掉所有的文件。
然而目前他还是让自己有所克制。他只是打印出了不同计算机的电话号码,然后便自行注
销。
但是迈特公司已经切断了它们通往外面的电话业务。现在他必然发现了这一点。可是他仍
然收集电话号码。因此,他一定有某些其他的途径来打电话。迈特公司网络不是他通向这个电
话系统的唯一踏脚石。
15 分钟以后他又回到我的系统中来了。不论他向哪里拨号,他的电话都没有能够打通。我
敢断定他没有掌握到真正的口令。
他一回到我的系统,就开动了克米特程序(文件传送程序)。他是想要复制一份文件并输入
他的计算机。又是我的口令文件吗?不是的,他是想要找网络软件。他曾设法向两项程序(telnet
和rlogin)输送了源代码。
每当我的一位科学家与军用网络相连接的时候,他们就使用telnet 和rlogin 程序,这两
项程序使某个人能够在遥远的地方接通一部外国的计算机。这两项程序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把
指令从一个用户那里传送给一部外国的计算机。两者都是埋置特洛伊木马的十全十美的地点。
通过改变我们的telnet 程序中的几行代码,他就能使一项口令成为攫取情报的手段,每当
我们的科学家们与一个远距离系统连接的时候,他那伺机而动的程序便会把他们的口令贮藏在
秘密文件中。啊,他们已经成功地接通了。但是,下一次当黑客利用我安装在伯克利的计算机
时,将会有一张口令表等着他取走。
我逐行地注视着克米特程序把程序大量地传送给了黑客。无需测定传送情报的时间了。我
现在知道了是卫星和到达德国的遥远的距离造成了这些长时间的拖延。
监视着他我感到有点恼火了。应该说是感到极其厌恶了。他是在偷窃我的软件,而且还是
敏感的软件。如果他想要得到这种软件,他原本会从别人那里偷到的。
可是我不能马上让克米特程序停止运转。他立刻就会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我正在向他逼近,
我特别不愿意表明自己的意图。
我必须尽快行动。我如何来阻止一个窃贼而又不让他注意到我是在监视他呢?
我找到了主链路,并把它连接到与黑客的线路相连的电路上。按动按钮,让它发出刺耳的
声音,使黑客的线路瞬间短路。增加的声响大到只会使计算机出现紊乱,但又不致于切断联系。
对他来说,这看上去好象是某些字符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象是拼错了字母和难以辨认的文本,
也就是计算机上出现了类似无线电静电干扰的情况。
他会把这归咎于网络干扰。他可能会再试试,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当通信线路
发生噪音时,长途交谈就没有用处了。
我的工作效验如神。我敲打按钮,他就会听到噪音,他的计算机就会要求重复最后一行。
我小心翼翼地让星星点点的数据通过。但是传送的速度非常之慢,以致整个文件要用一整夜才
能传完。
黑客中断了联机,然后又进行尝试。但是毫无办法。他无法打破我布下的迷魂阵,也无法
断定声音来自何方。
他放弃了打算偷盗我的软件的做法,而是满足于四处搜寻目标。他发现了进入伯克利的奥
帕尔计算机的通路,但是并没有利用它。
现在出现了奇怪的情况。伯克利的奥帕尔计算机是某个进行真正的计算机研究的所在地。
人们用不着花多大的力气就能够找到某些最好的通信程序、学术方面的软件和博奕程序。显然,
黑客关心的并不是学者们可能感兴趣的东西。但是让他接触点儿军事方面的情况,他就会欣喜
若狂。
黑客最后要求离开的时间是下午5 点51 分。我并不是说他遭到的每一个严重的挫折都使我
感到满意,而是说他是按我所预期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我的努力正在慢慢地形成一个解决办法。
史蒂夫·怀特整天跟踪这些连接情况,就象上午那样,它们全都来自德国。
“会不会这是从欧洲另一个国家来的某个人?”我问道,其实我事先就知道了答案。
史蒂夫回答道:“黑客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我所进行的跟踪只能证明从伯克利与德国进行过
一次联系。”
“能告诉我是德国什么地方吗?”
史蒂夫就象我一样好打听。“没有姓名地址录我就无法告诉你。每个网络都有其自己的使用
地址的方法。联邦邮政局明天会告诉我们的。”
“你上午就会与他们通话吗?”我问道。我怀疑他是否会讲德语。
史蒂夫说:“不会,发电子邮件要更容易一些,我已经发出了一封关于昨天的事件的信件;
今天要发的信件将对事件加以证实,再补充一点儿细节。不用担心,他们会开始行动的。”
32
我应该向谁去诉说这一最新的发现呢?我的头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曾经就黑客是从
哪里来的这件事打过赌,而且我输了。我还欠他一盒饼干呢。
向联邦调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