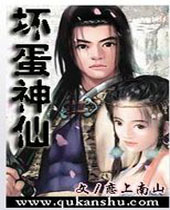杜鹃蛋-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门。”
“你是说你们暗中监视你们自己?”
“不,不,不。我们不断检查我们的工作结果。比如,当我们用理论方法解决一个数学问
题时,我们将用计算机来检查其结果。这样,另一个部门可能试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同一个问
题。这完全是抽象的问题。”
“你认为会有人介意我没系领带吗?”我穿了一条干净的牛仔裤,因为我猜想到这里可能
会见到什么重要人物。但是我没有西服,也没有领带。
“不用担心,”鲍勃说,“在你这种抽象水平,系不系都没有关系。”
会议是高度机密的,所以我不能听。轮到我发表讲话时有人来叫我。房间不大,只有投影
器的灯亮着。室内大约有30 人,大部分都穿着军服。就象在电影上看到的,他们都是陆海军将
领。
晤,我谈了半个小时,讲了那个黑客如何闯入军方的计算机和如何又偷偷进入我们的计算
机网络。坐在后面的一位将军不断打断我的话,提出一些难于回答的问题,如“你怎么证明那
封电子信件不是伪造的?”和“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解决这个案子?”
嗯,回答这些问题又用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们才让我下了讲台。在吃干酪三明治时,鲍勃·莫
里斯向我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
“我以前从未在一间屋子里见到过这么多高级将领。你知道,提出那些有水平的问题的那
个人,他是那间屋子里级别较低的人之一,他只是个少将。
我对军界一无所知。“我想我很受感动,虽然我说不清为什么感动,”我说。
“你应当受到感动,”鲍勃说。“来的全是将官。约翰·保罗·海德将军在参谋长联席会议
工作。坐在前排的那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大人物。他听了你的讲话,这是件好事。”
我却不那么有把握。我可以想象得出联邦调查局一个头头的日子该不好过了:他知道他的
机构应当有所行动,但是却受到压制,什么都没做。他需要的不是听伯克利某个长发郎的宣传,
他需要的是我们的支持与合作。
我突然感到很不自在。我把经历的事在头脑中重新过了一遍。我有没有把事情搞糟?那是
一种在做了什么事后觉得紧张的奇怪感觉。我对这些情况想得越多,军方的这些人给我留下的
印象越深。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瞄准我谈话的薄弱之处,并且了解了我谈话的详细内容和重要意
义。
我走得有多远了。就在一年前,我还会把这些军官看成是为华尔街资本家贩卖战争的傀儡。
毕竟,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看来情况并不是那样黑白分明。他们看起来精明
强干,是能处理严肃问题的人。
次日上午我要在国家安全局的X…1 部门发表讲话。毫无疑问,他们已拟就了一张问题清单,
要求集中谈下述问题:
l 对那个侵入者是如何跟踪的?
2 在帐目审计方面有什么特点?
3 如何审查享有系统级特权的人的帐目?
4 谈谈关于如何侵入计算机的技术方面细节。
5 如何得到利弗莫尔克雷计算机的口令?
6 超级用户的特权是怎么得到的?
7 侵入者有什么防范对方侦查的办法吗?
我盯着这些问题,一下子屏住了气,哦,我明白国家安全局的这些人问我的问题是什么了,
但是这里面有些不对头。
是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被用来闯入计算机系统吗?不是的,我感到问题不在这里。他
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是防御性的。
难道我反对国家安全局只收集情报而不与别人分享情报的作法吗?不,并不真正是这样。
我对分享情报已不再有所求了。
我把这些问题看了又看,看到第三遍时,意识到它们表现出一种我认为是令人不快的基本
看法。我挠挠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使我烦恼。
最后,我终于弄明白这些问题令我烦恼的原因。
令我烦恼的不是这些问题的内容,而是这些问题内在的中立性。提出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假
定对手是不具人格的,是个无害的“侵入者”。它们暗示这是个不带感情色彩的技术问题,要用
纯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只要你把偷窃你的财物的人看作是无害的“侵入者”,你就永远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只要国
家安全局的那些人仍然保持非人格化和保持超然态度,他们就永远也不会认识到这不只是侵入
计算机的问题,而且也是攻击、危害社会的问题。
作为科学家,我明白对实验保持超然态度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不参与进去,如果我不为
可能被这个家伙伤害的癌症患者担忧,如果我不因这个黑客在直接威胁我们大家而感到气愤,
我就永远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把这些问题加以改写,了草地写在一张新投影片上:
1 这个流氓是怎么闯入计算机的?
2 他偷偷进入了哪些系统?
3 这个坏蛋是怎么成为超级用户的?
4 这个卑鄙的家伙是怎么得到进入利弗莫尔克雷计算机的口令的?
5 这个可恶的家伙是怎么防范被侦察出来的?
6 你能审查一个本人是计算机系统管理人的无耻之徒的帐户吗?
7 如何跟踪一个讨厌鬼,一直追查到他的老巢去?
现在,对于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了。
国家安全局的这帮暗探使用不带任何道德色彩的行话谈话,我对此确实感到愤慨。我愤慨
是因为他们说我是在浪费时间跟踪一个无知的破坏者,而不是去研究天体物理学。我愤慨是因
为这个间谍在攫取机密的情报而不受任何惩罚。找愤慨是因为我的政府对这一切毫不在乎。
所以,当你是个留长发又不系领带的天文学家时,或者当你没有任何安全许可证(他们那
里必定有某种“不穿西服、不穿皮鞋就没有安全许可证”这一类的习惯看法)时,你怎么能激
起一批执政的技术专家的热情呢?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恐怕国家安全局的人关心的主要
是技术而不是任何道德上的影响。
后来他们给我看了他们的一些计算机系统。不过这参观有点令人感到困窘:我每进到一个
房间,天花板上的红灯都在闪亮。我被告知:“它告诫屋里所有的人,当着你的面不要谈任何机
密的事。”
“X…1 是什么意思?”我问我的向导。
“噢,这说起来令人生厌,”他答道。“国家安全局有24 个部门,每个部门都用一个字母表
示。X 是安全软件组,我们是负责检验计算机的安全性。X…1 部门的人是研究数学的,他们从理
论上检验软件,想要找到设计上的漏洞。X…2 部门的人则坐在计算机前,试图在软件存入后破
坏它。”
“这就是你们对计算机的弱点感兴趣的原因了。”
“是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处制造一台安全的计算机可能花三年的时间。造好后,X…1 部
门将研究它的设计,X…2 部门的人将对计算机极尽挑剔之能事。如果我们找到什么毛病,我们
就把它退回去,但是我们不告诉他们毛病在哪儿,而是让他们自已去摸索解决。”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找到了格努—埃梅克斯计算机的毛病。
在参观期间,我问了国家安全局的一些人,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办法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
经费。他们个人对我们的经费完全来自物理学研究经费感到遗憾,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没有
提供任何帮助。
“要是你是军我承包商,那倒容易些,”一个暗探对我说。“国家安全局避免与学者打交道。
似乎互相间存有一种不信任感。”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总额为85 美元。那是我在
旧金山湾技术图书管理员协会作报告的酬金。
在国家安全局的参观于午饭后才结束,所以我离开米德堡的时间晚了,而且我在前去位于
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的路上还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大约下午2 时左右,我找到了那
个没有路标的岔道,等到我的车开到房门时,我已晚了一个小时。
警卫盯着我看,就好象我是刚从火星上来的人。
“你要见谁?”
“蒂杰伊。”
“贵姓?”
“斯托尔。”警卫看了看她的记事夹子,递给我一张表要我填写,并把一张兰色的通行证轻
轻放在我租来的这辆汽车的仪器板上。
那是中央情报局发的要人停车证。回到伯克利人民共和国,这个停车证要值5 美元,也可
能值10 美元。
我?是个要人?而且是中央情报局的要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我开往要人停车场的路上,
我避让了几个慢跑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一名武装警卫告诉我没有必要锁上车门。四周蝉声不
绝,一只野鸭在嗄嗄地叫着。一群鸭子在中央情报局的大门口干什么?
蒂杰伊没有说明他想要进行的谈话的技术性强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把我准备好的投影器的
片子塞进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然后,我就向中央情报局大楼走去。
“你来晚了,”蒂杰伊在门厅里向我大声喊着。我怎么跟他说呢?说我在高速公路上总是迷
路吗?
门厅地面的正中是直径5 英尺的中央情报局的局徽,徽章上嵌着一只水磨石的鹰。我原以
为人人走到那儿都会象《没有理由的反叛》一书描写的高中学生那样从这个灰色的徽记旁边绕
过去。我可没看到那样的情景。人人都从那上面走过,谁也没有对那只可怜的鸟表现出任何敬
意。
墙上镶的大理石上刻着“真理将使你获得自由。”(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卡尔克特公司
的座右铭刻在这里,后来我注意到这句话引自圣经。)对面的墙上刻着48 颗星,我只能猜想它
们表示48 个人的生命。
在照例检查了我带的东西后,给了我一个发荧光的红色证章,上面有个大写的字母V。给
我这个来宾证章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我往四周一看,发现我是唯一没有系领带的人,不过我没
看到一个穿风衣的人。
这里的气氛与一所大学校园里的气氛一样。人们在走廊里漫步,有的在练习说外语,有的
在辩论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偶尔有两个人手挽手走过。
嗯,这里并不完全象大学校园。当蒂杰伊领我参观他在一楼的办公室时,我注意到每个门
的颜色都不同,但是门上没有象大学里那样贴着漫画或政治招贴画。然而,有些门上装有暗码
锁,简直跟银行的金库差不多。
“由于你来晚了,我们推迟了开会的时间,”蒂杰伊说。
“我得挑选一下投影片子,”我说。“我谈话的技术性有多强?”
蒂杰伊瞪着眼看着我说,“别担心,用不着那些投影片子。”
我预感到我今天会遇到麻烦。这一次是免不了的。坐在蒂杰伊的办公桌旁,我发现他桌上
有一整套橡皮图章。有货真价实的“绝密”章,还有“机密”、“不准携出室外”,“分类情报“、
“阅后即毁”和“NOFRON”等图章,我猜想这最后一个图章的意思是“不准私通”,但是蒂杰伊
的话让我明白了它的意思:“外国国民不得翻阅”。我把这些图章一个个都盖在一张纸上,然后
把它装进我装投影片子的信封里。
以前曾到伯克利看过我的另一名暗探格雷格·芬内尔来到办公室,把我领到中央情报局的
计算机房。这里更象是体育馆。在伯克利,我已习惯于在一间大屋子里摆着十几台计算机的工
作环境。在这里,上百台主机计算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洞穴状的大厅。格雷格指出,
除米德堡外,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房。
这里使用的全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
那时,在尤尼克斯计算机爱好者看来,这庞大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是一个大
倒退,又回到60 年代计算机中心流行时的情况。在已使用台式计算机工作站、计算机网络和个
人计算机的时代,戈利亚思的中心系统似乎已经成了古董。
“为什么全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器?”我问格雷格。“这些东西已跟恐龙一样成为老古
董了。”我讥讽地说,表现出我对尤尼克斯的偏爱。
“这个么,我们正在换,”格雷格回答说。“我们这里有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工智能组,有积
极研究机器人学的学者,而且我们的图象处理试验室干得实在不错。”
我回忆起我当初骄傲地带着蒂杰伊和格雷格参观我的实验所计算机系统时的情景。突然间,
我感到很尴尬,我觉得我们那五台在科学上广为使用的瓦克斯计算机在这些计算机面前似乎显
得太微不足道了。
不过,我们使用的目的各不相同。中央情报局需要庞大的数据库系统。他们想要整理许许
多多不同的数据,并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需要数字捣弄机,那种迅速进行数字运算的计算机。
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要估量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或是该机磁盘的容量,然后得出“这一台比较好”
的结论。
问题不在于“哪一台计算机计算速度快,”甚至也不在于“哪一台比较好”,而是在于“哪
一台比较适合我们的需要”或“哪一台能使你完成任务。”。
在参观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房之后,蒂杰伊和格雷格领我到七楼。楼梯的楼层是用不同
国家的文字标出的。我认出五楼用的是中文,六楼用的是俄文。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休息室,地上铺着波斯地毯,墙上挂着印象派的画,屋角立着乔治·华
盛顿的半身塑像。真是五花八门的大杂烩。我与格雷格和蒂杰伊坐在长沙发上,我们对面还坐
着两个人,每个人都配带着附有照片的证章。我们谈了一会。他们当中有个人讲一口流利的中
国话,另一个在进中央情报局之前是兽医,我不知道他们希望我谈些什么。
这时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了一位头发灰白的大高个。他边招呼我们进去边说:“嗨,我
是汉克·马奥尼。欢迎,请进。”
这样看来,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原来七楼是中央情报局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的办公之地。汉
克·马奥尼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旁边是咧着嘴笑的局长助理比尔·唐纳利和另外几个人。
“你的意思是说你听到过这个案子?”
“我们每天都在密切注视它的发展。当然,单是这一件事也许看来并不很重要。但是它意
味着今后将遇到严重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为使我们不断了解情况所做的努力。”他们给了我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