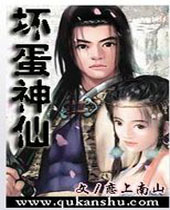杜鹃蛋-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信吗?”我问。
“嗨,扬基队会再次赢球吧?”跟以往一样,他一点口风不露。
在这一段时间,那个黑客几乎每天都注册几分钟。有时从战略防御计划网络帐户攫取任何
新输入的材料。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就设法闯入军用计算机。有一回他用了半个小时,想猜出
进入我们的埃尔克西计算机的口令,因为我曾暗示我们的埃尔克西是战略防御计划网络的中央
主管人。
我制造假军事文件的速度很快,他能读多少,我就能制造出多少。由于我知道他把我的作
品传递给匹兹堡的某个间谍,我又加进了一点可以核实的信息:五角大楼预定在“阿特兰蒂斯”
号航天飞机上发射一颗秘密的卫星。对任何一位看报的人来说,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但是我料
想,由于他渴望得到秘密情报,他会认为这些零碎但却是有价值的真实消息证实他找到的是蕴
藏丰富的主要矿脉。
1987 年6 月21 日,星期日,中午12 时37 分,他以斯文特克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尤尼克斯
计算机系统注册。他花五分钟的时间核对这个系统的状态,然后开列了一些邮件材料的名单。
这次闯入似乎与他以前历次闯入是一样的。
但是这次对话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那就是这是他的最后一次。
52
“嗨,克利夫,我是史蒂夫。”我马上把手中的巧克力饼干放下了。
“我刚从德国联邦邮政局的沃尔夫冈·霍夫曼那里得到消息。他说,下星期一到星期三警
察将在那个黑客的公寓外面日夜值勤。他们将不断地监视他,只要他与伯克利的计算机系统连
接,他们就冲进去逮捕他。”
“警察怎么知道何时往里冲?”
“信号由你来给,克利夫。”
下一次这个黑客一碰到我的系统,我就给联邦调查局和Tymnet 打电话。他们将进行跟踪,
把情况告诉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处,那些警察就会冲进他的公寓。
折腾10 个月之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他会出现吗?要是他不出现怎么办?他们是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抓起来呢,还是会把整
个这件事放弃不管?如果我交好运,他们是会从整个这件事中脱身的。
那个周末我与马莎一起在家里度过,星期日晚上到了实验所。要是我时来运转,那个黑客
会在斯文特克的帐户出现,于是我就给要是我联邦调查局打电话,紧接着他就会在转储我胡编
乱造的那些假的战路防御计划材料时被抓起来。我可以想象得出警察冲进他的房门时他慌乱地
想要把计算机藏起来时的情景。
我一边想象着这些情况,一边在办公桌下躺下,把自己裹在马莎和我去年冬天做的被子里。
为防止我的遥呼机出毛病,到该响的时候不响,两台个人计算机整夜开机进行监视,每一台都
装有电铃。已经干了10 个月了,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
6 月22 日,星期一的下午,沃尔夫冈·霍夫曼发来电报说:“预料不久就将逮捕。那个黑
客一出现就通知我们。”
好吧,我正等着哪。每隔5 分钟,我就到交换台去看看,然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噢,是
啦,有几个物理学家正在使用Tymnet 的计算机系统对一些高温超导体进行分析。但除此而外便
没有别的业务活动了。我的警报器和绊网都已布置好,但是连一点嘟嘟的声音都没有。
我在办公桌下又过了一夜。
6 月23 日,星期二上午,迈克·吉本斯从联邦调查局打来电话。
“你可以关门休息了,克利夫。”
“出了什么事了?”
“今天上午10 时已下达逮捕令。”
“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有人在我的系统出现。”
“出现不出现都无所谓。”
“有人被抓起来了?”
“这个我不能说。”
“你现在在哪儿呢,迈克?”
“我在匹兹堡。”
一定出了什么事。但是迈克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将等等,然后再向那个黑客关上我
的大门。
几个小时之后,沃尔夫冈·霍夫曼发来电报说:“搜查了一套公寓住房和一家公司,当时家
中无人。打印结果、磁盘和磁带都已没收,几天后将会得出分析结果。预料不会再有闯入计算
机的活动了。”
这是什么意思?我猜想警察冲进了他的公寓住房。为什么他们不等我们的信号就行动呢?
我应当庆祝胜利吗?
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终于可以关上我们的大门了。我改变了我们Tymnet 计算机系统
的口令,堵住了格努—埃梅克思编辑程序的漏洞。对于每个人的口令我们该怎么办呢?
确保计算机系统安全的唯一办法是在头天晚上改变每一个口令。然后于第二天上午逐个核
对每个用户的口令。如果你的系统只有几个人,这是简单易行的。而我们的系统有1200 名科学
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然而,如果我们不改变每个人的口令,我们就不能确保别的黑客不会偷到一个帐户。最后,
我们废掉了每一个人的口令,要求每个人挑选一个新口令,一个在字典上查不到的词。
我在这个计算机迷偷到的所有帐户中都设下圈套。如果有人要以斯文特克的姓名注册联机,
这个系统就会拒绝接受,但是它将记下有关这次呼叫来自何方的所有信息,只是让他试试而已。
马莎和我无法大规模地庆祝胜利,因为她的律师考试需死记硬背的功课把我们拴住了。但
是我们逃了一天学,跑到北部海岸去玩。我们漫步在开满野花的悬崖峭壁上,观看海浪冲击我
们脚下100 英尺深的岩石,变成白花花的水珠。后来我们下去,走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的海
湾,那里成了我们自己私人的海滩。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的一切焦虑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
外,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
在随后的几天里,从德国传来了消息。显然,汉诺威的警察同时搜查了汉诺威一家小型计
算机公司的办事处和它的一个雇员的公寓住宅。他们在这家计算机公司查获并没收了80 个磁
盘,在公寓查到的比这还多一倍。这些是证据吗?它们已被运到叫做威斯巴登的地方“供专家
进行分析”。哎呀,我自己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分析出来。只要去找“战略防御计划网络”这个
词就行。作为这个词的发明人,我一下子就可以判断他们的打印结果是否真是麦考伊计算机系
统的东西。
这个黑客性甚名谁?他到底要干什么?他与匹兹堡有什么联系?他怎么样了?我该问问联
邦调查局的迈克了。
“由于一切都已结束,你能告诉我这个家伙的姓名吗?”我问道。
“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而且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姓名,不行。”迈克回答说,表现出比以往
更不愿回答我的问题。
“好吧,我能从德国人那里了解这个家伙的更多情况吗?”我虽然不知道这个黑客的姓名,
却知道那里检查官的姓名。
“不要同德国人联系。这是个敏感问题,你会把事情搞糟的。”
“你甚至不能告诉我这个黑客是否已被关进监狱?换句话说,他是否仍在汉诺威的街上逛
来逛去?”
“这个问题不能由我来回答。”
“那么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会在适当的时机告诉你。另外,把你的所有的打印结果锁好。”
把打印结果锁起来?我看了看我的办公室。夹在两排装满计算机手册和天文学书籍的书架
之间有三个纸箱,里面全是这个黑客的打印结果。我的办公室没有锁,而且这个楼是一天24 小
时都开放的。噢,对了,看门人的小屋是可以锁上的,我可以把这些纸箱存在洗涤槽上面紧挨
着屋顶的架子上。
在迈克还没有挂上电话以前,我问他我何时可以指望听到这个案子的情况。
“哦,几个星期吧。那个黑客将被起诉受审,”迈克说。“在此期间,你不要对别人谈这件
事。不要把这个案子公布出去,还要躲着点记者。”
“为什么不能公布这个案子?”
“发表任何情况都可能使他免受惩罚。没有报纸的掺和,这个案子就够难办的了。”
“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案子是一目了然的,”我反驳说。“美国的联邦检查官说过,我们有
充分的证据给那个家伙定罪。”
“我跟你说,你对发生的情况的了解并不全面,”迈克说,“相信我的话,不要跟别人谈这
件事。”
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满意,他们也应当感到满意。尽管起初出了一些错,但迈克
始终坚持调查。可是联邦调查局却什么都不让他告诉我;对于他们的这种作法,我毫无办法。
但是他却不能阻止我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核查。
10 个月前,卢斯·阿尔瓦雷斯和杰里·纳尔逊要我把这个黑客文件看做是研究方面的问题。
好吧,调查终于完成了。噢,还有一些细节有待解决,但是实际工作已经结束。不过联邦调查
局却不肯让我发表我所了解到的情况。
在做一项试验时,你记笔记,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你就可发表你的试验结果。如果你不发
表,那么别人就无从学到你的经验,其出发点是免于别人再重复做你所做的一切。
无论如何该是改变一下的时候了。那个夏天的其余时间,我在计算机上制作望远镜的古怪
图像和在计算机中心教一些课。在跟踪那个德国人之后,我学会了如何把计算机连接在一起。
联邦调查局迟早会让我发表我的试验结果的。所以当它允许我这么做时,我应做好准备。
大约在9 月初,我开始写有关这个黑客的枯燥乏味的科学报告。我不过是从我的长达125 页的
实验笔记本中摘取一些精华,写成一篇令人生厌的文章,准备在某家不起眼的计算机杂志上发
表。
不过,停止跟踪这个黑客的活动,并不那么简单。这种跟踪活动荒废了我一年的时间。在
我跟踪的过程中,我编了几十个程序,把我的心上人抛在一边,与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
空军缉毒警察处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搅在一起,彻底毁掉了我的旅游鞋,偷窃打印机,并且在东
西海岸之间往返进行了几次飞行。由于我的生活不再围着海外某个无耻之徒的古怪念头团团转,
我在考虑我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
在此同时,在6000 英里之外,有个人却在懊悔,他要是当初从未听到过伯克利就好了。
53
在汉诺威的黑客被捕前一个月,达伦·格里菲思从加利福尼亚南部过来加入我们小组。
在工作时,我们的上司是按自己的节奏干的,而且是干他感兴趣的项目。5 点以后,一般
雇员都走了,他调高了他的工作间的立体声收音机的音量,一面听音乐,一面编程序。“音乐声
越高,代码编得越好。”
我向他介绍了过去一年黑客闯入计算机的事,心想他会对格努—埃梅克斯文件漏洞感兴趣,
但他只是耸耸肩。“嗨,谁都知道怎样利用它。不管怎样,这只涉及到几百个系统。如果你要找
到一个有意思的安全漏洞,检查一下VMS 就行了。他们的漏洞大得很,卡车都能开过去。”
“哦?”
“是的。数字设备公司的每一台使用4。5 型VMS 操作系统的瓦克斯计算机都有这样的漏洞。”
“问题出在哪里?”
达伦解释说:“任何人只要与这个系统连接起来,就可以通过执行一个短短的程序而成为系
统管理人。你无法制止他们。”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数字设备公司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这些系统毕竟是他们出售
的。”
“是的,他们寄出程序修补码,但是对漏洞的情况闭口不谈。 他们不愿让顾客惊慌失措。”
“这听起来合乎情理。”
“是的,但是没有人使用那些修补码。你怎么办?邮寄的磁带说,‘请装上这个程序,不然
你的系统可能出问题。’??你置之不理,因为你有更多的事要做。”
“那么所有系统都会受到袭击吗?”
“是的。”
“等一等。操作系统是国家安全局检查合格的。他们检测后,证明它是安全的。”
“当然,他们花了一年时间检测。但是,在他们核查了这个系统后一个月,数字设备公司
对它稍加修改。只是对口令程序作了小小的修改,”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的核查程序也有漏洞。
“现在有5 万台计算机是不安全的。”我简直不能相信。如果这个黑客知道,那他可如获至
宝了。好在我们抓住了他。
这个问题看来很重要,所以我给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的鲍勃·莫里斯打了电话。他以前也
没听说过这种情况,但是他答应调查。我干了我该干的事,向当局提出了警告。
大约在7 月底,达伦从计算机网络得到一个信息。德国海德尔堡的系统管理人罗伊·奥蒙
发现一个称为浑沌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打入了他的瓦克斯计算机。他们利用了达伦所讲的漏洞。
奥蒙的信息描述了这些破坏者怎样闯入计算机,安置特洛伊木马以获取口令,然后销掉足迹。
是浑沌计算机俱乐部吗?我听说,在1985 年,几个德国黑客结成一伙,专门“刺探”各计
算机网络。在他们看来,政府垄断只会制造麻烦——他们称之为“联邦邮政局”。他们不久就发
展成一个帮会集团,系统地袭击德国、瑞士、法国的计算机,最后袭击到美国。我以前昕到的
那些化名——彭戈、宗贝、弗林普——都是这个集团的成员??自称计算机彭克,以闯入的计
算机多而自豪。
听起来耳熟。
到夏末,问题扩大了。浑沌集团通过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空间通信网络,打入了全世界100
台计算机。等一等。还有佩特瓦克斯计算机!6 月份发出过警告——我跟踪他们,又重新跟到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络。我敢肯定,他们的联系可以一直通到德国。
不久,我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浑沌计算机俱乐部闯入瑞士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物理实
验室的计算机,给那里造成了没完没了的麻烦——据说他们偷了口令,毁了软件,破坏了实验
系统。
都是为了取乐。
浑沌集团的成员从瑞士实验室偷到进入美国各物理实验室——伊利诺伊的费米实验所、卡
尔特克公司和斯坦福大学——的口令。从那里进入航天局的网络,航天局的计算机就近在咫尺
了。
他们每进入一台计算机,就利用这台计算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