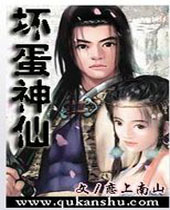杜鹃蛋-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尔特克公司和斯坦福大学——的口令。从那里进入航天局的网络,航天局的计算机就近在咫尺
了。
他们每进入一台计算机,就利用这台计算机的漏洞而成为整个系统的管理人。然后他们修
改操作系统,使他们能输入只有他们才知道的特别口令。这样,每当浑沌俱乐部的成员在受损
害的瓦克斯计算机上使用这些神秘的口令,他们就可以进入,即使原来的漏洞补好了。
问题严重。数百台计算机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可能轻而易举地破坏每个系统的软件。但是
有什么办法呢?航天局对于每一台与它的网络联结的计算机并不负责。这些计算机有一半在大
学,用于科学实验。航天局大概连一张关于与它的网络联结的所有计算机的名单都没有。
同军用网络一样,航天局的网络就象连接全国计算机的公路。窃贼自然要利用这条路,但
是很难把这归咎于筑路者。航天局只负责保持道路的完好无损。每个计算机的安全要靠使用计
算机的人。
浑沌计算机俱乐部给计算机网络的人造成了头痛的问题——他们嘲弄几百名系统管理人和
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如果你有一台瓦克斯计算机,你必须从头开始重新编制系统软件。编这么
一个软件要一下午的时间。把它乘以一千个场所。或者也许是5 万个,对吗?
最后,浑沌俱乐部耀武扬威地宣布他们打入了报界,把自己描述为才华横溢的程序编制者。
我到处寻找,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提到我的实验室、军用网络或者汉诺威,但是一无所获,似乎
他们从未听到过打入我计算机的黑客。然而,无巧不成书,在我抓住闯入计算机网络的德国人
以后两个月,一个德国人俱乐部公开它的活动,说他们已经钻进国家航天局的网络。
这可能是打入我计算机的人吗?我想了一会儿。浑沌俱乐部似乎使用VMS 操作系统,不大
知道尤尼克斯系统。我所遇到的黑客肯定知道VMS,但是使用尤尼克斯系统似乎更自如。他毫
不犹豫地利用这种计算机的任何缺陷。汉诺威接近浑沌集团的老巢汉堡,相距不到100 英里。
但是我遇到的黑客是6 月29 日被捕的,而浑沌俱乐部是8 月闯入一些系统的。
如果打入劳伦斯—伯克利实验所的来自汉诺威的黑客与浑沌俱乐部有联系,那么他的被捕
会震惊整个俱乐部。他们一听到伙伴被捕的消息就会立即烟消云散。
另一个一点是??航天局没有秘密。噢,也许航天飞机携带的军事试验仪器是保密的。但
是航天局的几乎所有其他东西,乃至火箭的设计,都是公开的。你可以买到航天飞机的蓝图。
因此这不是间谍要去的地方。
不,我遇到的黑客不是浑沌俱乐部的人。也许他同他们的俱乐部有松散的联系??也许他
查阅过他们的电子公告牌。但是他们不认识他。
浑沌俱乐部的人以一套特殊的道德标准来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他们说,只要不毁掉
任何信息,他们可以在别人的数据库里随意浏览,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
他们技术人员的好奇心比我的个人隐私权更重要。他们声称有权考察他们能够闯入的任何计算
机。
至于数据库的信息呢?如果他们能知道怎样得到这些信息,他们会迳自取阅,不会有什么
不安。假如这是一张艾滋病人的名单,或者是你去年的所得税呈报表,或者是我的信用史,那
怎么办呢?
达伦了解计算机网络,对漏洞洞察无遗,因此同他谈论这些事情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每
次谈话,他似乎都觉得有趣,但又无所谓,把黑客问题看作纯粹的智力游戏。我感到他对于我
全副注意力都被这件事吸引住并极力要抓住这个黑客颇不以为然。
终于有一天下午,我对黑客的事发了一通牢骚,悲观地估计将来会有麻烦。达伦耐心地听
完后,眼晴直盯着我。
“克利夫,”他说,“你是老手了。干吗那么担心什么人在你的系统里玩玩呢?你再年轻几
年也可能这样干。你对创造性的无政府主义的欣赏到哪里去了?”
我力图为自己辩护,就象几个月前同劳里争辩一样。我并不想让自己充当网络警察。我开
始调查是因为一个简单而莫名其妙的现象:为什么我的帐上总差75 分钱?一件事引起另一件
事,最后我跟踪起我们的朋友了。
我不是在一时气愤之余四处瞎撞,就因为这个家伙到过那儿便竭力要抓住他。我已经知道
我们网络的情况。过去我认为它们是一套复杂的技术装置,一根根纵横交错的电线和线路。实
际上它们远不止这些——它们还是一个通过信任与合作结合在一起的脆弱的群体。一旦失去信
任,整个群体就会永远消失。
达伦和其他一些编制程序的人有时表示尊重迷恋于计算机的黑客们,因为他们能考验系统
是否可靠,暴露漏洞和弱点。我可以尊重这种观点——只有严格、正直的人才会感激揭露我们
错误的人,但是我再也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了。我不是把黑客看作象棋大师,而是看作制造不信
任和偏执狂的破坏者。
夏日一天天过去,种种迹象表明此案就要了结了。迈克·吉本斯没有给我打电话,而且很
少回我的电话。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了解这个案子技术方面的问题——计算机的漏洞和闯入者所呆的地方。我要知道的就是
这些吗?但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这不能令人满意。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我想知道谁干的,为什么这样干。
54
谁在幕后?要找到答案,只有一个办法:认真调查研究。
联邦调查局只对我说:“静一静,不要提问。”这没有什么帮助。
也许我到处打听干扰了正在进行的审讯。但是,如果有什么审讯的话,他们肯定需要我的
合作。我毕竟有非常重要的证据:2000 页打印出来的东西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箱子里,箱子
锁在房屋管理员的柜子里。
即使我不能提问,我仍然可以作科学调查。发表调查结果,同调查一件不寻常的怪事一样,
也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就我这件事来说,科学调查大概更重要。关于这个黑客的消息传开了,
军事部门有人开始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更多的消息。我应该告诉他们什么呢?
8 月底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个黑客整整一周年,是我们最后在汉诺威抓住他以后两个月。
联邦调查局仍然要我保持沉默。
当然,从法律上说,联邦调查局不能阻止我出版或者到处打听。马莎态度很坚决:“你愿意
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她应该知道,因为她正在学习宪法,准备应付律师资格考试。再过3 个星期,一切就都过
去了。为了让她的脑筋摆脱考试,休息休息,我们开始给被子加图案。只是不时地这里或那里
缝几分钟,但是图案越来越大.尽管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很漂亮的图案慢慢出现了。
我们刚开始剪碎片,劳里就来吃午餐了。
劳里和马莎谈着被子的花样,每个花样都有古老而浪漫的名字。听着她们说话,我感到非
常温暖。这是我的家,我的爱。我们现在做的被子可能跟随我们一辈子,实际上,在我们死后,
它仍然存在,给我们子孙以慰藉??。
我想得太远了。我和马莎毕竟还没有结婚,只是住在一起,只是在对两个人都有好处的时
候共同生活,如果合不来了,可以分手。这样比较好,比较开放,比较开明。不是那种“到死
才分离”的老式结合。
当然是这样。
“这该是你们结婚用的被子。”劳里的话触及我心底深处的思想,使我吃了一惊。我和马莎
都瞪眼看着她。
“真的。你们俩已经结婚——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近8 年来,你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和情
人。为什么不把关系正式定下来,庆祝一番昵?”
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劳里说的完全是实情,而且也太明显了,我反而视而不见了。我一直
在想,我们只应该在一段时间里继续这种关系,在情况好的时候,“暂时”住在一起。说真的,
在日子艰难的情况下,我会离开马莎吗?要是别的什么人更能吸引我,我会离开她吗?我想成
为那种人吗?我希望有生之年那样生活吗?
当时我意识到该做什么,我希望怎样生活。我看着马莎,她表情平静,眼睛注视着颜色鲜
艳的布片。我含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我看着劳里,求她帮忙,但是她一看我的脸,就到厨房
去沏茶了,留下我和马莎。
“亲爱的?”
她抬起头,凝视着我。
“你希望什么时候结婚?”
“明年春天,雨季过后,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怎么样?”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们义无反顾,没有后悔,也不去环顾周围有没有更好的人。我和
马莎将一起度过有生之年。劳里倒茶,我们坐在一起,没有多少话,但是很幸福。
到10 月份,我又开始考虑黑客的事。我和达伦争论要不要发表一项报告。“如果你不说,”
达伦争辩说,“别的黑客还会破坏其他人的计算机。”
“但是,如果我发表了报告,那就会教会许多黑客,使他们知道怎样干了。”
1 月份是逮捕黑客后6 个月,是我们首次发现他以后一年半,然而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时该是发表我的跟踪结果的时候了。
所以,我把报告寄给《计算机协会通讯》。尽管你在报摊上买不到这个刊物,但是多数计算
机专业人员可以看到它。它是真正的科学刊物:每篇文章都有人介绍。这意味着另有3 个计算
机专家核对我的文章,以匿名方式发表意见,说明是否应该发表。
文章原计划登在5 月号上。计算机协会和劳伦斯—伯克利实验所准备在5 月1 日一起宣布
这件事。
5 月份我们忙得一塌糊涂。我和马莎计划在月底结婚。我们预订了伯克利玫瑰园,缝好了
结婚礼服,邀请了亲戚朋友。即使没有公布黑客的事,这个月也不会安静。
但是.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德国《快捷》杂志抢了先。他们在4 月14 日刊登一条
消息,说明一个德国黑客是怎样闯入36 个军用计算机的。虽然他们的记者设法见到了那个黑客,
但是大部分消息出自我的工作日记。
我的工作日记!《快捷》杂志是介于《生活》杂志与《国民问询》杂志之间的刊物,它怎么
会得到我的实验室日记呢?我的工作日记保存在计算机里——在磁盘上,而不是在纸上。难道
有人闯入我的计算机并翻看了我的工作日记吗?
不可能。我的工作日记存在我的麦金托什计算机里,我从来没有把这台计算机同任何网络
连接,而且每天晚上我都把磁盘藏在桌子抽屉里。
我重读了翻译过来的那篇文章.意识到有人在1 月份得到一份我一年前的工作日记,把它
泄露出去。过去我编造过假的战略防御计划网络。我把那篇日记的复印件给了什么人吗?
是的,我是给过人。1 月10 日,我把工作日记给了联邦调查局的迈克·吉本斯。他一定把
它交给了驻柏林的法律专员。谁知道后来又转到什么地方了?
有人把它透露给《快捷》杂志。他们先于我两周发了消息。该死的!
保持了一年的沉默,同当局进行了一年的秘密合作,结果却卖给了德国一家廉价的杂志。
多么可悲!
《快捷》杂志虽然得到一份我的笔记,但说的根本不准确。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只有由我
们自己把事实揭示出来。该死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晚了。约翰·马科夫——现在《纽约时报》——听到这个消息,提出了
一些问题。该死的!只有一件事能做:我的实验所宣布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讲。该死
的!
那天晚上11 点,我忐忑不安,担心得很。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家安全局打给我的电话
也没有给我任何帮助。
国家安全局计算机安全中心的负责人萨莉·诺克斯也在城里。她听说第二天要举行记者招
待会。“你不敢提我们的名字吧?”她的声音直震耳朵,“讲我们坏话的报道够多的了。”
我看看马莎。她听到电话里传出的这个女人的声音,眼珠直转。我极力安慰这个特工人员。
“听我说,萨莉,国家安全局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不会说你们的资金应该削减。”
“这没有关系。新闻界一听到我们的名字,就会有麻烦事。他们歪曲任何有关我们的事情。
他们绝不会发表一篇公正的报道。”
我看看马莎。她示意让我把电话挂上。
“行,萨莉,”我说,“我保证连你们局的名字都不提。如果有人问,我只说‘无可奉告’”。
“别这样说。那些猪猡会四处乱嗅,寻找更多的消息。告诉他们,我们与此事无关。”
“听着,我不想撒谎,萨莉。不管怎样,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难道不是一个不保密的公开
机构吗?”
“是的,但是这不能成为听任报界到处打听消息的理由。”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派一个人来参加我的记者招待会?”
“我们没有一个雇员受权能同新闻界谈话。”
抱着这种态度,难怪新闻界对她的机构的报道这么坏了。
马莎给我写了张条子:“问她有没有听说过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我插不上嘴。萨利接着
大声嚷了25 分钟,试图说服我不要提国家安全局或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
此时已是深夜11 点30 分,我筋疲力尽,再也受不了了。我要想办法挂了电话。
“听我说,萨莉,”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唠叨完?请你告诉我不能说什么。”
“我不告诉你该说什么。我告诉你不要提计算机安全中心。”
我把电话挂了。
马莎在床上翻过身来,看着我。“他们都是这样吗?”
第二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记者云集。我习惯于参加科学会议和技术讨论会。我总听说记者
招待会,但是并没有亲眼见过。现在我成了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提问的目标。
记者招待会很热闹。我和上司罗伊·克思讲了半小时,回答记者的问题。电视记者问的问
题很简单(“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你感觉怎么样?”)报社记者问的问题尖锐而难以回答——“国
家应该制订怎样的计算机安全政策?”或者“波因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