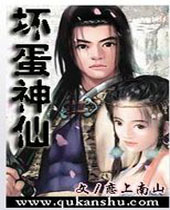杜鹃蛋-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行踪很难发现:联邦调查局监视着他,无论谁控制他,都不会满意。
但是西德警察有大量对马库斯·黑斯不利的证据;打印材料、电话窃听记录和我的工作日
记。他们在1987 年6 月29 日闯进他的住房时,没收了100 张软盘,一台计算机和介绍美国军
用网络的文件。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但是,在警察搜查黑斯的住房时,没人在屋子里。尽管我正在耐心地等待他出现在我的计
算机里,德国警察闯进去时,他还没有同我的计算机接上。
在第一次审讯时,黑斯在上诉后获释。他的律师争辩说,在警察搜查黑斯的住处时,黑斯
没有同我的计算机连接上,所以他可能没有干闯入别人计算机的事。这一点再加上搜查证的问
题,足以推翻对黑斯盗窃计算机信息的控告,但是德国联邦警察还在继续调查。
1989 年3 月2 日,德国当局指控下列5 人犯有间谍罪:彭戈、哈格巴德、彼得·卡尔、德
克·布雷津斯基和马库斯·黑斯。
彼得·卡尔定期在东柏林会见克格勃特务,出卖其他几个人可能窃取的任何资料。德国联
邦刑警局抓他时,他正要逃往西班牙。他现在在监狱里候审。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因从德国军队
开小差而坐牢的德克·布雷津斯基。
彭戈正在重新思索那些年为克格勃所干的事。他说,他希望他当时能“采取正确做法,向
德国警察当局详细说明我卷入这件事的经过原委”。但是,只要这个现行刑事案还在审理之中,
他什么也不愿说。
事情公开报道以后,彭戈在企业中的伙伴不再支持他了,他负责的几个计算机项目被取消
了。除了企业上的损失外,我说不准他是否认为他做错了什么事。
今天,马库斯·黑斯保释在外,漫步于汉诺威街头,等候间谍案的审讯。他抽的是本森和
赫奇斯牌香烟。他不时左顾右盼,提防别人。
哈格巴德同黑斯合伙干了一年。在1988 年底,他试图戒掉可卡因,但那是在花光了克格勃
给他的钱以后。他负债累累,又没有职业。1989 年春,他在汉诺威一政党的办公室谋得一个差
事。他因为与警察合作而没有被以间谍罪起诉。
哈格巴德死于1989 年5 月23 日。在汉诺威郊外一片孤立的树林里,警察在一个熔化的汽
油桶旁边发现了他烧焦的骨头。借来的车停在附近。没有发现自杀的迹象。
56
我开始这次跟踪黑客的活动时,把自己看作一个从事世俗工作的人。我干我分配干的工作,
避开权势,对重要问题总是站在外围旁观。我冷漠,不介入政治领域。是的,我模模糊糊地认
为自己同60 年代的老左翼运动是一致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我的工作与社会的相互关
系??也许我选择天文就是因为它同地球上的问题关系很小。
现在,我发现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都依靠计算机,在这方面他们是协调一致的。右派认为
保证计算机安全是保护国家机密所必要的;我的左翼朋友则担心这些潜入计算机的分子偷窃数
据库信息会侵犯他们个人的隐私。政治上的中间派意识到,如果计算机的资料被外人利用,失
去安全的计算机就会造成金钱上的损失。
计算机成了一个没有知识、政治或官场界限的最起码的共同点,成了全世界跨越任何观点
的必需品。
意识到这一点,我主张对计算机安全问题积极采取行动。我非常担心易受攻击的数据库的
保卫工作。我想知道金融网络上出什么事,那里每分钟都有千百万美元流过。我感到气愤,联
邦储备委员会似乎并不注意巨大的财富。我感到不安,掠夺者大大增加了。
你可以制造安全的计算机与网络,可以制造外人不能轻易进入的系统,但是这些系统通常
都难以使用,不方便,并且速度很慢,费用昂贵。计算机通信的费用已经很高了,要是再增加
密码编制和复杂的鉴别计划,那只能使费用更高。
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似乎成了国际间谍袭击的目标和供他们利用的渠道。想一想,如果
我是情报机构的特务,我会干什么呢?为了搜集秘密情报.我可能训练一个特工人员讲某种外
语,然后派她到一个遥远的国家,给她钱让她去行贿,但是担心她可能被抓住或者只得到假情
报。
我也可以雇一个不正派的计算机程序编制者。这种间谍不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发
生丢人的事的危险不大。花钱也少——几台小型计算机和同一些网络的连接。得到的情报新,
直接来自目标的文字处理系统。
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不能直接打电话进去:阿尔巴尼亚。这对间谍活动的未来意味着
什么?
噢,我在想什么呀?我不是间谍——我只是一个长期脱离社会的天文学家。
我关掉监视器,卷起接线。此时我意识到,这一年来,我陷入了迷官。我以为我设下了陷
阱。那个黑客寻找军用计算机时,我正在探索不同的团体——在网络上,在政府里。他打入了
三四十台计算机,我只找到了12 个组织。
我自己的探询改变了。我认为我是在寻找一个黑客。我以为我的工作与我的家或者我的国
家没有关系??我毕竟只是干我的工作。
现在我的计算机安全了,漏洞堵住了。我骑车回家,拿起几个草莓,同打成泡沫的牛奶混
在一起,给马莎和克劳迪娅。
杜鹃在别的鸟窝里下蛋。我又回到天文学上。
尾声
在我竭力设法结束对黑客的追踪时,我们还要筹备婚事。这段时间十分忙碌,我咒诅我的
工作(还有黑斯)分散了我对家庭生活的注意。我们在5 月底结婚.所以4 月的意外事情特别
令人烦恼。大部分准备工作是马莎做的。
然而,她诸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决心要使婚礼体现我们的性格。我们用丝网印染法印制我
们的请帖,说我们两人以及我们的家属邀请他们光临。丝网上的墨水自然要渗漏出来,一半请
帖上有我们的指纹,但这是家庭计划的一部分。
马莎穿白色礼服,带白色披纱吗?我要穿无尾晚礼服吗?太可笑了。劳里穿伴娘的服装吗?
从来没有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让劳里穿上什么服装。我们最后总算决定好了。劳里穿白亚麻布
裤子,剪裁舍身的夹克。马莎穿一套简单的淡黄色服装。我给自己缝了棉布衬衫。(什么时刻试
试给自己做衬衫,你会知道更加尊重做衬衣的人,尤其是在从背面缝完袖口以后。)
我们举行婚礼时,天下着雨,玫瑰园没有地方躲雨。克劳迪娅的四重奏班子打开一张雨布,
给小提琴遮住了瓢泼大雨。我姐姐珍妮在海军学院一下课就赶来了——一来就同劳里辩论起政
治问题。婚礼结束以后,在乘车前往海边一家偏僻的小旅馆时,迷了路。
尽管如此,一切都很美好。不管你对结婚怎么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当然,我可以继续只与马莎同居,所尽的义务不超过支付下个月的房租。我同其他几个人
这样随便地在一起住过,说我们相好,但是随时准备在关系不好时分手。我们以开放和摆脱压
制性传统束缚的话来粉饰自己,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是借口。事实上,我从来没敢把自己完全
交给什么人,从未下决心使关系永远保持下去,不管关系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我十
分爱慕与信任的人,我得到勇气坚持下来,不仅坚持到现在,而且直至永远。
但是家庭的幸福并不能解决一切——我还得考虑下一步干什么。黑斯的面目清楚了,我可
以回到天文学上去或者至少回到计算机上。不用把时间完全放在跟踪国际间谍上,但是到处都
需要进行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知道你的学科会使你取得什么成果。
情况不一样了。干计算机的人认为我在过去两年把时间浪费在跟间谍打交道上。天文工作
者们知道我两年没干本行工作。我今后该往哪里走?
马莎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在海湾那边的旧金山给一位法官当书记员。她喜欢这项工作——
作审讯记录,研究案例,帮助草拟决定,相当于法学院研究生的工作。
她在波士顿找到另一个书记员的工作,1988 年8 月开始。她边吃草莓牛奶,边讲述各种可
能。
“我到波士顿巡回法院当书记员。那里学术味更浓——不审讯,只有上诉的案子。可能很
有意思。”
“还有其他选择吗?”
“嗯,我想再去上学,完成法理学的学位。那要几年时间。”总是学习。
我离开伯克利跟她去马萨诸塞吗?
决定很简单:她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如果她去波士顿,我就设法在那里找一份工作。
幸运的是,哈佛史密森氏天文物理中心要一个既懂天文学又懂计算机的人,一个会掌管X 光天
文学数据库的人。
我们对伯克利恋恋不舍——草莓、街头自动售货机、阳光。不过我们和同住一套房子的人
签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我们随时可以去,并且不用洗碗;他们也可以在马萨诸塞州我们住的
地方逗留,只要给我们带些加利福尼亚的猕猴桃就行了。
最难受的是离开好友克劳迪娅。我已经习惯于听她深夜练习莫扎特的乐曲了。她还没有找
到一个同住的人,尽管几个有希望的音乐家在我们离开时向她献过殷勤。最近的传说吗?是的,
有一个漂亮的乐队指挥在追她。
这样,在1988 年8 月,我们收拾了两个箱子,准备了在马萨诸塞住一年的东西。
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东海岸有几个好处。我的计算机网地址改变了??这是件好事,因为
在我发表那篇文章后,几个黑客曾试图闯入我的计算机。有一两个人以各种方式威胁我——因
此最好不要使他们得到一个静止不动的目标。各种保密组织不再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建议、
看法和听到什么传说。现在在坎布里奇,我可以一心扑在天文学上,忘掉计算机的安全问题和
黑客们。
在过去两年中,我成为计算机安全专家,但是没有学到任何天文学知识。更糟糕的是,我
对X 光天文物理学一无所知:我习惯于行星学,而行星是不释放X 光的。
那么X 光天文学家研究什么呢?太阳,恒星和类星体,探索星系。
“星系爆炸吗?”我问天文物理中心的新上司史蒂夫·默里。“星系不爆炸。它们只是成螺
旋状呆在那里。”
“你是在70 年代学的天文学,”史蒂夫回答,“我们研究恒星爆炸成超新星,中子星爆发出
X 射线,甚至物质陷入黑洞。在这里呆一段时间,我们会教给你一些真正的天文学。”
他们并不是开玩笑。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坐在计算机后面,建立X 射线观察结果的数据库。
这里有标准计算机,但是还有第一流的物理学。在星系的中间确实有黑洞。我看过资料。
史密森氏天文物理实验室与哈佛观象台在同一个楼里。自然谁都听过哈佛观象台,但是史
密森氏学会呢?那是在华盛顿,不是吗?我到了坎布里奇后才意识到史密森氏学会有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天文学部门——天文物理中心。这对我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他们在天文学方面有出色
成就就行了。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可能也许使人觉得远在天边,但是从文化上说,它同伯克利很接近。
有不少60 年代的嬉皮士,左翼政治活动、书店和咖啡馆。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音乐家在街头
演唱。在商业区的地铁车站,吉他和曼陀林演奏着小夜曲。还有一些居民区,那里的一些房屋
已有一百年之久。在坎布里奇骑车十分惊险——司机直冲你开来。悠久的历史、超凡脱俗的市
民、优秀的天文学、便宜的意大利馅饼??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理想的生活之地。
婚姻生活吗?除了马莎不让我动微波炉外,一切都是美满幸福的。
1988 年11 月2 日,星期三,我和马莎朗读一篇小说,一直到午夜才盖上被子睡觉。
正当我梦见自己躺在一片橡树叶上漂游时,电话铃响了。该死的。夜光钟指示是凌晨2 点
25 分。
“喂,克利夫,我是吉恩,航天局埃姆斯实验室的吉恩·米亚。我不得不把你叫醒。我们
的计算机受到袭击。”他激动的声音使我清醒过来。
“醒一醒,检查一下你的系统,”吉恩说,“如果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给我打电话。”
我挂上电话。10 秒钟后,电话铃又响了。这次只是发出尖而短的声音,是莫尔斯信号的声
音。
我的计算机在呼叫我,要我去看一看。
噢,天哪,躲不住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可靠的老麦金托什计算机前,拨了哈佛观象台计
算机号码,打下我的帐户名克利夫,然后打下字典上找不到的我的口令ROBOCAT。
连接很慢。5 分钟后.我不再尝试了。我的计算机就是没有反应。出毛病了。
好吧,只要我不睡着,我也许可以看到西海岸的情况怎么样。也许那里有一些电子邮件在
等着我。我通过Tymnet 接通劳伦斯—伯克利实验所,但是没有我的长途电话。
伯克利的尤尼克斯系统也很慢,慢得令人沮丧,但是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人用它,这就是
达伦·格里菲斯。
我们在屏幕上交换了一些信息:
你好,达伦。我是克利夫。
情况怎么样:…)
克利夫,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们受到袭击。
行0…0
0…0 的意思是完了关机。:…)是一付粗犷的笑脸。你斜着看,它对你微笑。
马萨诸塞是凌晨两点15 分,但是伯克利还不到午夜,离达伦睡觉还早呢。
“喂,达伦,这次袭击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东西在侵蚀我们的系统,使许多过程开始运转。系统运转很慢。”
“一个黑客吗?”
“不,我猜想是病毒,但是现在还说不清,”达伦一边打字一边慢慢地说。“我才干了10 分
钟,因此还说不准。”
我想起了吉恩·米亚的电话。“航天局的埃姆斯实验室讲到同样的问题。”
“嗯,我敢肯定我们受到ARPANET 的袭击,”达伦说,“看一看所有这些网络的联系吧。”
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要我用电话讲话,我的计算机就不能接上,我就什么也看不见。因
为只有一根电话线,我要么使用电话讲话,要么用麦金托什计算机同另一台计算机通话,不能
两者同时使用。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