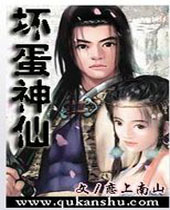杜鹃蛋-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有两种办法可以了解这种病毒,”唐说。“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是进行分解,一步步跟
着计算机代码,弄清它要干什么。”
“行了,”我说。“我试过这种办法,不容易。第二种是什么?”
“把它当作黑匣子。观察它把信号送入其他计算机,估计里边有什么。”
“有第三种办法,唐。”
“什么办法?”
“发现谁编的病毒。”
我扫了一眼计算机网络新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彼得·伊和基思·博斯蒂克正在揭
开病毒的秘密,他们描述了尤尼克斯的漏洞,甚至公布了修补软件的办法。干得不错!
不到一天,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乔恩·罗克利斯,斯坦·扎纳罗蒂,特德·曹以及马克·艾
钦就开始分解病毒程序,把位和字节译成意思。到星期四晚上,即病毒放出后不到24 小时,马
萨诸塞理工学院和伯克利的两组人就分解了代码,在破解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弹道研究实验所的迈克·米斯也取得了进展。不到几小时,他就建起了病毒试验室,用软
件工具来刺激病毒。他从实验中知道病毒是怎样扩散的,利用什么漏洞传染给其他的计算机。
但是谁编制的病毒呢?
大约在上午1l 点,国家安全局的全国计算机安全中心有人给我打电话。
“克利夫,我们刚刚开会讨论了病毒的问题,”打电话的人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是
你编的病毒吗?”
我感到惊愕。我?编这种病毒?
“不,该死的,我没有编。我昨天一夜都在想办法消灭它。”
“会上有一两个人提出你是最可能的制造病毒的人。我只是核对一下。”
你一定在开玩笑。我?什么事会促使他们认为是我编的呢?我想起来了。我给他们计算机
送去了信息。我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他们的。真是偏执狂!
他们的电话引起我的思考。谁编了病毒?为什么?一个人不会无意识地编一种病毒。编这
种程序需要花好几个星期。
星期四晚,我给鲍勃·莫里斯打电话。“有什么消息吗?”我问他。
“我总会把真相告诉你的。”鲍勃说,“我知道是谁编的病毒。”
“你打算告诉我吗?”
“不。”
现在他们的效率很高,我打电话后10 小时,全国计算机安全中心就发现了作案者。
但是我没有发现,他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所以我还得在网络上窥探。要是我能发现第一
台被传染的计算机就好。不,那不行。那里有成千上万台计算机。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打来了电话:“我听说编病毒的人姓名的首字母是RTM。这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多大帮助,不过我要查清楚。”
怎样从姓名的首字母上找到这个人呢?当然??你可以从网络名册上查找。
我接通网络信息中心,寻找首字母是RTM 的人。忽然出现了一个名字:罗伯特·T·莫里斯
(ROBERT T MORRIS)。地址:哈佛大学艾肯实验室。
艾肯。我听说过。它离我的住处三个街区。我想我可以走过去。
我穿上外衣,走上柯克兰街,然后转到牛津街。那条街上的人行道是用砖砌的。在哈佛回
旋加速器实验所对面,隔着大街,有一个卖中东食品的餐车。100 英尺外就是艾肯计算机实验
室——在一群古色古香的维多利亚建筑之中的一座难看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
我走到一位秘书的身边。“你好。我找罗伯特·莫里斯。”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她说。“不过,我要用计算机核对一下。”她把信息打入终端:
指定莫里斯
她的计算机回答:
注册姓名:RTM 实际姓名:罗伯特·T·莫里斯
电话:616/498/2247
最后一次接通的时间:11 月3 日星期四零点25 分,使用TTYP2,
来自128。84。254。126
罗伯特·莫里斯最后一次使用哈佛计算机的时间是在午夜过后25 分钟,在病毒袭击的那天
凌晨。但是他不在马萨诸塞,那个地址128。84。254。126 在康奈尔大学。他是从康奈尔大学的一
台计算机进入哈佛系统的。真奇怪。
秘书看到这段信息,抬起头,对我说:“噢,他一定在这里学习过。电话号码是3 号房间的
号码。”
我走到3 号房间,敲了敲门。一个穿着短袖汗衫的学生探出头来。“听说过罗伯特·莫里斯
吗?”我问。
他的脸发白了。“听说过。他已经不在这里了。”门砰地一下在我面前关上了。
我走开了,想了一会儿,又返回来。“你听说过病毒吗?”我在门口问那个小伙子。
“RTM 不会干那种事。我敢肯定。”
等一等。我并没有问莫里斯有没有编病毒,这个小伙子就否定了。有一个容易的办法考验
他是不是诚实。“莫里斯晟后一次使用哈佛的计算机是什么时候?”
“去年,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现在在康奈尔,再也不和我们的计算机联机了。”
这小伙子的说法与他的计算机的会计记录不一致。他和计算机这二者总有一个讲的是真话。
我要信赖计算机。
我们谈了5 分钟。他告诉我他是莫里斯的好朋友,他们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RTM 绝不会
编计算机病毒。
“是的,”我想。
我走了,心想莫里斯的老办公室同事在为他隐瞒。莫里斯必定同这个小伙子谈过,两人都
吓坏了。我在这种压力下也会害怕的。半个国家都在寻找制造这种病毒的人。
病毒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检查了坎布里奇的其他计算机,寻找与康奈尔的联系。马萨诸
塞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显示出罗伯特·莫里斯在康奈尔的计算机深夜同它进
行了联系。
现在有眉目了。病毒是在康奈尔设计并制造的。制造者利用ARPANET 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
连接,向那里放出病毒,过了一会儿,当他意识到他创造出的东西失去控制时,他感到惊慌失
措了,所以他接通哈佛的计算机,可能是要检查病毒发展的情况,也可能是请他的朋友帮忙。
然而,该取笑的是我。我没有想到小罗伯特·莫里斯是鲍勃的儿子??老罗伯特·莫里斯。
是的,鲍勃·莫里斯的儿子。鲍勃·莫里斯昨天才告诉我,他知道邮件传送系统的漏洞有好几
年了。鲍勃·莫里斯这个头头曾盘问我天体物理学的问题,他抽的烟差点儿把我憋死。
鲍勃·莫里斯的儿子使两千台计算机停止了工作。为什么呢?向他爸爸显示他能干?还是
万圣节的恶作剧?或是向两千名编制计算机程序的人显示他的才能?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我不相信他是与他父亲合伙干的。传说他同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的一
两个朋友合作,但是我不相信他父亲会鼓励什么人制造病毒。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乔恩·罗克利斯分解了代码以后说,这种病毒“编得并不很好”。它与
众不同的是它从几个方面袭击计算机:尤尼克斯邮件发送系统和指定程序,猜测口令,利用计
算机之间的信任。另外,莫里斯还从几个方面对程序进行了伪装,以免被发现。但是他犯了几
个程序编制上的错误,这种蛀虫也许许多学生或程序排制人员都能编写出来。
一旦你知道这种特别的蛀虫——病毒是怎样传染计算机的,医治它的办法就很明显了:修
补邮件发送系统和指定程序,改变口令,销掉系统病毒的所有复制件。显而易见吗?是的。容
易吗?不容易。
传话并不容易,因为大家都在切断电子邮寄系统。蛀虫毕竟是以这个途径生儿育女的。利
用其他的网络和电话,消息渐渐传开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莫里斯的蛀虫大部分被消灭了。
但是我怎样防止其他病毒呢?希望并不大。由于病毒伪装成合法程序的一部分,所以很难
发现。更糟的是,一旦你的系统被传染,很难了解它们。编制程序的人不得不破译代码,这是
一种单调而又费时间的工作。
幸运的是,计算机病毒很少。尽管现在人们喜欢把系统的问题归咎于病毒,但是病毒只袭
击那些交换软件和使用计算机公告牌的人。同样幸运的是,这些人通常知识丰富,有备份磁盘。
计算机病毒的效用有专一性: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上有效的病毒,对麦金托
什计算机或者尤尼克斯系统就无能为力。同样,ARPANET 的病毒只能袭击使用伯克利尤尼克斯
系统的计算机。使用其他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尤尼克斯、VMS 或者DOS
都不受传染。
多样化也可以抵御病毒。如果ARPANET 的所有系统都使用伯克利的尤尼克斯系统,病毒可
以使5 万台计算机全部瘫痪。实际上,这种病毒只传染了2000 台。生物病毒也有专一性:我们
不会从狗那里传染上感冒。
官员和经理人员永远会劝我们以一种系统为标准:“让我们只用太阳公司的工作站”,或者
“只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系统”。然而,我们的计算机大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成员。同我们的邻
里一样,电子家庭通过多样化而兴旺发达。
在这段时间,我在天文学方面干了多少工作呢?
什么也没有干。在这36 个小时中,我设法消除我们计算机里的病毒。然后是开会,写报告。
还有两个模仿制造病毒的人,幸运的是,没有一个象原设计者那么聪明。
我最后听说,罗伯特·莫里斯躲起来不露面,避开记者采访,想知道有多大可能被起诉。
他父亲仍在国家安全局,仍然是计算机安全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这次损失有多大?我对网络作了调查,发现在15 小时内有2000 台计算机被传染。这些机
器完全瘫痪,在病毒消除以前完全不能使用。消除病毒往往要两天的时间。
假设什么人使2000 辆汽车瘫痪,比如说把轮胎的气放掉,你怎么计算损失?从一个方面衡
量,没有任何损失,汽车完好无损,只要打上气就行了。
你还可以从失去汽车的角度来衡量。让我们看一看:如果你的车一天不能开,你有多大损
失?派一辆拖车出去花多少钱?租一辆车多少钱?你有多少工作没干?这就很难说了。
也许你要感谢给轮胎放气的人,因为他增强了你的汽车安全意识。
现在有人使2000 台计算机瘫痪了两天。造成了多大损失?程序编制人员、秘书和经理人员
不能工作。资料不能收集。科研项目推迟了。
编制病毒的人至少造成了这样大的破坏。还有更深一层的破坏。在病毒袭击后不久,一些
天文学家和程序编制人员接受了民意测验。一些使用计算机的人认为病毒是一种无害的恶作剧
——这是最有意思的笑话之一。
天文学家的看法不一样。整整两天,他们无法工作。他们的秘书和研究生不能工作。建议
和报告没法写。我们从自己腰包里掏钱支付他们与网络联结的费用——这种恶作剧使得扩大天
文学网络更加困难了。
一些程序编制者把这次病毒事件看作提高计算机安全意识的一次有益的演习。应该感谢编
造病毒的人。是的,就象小偷进入一个小镇,闯进人家家里,结果让镇上的人深深感到有必要
买牢固的门锁。
从前我也会认为这种病毒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在过去两年中,我的兴趣从微观问题(7
毛5 分钱的差额)转到宏观问题:我们网络的福利,一般的做事光明磊落的意识、袭击计算机
的法律影响、国防承包商的安全、计算机领域的公共道德等问题。
天哪,听我自己这样高谈阔论,我意识到我已经成年了——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人。
我想我已经成年了。
最精彩的B 级电影《一小滴》的结尾是把那个恶魔拖到南极:它在冻僵状态不能作恶了。
然后,“完”字从屏幕上闪过去,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出现了一个小滴形状的问号。魔鬼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当我最后拆掉监视器的联线,在工作日记册上记上最后一天使用的情况,正式结束了深夜
追踪马库斯·黑斯的活动时,心里曾有这样的感觉。
魔鬼还在那里,随时会活过来。每当什么人受金钱、权力或者只是好奇心的诱惑而偷窃口
令,潜入计算机网络时;每当什么人忘记他喜欢玩弄的网络很脆弱,只有在人们互相信任的情
况下才能存在是;每当一个喜欢开玩笑的学生当作游戏一样闯入计算机系统(就象我以前可能
干过的那样),而忘记他在侵犯别人的隐私,危及到别人辛辛苦苦整理的资料,种下不信任与偏
执的种子的时候,魔鬼还会活过来。
电话铃响了,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所打来的。我离开那个地方是因为他们设计核弹。
一个黑客打入了他们的计算机,他们要我帮忙,认为我是专家。(全文完)
在此特别感谢CCF 的FatCatHu 和nickwolfe 辛勤的OCR 劳动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