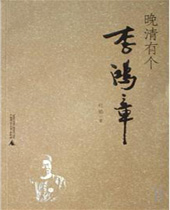议李鸿章及民主-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在 水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欣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 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