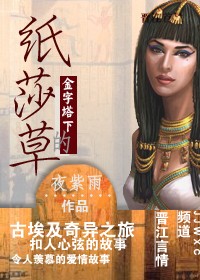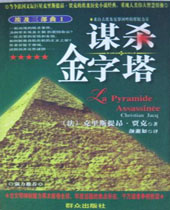我钻进了金字塔-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现在,石油收入全部归伊拉克政府,这正是西方国家借口人权攻击萨达姆的根本原因。
巴格达解放广场的旧货市场,可以买到“任何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战争使伊国人对本国货币毫无信心,对美元却近乎疯狂的崇拜。一架德国产8*10蔡斯望远镜才20美元,而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头巾的家伙20美元卖给我一只“欧来茄”海王手表,可当我戴到手腕上才发现,除了秒针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这位潜入人流的老兄时,他已摘掉头上的围巾,露出满脸大胡子。他宽宏地同意。“买回”那只表,不过只能“付”我10美元。当然,我也有赚的时候,一支派克45型钢笔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军刀3美元。在一个相机摊上,竟发现一台带MD一4马达、135mmF2镜头的尼康F3,我屏气凝神强压住激动问摊主100美元能否成交,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美得我扔下120美元,抄起相机就跑。跑出百米之后,我才仔细打量这台磨得露了黄铜、镜头上还打着“美联社”标志的黑市货。可等我返回使馆,使馆的小于却迎面泼来一瓢凉水:“这台相机昨天开价才80美元!”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也在秘密地拍卖财产,但避开新闻界,只对各国使馆开放。我和小于开着中国使馆的卡车到美国使馆一举买下了美国人10台崭新的“将军”牌空调。
波兰外交官托马斯作为美国利益代表现场拍卖,偌大的库房中堆满了冰箱、洗衣机、家具、吸尘器、铝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导我和使馆的小于到使馆后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后借机献媚:“小姐,你真美!美国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妈生在贝鲁特。你是记者?”
“不!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欢迎你来中国使馆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爱!”
“你真迷人!顺便问一下,那些电脑卖吗?”
“所有电脑都已卖给了印尼使馆。”
“真可惜我来晚了。亲爱的,能否这么理解:美国使馆把能卖的全卖了?”
“可以这么说!”
拍卖大厅的警卫不许我进,理由是我身上有相机,此间的拍卖是严禁记者采访的。我把大花裤权卷至大腿根,红背心撩至胸口,腆起脏汗横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车车门上:“有我这样的记者吗?我是使馆的司机兼厨师,我只想给自己留个影!”警卫对视了一下:“看来你也干不了用脑子的活儿。”当天,我在发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缀语:“看来,一个把房产之外的财产全卖了的使馆短期内不会改善两国关系。”这张质量极差的传真照片竟馋得美联社贾西姆啧啧称羡,这是1993年7月的事。
《纽约时报》驻白宫主笔迈克尔·凯利在他的《殉难日》一书中称巴格达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一名腰缠万贯的约旦投机商称:“这里到处都是漂亮小妞儿,你可以廉价地‘威凯威凯’。”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在底格里斯河畔就碰上一个在旅游学院学英语的姑娘,她的前胸赫然印了一行大字:“Suckit(吮这儿)!”还以职业的温柔死缠着和我们合影,我们不得不正言以对:“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不由想起一句悲伤的中国古语:“卿夺佳人,奈何作贼。”
入夜,古老的巴格达笛声悠扬、锣鼓喧天。伊拉克政府正在市中心猎人俱乐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9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的长子乌代也在其中。由于经济困难,伊政府号召人民摈弃传统奢华的阿拉伯婚礼,代之以爱国主义的集体婚礼,萨达姆总统让其长子乌代以身作则。
伊拉克政府为参加集体婚礼的新娘提供(借用)婚纱,向新郎赠送西装,并允许每对新人的50位亲戚免费出席集体婚礼,享受国际封锁下罕见的“库兹”(烤羊腿)。断腿的民歌手伊斯麦坐在椅子上唱着悠扬的歌,他的双腿是海湾战争中被美国飞机炸飞的。一位来看热闹的小姐国难不忘美容,卷了乌发、润了粉颜,还从容不迫地坐在民歌手身旁染指甲。
举办集体婚礼的猎人俱乐部百米之外就是伊拉克军事情报总局,一群士兵仍在清理前不久惨遭轰炸的主建筑。
防空武器昂首向天,一面伊拉克四色国旗在夜空招展,旗上的手写体阿文赫然分明:“安拉最伟大。”
第12节埃及地震亲历记
#page{position:absolute; z…index:0; left:0px; top:0px}ntent{font: 11pt/16pt 〃宋体〃}第12节埃及地震亲历记护身符不翼而飞 1992年10月12日午后,我一觉醒来,中东烈日正透过百叶窗直射到我腿上,干枯的汗毛在侧逆光下金光闪闪,贴满止疼膏的膑骨火辣辣的疼、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突然发现脖子上的护身符不翼而飞。
我的护身符绝非价值连城的钻石、翡翠、和氏壁,而是一枚仅伍分硬币大孝刻有六字真言的铜观音。可这枚祖传的铜观音陪我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抓大熊猫、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从天安门到巴格达。洪水、大火、动乱、战争……铜观音保佑我走遍世界。
我将护身符的失踪看做是某种危险将至的征兆,就像海湾战争在特拉维夫挨“飞毛腿”前,尼康相机包的背带莫名其妙地断了三次。
不祥的预感像只庞大的阿拉斯加灰熊,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莫名的恐惧紧紧纠缠着我。
尤其令我不安的是我放在冲扩店的四卷负片,竞不可思议地卡在冲扩机里。尽管店主哈利德一再以安拉的名义赌咒发誓“枯鲁塔麻姆”(阿语:一切都好),可我从中午到现在连跑四趟还是没有结果。
下午2:40,我开着大吉普第五次去冲扩店,店老板哈利德干脆躲了出去,仅留下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伙计敷衍我,气得我直骂娘,发誓再也不来这家鬼店。
我离开冲扩店,开上大吉普回分社,看看左腕上的潜水表已是下午3:05。我爬到吉普后座上将昨天吃剩的罐头。
面包塞进一只大塑料袋,又取出汽车收音机中的盒带,准备回房间伴着瓦格纳辉煌的旋律吃我的午饭,继续读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我左手提着塑料袋爬上楼,钻进洗手间准备把憋了半天的一泡尿先解决掉。就在这时,一阵闷雷般的轰鸣由远而近,大地上下震颤,继而左右摇晃,我根本无法把尿撒进尿池里。
我用手撑住墙壁,抬起左腕看了一眼潜水表:下午3:09。
她震持续了一分钟
整个震颤过程持续了一分钟。在这漫长的一分钟里,先是有人大呼小叫“地震”,继而是五音错位的喊夫唤妻。
我根本不信真是地震,因为我脑子里只有“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我随着慌张的人流往外跑,迎面撞上一个脸色煞白带着哭腔找丈夫的女人,看着她的失魂落魄,我猛然想起我还是个男人。我逆着人流返回楼上,抄起床头的多姆克摄影包,又从冰箱中摸出五个柯达胶卷和一卷绷带,拎着落满灰尘的钢盔直扑停在车库的大吉普。此时,我就像一只全神贯注于捕鼠的大公猫,周围的一切似乎已不再存在。我真担心持续的震颤会把我的大吉普砸在楼里,由于太紧张,连打了两次火才发动着引擎。弄不清是大地的颤抖还是六缸吉普4500毫升发动机的轰鸣,我耳畔回荡着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我尽力稳定情绪将车倒到街心,大吉普咆哮着迎着惊惶失措的人流霸道地横在街心。我摇下玻璃朝外面大喊:“谁跟我走?”我称之为六哥的分社办公室主任应声上了车。我的铁哥儿们王波揪着自己的小背心的背带、趿拉着拖鞋可怜巴巴地问我:“穿这个行吧?”我没等他完全爬进来就抬开离合器,大吉普吼叫着冲开人群。王波趴在我耳旁大喊:“咱们去哪儿?”“哪儿惨去哪儿!”我回答得咬牙切齿。宽广的阿盟大街成了抱头鼠窜者的避难所,可我无心在此恋战。我知道老开罗的旧房区肯定比这儿出戏,茵芭芭和舒伯拉区不砸死人才怪。可眼前一些胆小的可怜虫弃车而逃,把道路塞得死死的,好在我的大吉普四轮驱动可以蹿上爬下越野而行。“七·二六”大街一幢五层楼震塌的一角堵死了干线,我不得不右转弯沿着濒尼罗河的科尼奇大道向南走。再往前是政府新闻部,我让王波下车去新闻部打听一下震中在哪里、震级多少。我则找路口掉头,将大吉普靠在马路牙子上追拍魂不附体的人群。
六哥和王波四只拖鞋僻啪小跑着奔回来,争先恐后地大喊:“新闻部里的人全躲地震去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埃及人失魂落魄地一把拽住脖子上挂满尼康相机的我,其神态酷似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八路军的大春哥。原来新闻部后面就塌了三座小楼,他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跟在这老兄身后亦步亦趋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终于来到一堆破烂不堪的废墟前,可房主说什么也不许拍照。
再向前就是舒伯拉区,根据多年经验,我紧盯着一辆救护车的屁股,轻而易举地到了现常这里的房屋至少已有80年历史,自然惨象环生。紧挨着我的大吉普,一家人正颤巍巍地竖起大木梯把还困在二楼的孩子接到地面。数不清的灾民在破砖烂瓦中挑拣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哪儿是震中,谁也不清楚地震有几级。一位安莎社记者告诉我震中“应该在地中海底”,我笑骂道:“应该是维苏咸火山!”
独自一人钻进新华社中东分社大楼的暗室里,冲胶卷时我才突然感到以往从未有过的恐惧,“死”仿佛近在飓尺。
此时,我真盼望自己能有个儿子可以延续我的生命,我痛苦地感到我已经老了,以往的胆识已一扫而光,我真怀疑当初在巴格达、特拉维夫挨炸时我是否邪魔附体。为战胜自己的懦弱,我将收录机的音量开关扭至极限,让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驱散冥冥之中的恐惧,赶走死神的黑翼。
照片很快制作完毕,待写完文字说明才知道整个开罗与外界的电话联络全部中断,任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入夜,我开着大吉普奔赴开罗灾情最重的海利波利斯区,这里一幢有72套房间的14层巨厦被夷为平地。我看见路透社摄影记者阿莱、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法新社摄影记者阿尔多等人嘴上缠着白绷带,迎着刺鼻的血腥味往前冲,这是一群十足的捉老鼠的大公猫。我的老朋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断腿巴利也混迹其间,拖着他那条在贝鲁特打断的右腿一个趔趄栽下来,大脑袋正撞在我肚子上。
我用力挽住巴利的胳膊,同时尽量保持住自己的平衡。巴利一面喊了声:“谢了,唐!”一面挣扎着继续往废墟上爬,越过他倾斜的脊背,我看见他那大眼睛的阿拉伯女人正使出吃奶的力气,用肩膀顶着巴利的右腿。
寻找震中
午夜两点,我将大吉普藏在清真寺旁的一块空地上,偷偷摸摸地钻回楼里睡觉。我绝非有意以武力试探社长不许上楼的命令的权威性,实在是我已太累,必须脱光衣服“真正地”睡一觉,因为我已打定主意,明早一定要第一个赶到那子虚乌有的震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禁不住重温1989年山西地震的旧梦,那回我以一辆“大发”昼夜兼程2000公里,我的传真照片不仅占领了《人民日报》头版,还被美联、路透、法新、共同社们买去。光荣与梦想俱成历史,这里是开罗,地震仍在发生。紧张工作之余,我体会着小猫晒太阳才有的温暖,恍惚睡去。
当我被闹钟吵醒时已是10月13日凌晨6:00。我邀阿文记者老杨与我同行,目标是100公里外卡伦湖畔子虚乌有的那托拉尼沙山,据埃及《金字塔报》透露,那一带可能就是震中。驱车出开罗沿着直通法尤姆的沙漠路狂奔,一种中说不出的惬意溢于心头。
我开的这辆91年款丰田大吉普曾随我二闯以色列,半年前以色列国防军围堵了我几十公里才在加沙城北将我拿获。法新社、路透社们把闯边界的我描写成“驾飞车的唐”,以色列国防军干脆叫我“飞人”。开快车成性的我按报上讲的经纬度迅速赶到开罗西南指定的坐标位置。可这里既无加托拉尼沙山更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就连在这片沙漠中修路的筑路队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和老杨边走边问,一直围着卡伦湖转了大半圈,才在沙克舒克村口碰上一个自称知道震中加托拉尼沙山的人。
这个头裹绷带的家伙声称震中加托拉尼沙山还得再向沙漠纵深开70公里,可我的大吉普的贮油只能再坚持50公里。
看着这老哥目无定睛的神情,我开始怀疑他那缠着绷带的下巴到底是房梁砸的,还是挨了左勾拳。
按理说小村沙克舒克是离震中最近的永久居民点,可灾情并不比开罗重多少。穿黑袍蒙黑纱的阿拉伯妇女若无其事,各自在破败不堪的屋檐下忙着家务。村旁的卡伦湖上帆影点点,捕鱼如常。
离沙克舒克村继续前进20公里,便到了北非古城法尤姆。我们的大吉普纵穿最繁华的穆罕默德大街,发现有五六处楼房受损,军队正在封锁现场,组织抢险。但总体看来灾情远远小于开罗。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已中断对中国的出访回国,当天就视察了救灾现常这次“埃及历史上最强烈的地震”至少已造成500人死亡、4500人受伤。仅开罗金字塔医院就处理了1000多名伤员,医院门口数十名痛失亲人的阿拉伯妇女哭嚎之声震天。
下场地震推迟到五点开演
开罗海利波利斯那座崩塌成一堆瓦砾的14层公寓楼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核心。由德国红十字会派来的寻人犬营救队正在仔细搜寻,每隔个把钟头就刨出一个垂死或已被水泥预制板砸扁的居民。阿拉伯人严禁给死人拍照,数十位义务人员高扯白布专门阻挡电视和摄影记者的镜头。炎炎烈日下,口干舌燥的德国寻人犬累得体力不支。戴眼镜的寻人犬饲养员克劳布小姐与她的爱犬共用一个水壶喝水。
我没见过1940年的考文垂和1941年的珍珠港,可我亲历的特拉维夫和巴格达的战争废墟都没有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