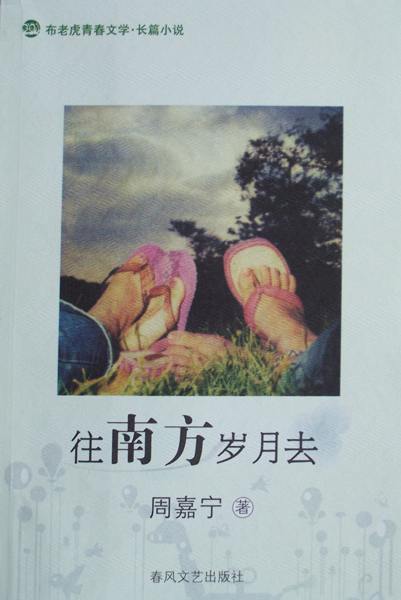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里闹起来了,大发脾气说现在要跟夫人对质。”她以为自己在耳语,其实音量已经引得坐在两旁的妇人们侧目。令秧尴尬地站起来,同唐璞夫人告了辞,领着小丫鬟动身了。她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孩子也颠三倒四说不出个所以然。最终还是回去的路上,侯武简明扼要地回明了事情——得亏是他亲自赶了车来接——原来就在刚刚,几个着朝服的宦官来到了唐家,下了马便不由分说地占据了中堂要宣圣旨。川哥儿自然急急地换了衣裳出来跪着,一起不得不跟出来的,自然还有杨琛。圣旨究竟说了什么,侯武也不甚明了,当时他跪在离中堂老远的地方,不过是称赞了唐家收留杨琛有功之类的话。领头的公公还留话说三日后清早,便有车来接杨琛回京,还说当日请夫人务必在府里候着,因为皇上赏赐给夫人的东西那日就到徽州了。侯武用力地加了一句:“这个我是绝对没有听岔,那公公真的说了皇上有赏给夫人,只不过他们一行人快马加鞭地先来给杨公公一个安心,御赐的赏品却不能在路上颠簸唯恐弄脏弄坏了。”
令秧觉得所有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她急急地问道:“皇上是怎么知道我的?”几乎是同时,小丫鬟困惑地问道:“如此说来不是天大的好事么,川少爷还要生哪门子的气?”侯武为难道:“这个,我可说不好。”一句话,倒是把两人的问题都回答了。
川少爷脸色铁青地坐在令秧房里,小如胆战心惊地倒了茶放桌上,他手一挥杯子就跌下去摔得粉碎。小如静悄悄地躲在门口,也不敢过去扫地,一转头看见令秧终于不紧不慢地款款走在回廊上,立即念了声佛:“阿弥陀佛,夫人可算是回来了。”川少爷听着了,立即握紧了拳头站起身,在室内狂躁地来回踱着。
令秧跨进门槛,淡淡地吩咐小如道:“出去吧,到杨公公那里问问,他想吃什么,然后让厨房去做。”
川少爷听了这话,立即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小如咬咬嘴唇慌忙地逃走了,令秧慢慢地掩上了身后的门,转身笑道:“怎么这川少爷越大倒越像是活回去了,连个茶杯都端不稳。”
川少爷冷笑道:“我来就是想请教夫人,现如今这个家里做主的究竟是哪个?老爷刚过世那阵子倒也罢了,我还未及弱冠;可如今,我就把话索性跟夫人挑明了,这个府里在外头应酬官府的是我,在族中顶门立户的也是我,我敬着夫人为府中主母,也纯是看着老爷的面子。家内的大小事务夫人做主我不拦着,已经足够尊重了;夫人若是在外面给我难堪,那便是僭越,休怪我说话难听……”
令秧轻轻地打断他:“我糊涂了,怎么皇上的圣旨到了给咱们赏赐,反倒是我做错了不成?杨公公是谢先生在田地里发现的,莫说是朝廷的宦官,哪怕是个贩夫走卒,难道能见死不救?我没告诉你也是因着你去书院了不在家,你如何连点儿道理也不知道了呢。”
川少爷的脸慢慢地逼近了她的,那么清俊的面庞,也可以被激愤撕扯到狰狞的地步:“我忘了告诉夫人,休要再提那个谢舜珲。一个也算是读过圣贤书的男人,在这种时候给阉人帮忙,真是丢尽了天下读书人的颜面!这里究竟是唐家的地方还是谢家的地方?他自甘堕落也便罢了,牵累得所有人都知道是我的府上窝藏了那阉人,我如何回书院里去交待众人?”
“既是读过圣贤书的。”令秧的声音里毫无惧怕,“便该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谢先生当日如何待你不用再提了,单理论这件事情,皇上的赏赐都来了咱们家,这难道也是有错的?”
“妇人之见,跟你讲不清楚!”川少爷暴躁地挥了挥手,险些抽到令秧脸颊上,“看看天下读书人,哪个不骂阉党?即便是圣上也知道读书人跟阉人水火不容,即便是因为阉人得罪了圣上,也只是一时,子孙后世也会记得你做了读书人该做的事;即便圣上一时气急了砍了你的脑袋,过一阵子照样后悔给你立碑……你们这些见识短浅的妇人如何能懂得这个?靠着谄媚阉人换来这一星半点的小利,脏污的是我在外头的名节!你以为天底下只有寡妇才在乎名节么?”
“话虽如此说。”令秧觉得自己被伤害了,“赶明儿杨公公走的时候,你不照样地点头作揖,你敢当着他的面说一句‘阉人’么,以前还觉得谢先生说话离经叛道,现如今才知道……”
“休要再提他!”川少爷快要吼了起来,“我不会准他谢舜珲再踏入我家门半步!溦姐儿的婚事我明日便去退了,我不知道他究竟灌过什么迷魂汤给夫人,总之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你敢!”令秧真的被激怒了,可惜她委实不大会骂人。
“我如何不敢!”
“你毁了我女儿的婚事,老爷还在天上看着呢!”令秧混乱地喊道,头脑一阵发晕。
“老爷在天有灵必定恨不得溺死她。”川少爷突然间冷静了下来,“她是你和我的女儿,你打量老爷真的会不知道?”
这是令秧第一次从人嘴里听见这个,赤裸裸的真实,她脑袋里像是飞进了成百上千只蜜蜂,指尖也像是发麻了,在袖子底下冰冷地颤抖着,就连那只残臂此刻也像是又有了知觉。
她扬起手想打他,可就在此时,门开了——小如那丫头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拦着呢,是她把小如打发到厨房去的,她真是该死,她木然地望着门边脸色惨白的兰馨。川少爷立即换上了一副镇定的语气:“你跑来做什么,回房去。”
兰馨的身子微微晃了一下,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令秧,因为失了血色,一张脸倒益发显得粉雕玉砌。她微微一笑:“夫人别忧心,兰馨什么都没听见。兰馨不过是担心夫人这边有口角,所以才来看看的。没事的话,我回去了。”
那天夜里,兰馨把自己吊死在了卧房的房梁上。她的丫鬟直到黎明时分才发现,她早已冰凉。
那日,杨琛的早饭比平时来得迟了些。令秧拎着食盒进来的时候,居然还宁静地一笑:“杨公公,不好意思,今日府里出了点子事情。”她发现他正用力地看着她,便安静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满脸的悲悯:“夫人这就太客气了,我知道府上出了大事。饶是这样还要劳烦夫人,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令秧已经把食盒放在桌上,一层一层地取下来,刚要去取第三层的时候,突然哭了。杨琛就静静站在桌子的另一头,等了好久,不理会所有的饭菜都已冷透,看着她哭。
令秧不记得,自己已经多久没哭过了。
第十二章
兰馨的“七七”过完以后,川少爷便离开了家。
走的时候头也没回。兰馨在世的时候,特别是最后几年,他从未正眼看过她,所以出殡的时候,便有人议论纷纷,奇怪为何川少爷哭得如此肝肠寸断——兰馨的娘家人,原打算兴师问罪的——他们不相信兰馨只是因为一点口角才一时想不开的,可后来硬是被川少爷心魂俱裂的眼泪浇熄了所有的气焰。再加上蕙娘把丧事料理得风光隆重,对娘家来吊丧的一众主仆都照顾得非常周到,后来,兰馨的哥哥便也长叹一声,叹息自己妹子秉性素来刚烈,再加上这么多年未能诞下一男半女,常年心思郁结,脸上一时挂不住做了傻事也是有的。三姑娘却因为身孕,没来兰馨的葬礼。其实令秧知道,三姑娘和兰馨不同,她心里最清楚不过,什么才是要紧的事情。
众人只看得到,原本就不多话的川少爷,自从少奶奶过世以后,更加寡言少语,再加上消瘦了很多,人看起来也阴沉了。当然了,这种阴沉在外面的女人们眼中,自然又另有一番味道。也许他直到此时才算明白,兰馨对于他来说,并非可有可无。但是令秧已经无从知道答案了,因为直到川少爷离家,他们都再未交谈过一句。
川少爷这次走得更远,出了徽州,到了常州府。常州府的无锡县,有一位名叫顾宪成的先生,原本也是京官,被革职为民,返乡便办起了一所“东林书院”,这东林书院名播千里,很多有学问,有见识,心忧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那里针砭时弊指点江山——莫说是无锡知县或常州知府,就是在京城朝中,也有支持东林学派的重臣。川少爷觉得在那里也能寻到一个男人该有的事业。至少在那里,有更多的人跟着他一起骂阉人,并且骂得更有才情。
这些都是谢舜珲解释给令秧听的。川少爷去参加“东林大会”,其实也是谢舜珲的建议,依照谢舜珲的眼光,民间这些大大小小的书院学派里,只有东林书院最有成大气候的可能。兰馨一去,川少爷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忘记了,自己说过再也不许谢舜珲踏入家门的话。反倒是在一个深夜里敲开谢舜珲的房门,如很多年前那样,无助惶惑地喊了一句:“谢先生,这个家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待下去了。”
川少爷走了,唐家大宅却没有显得很空。大家照旧是热热闹闹地穿梭其间,这让令秧心里隐隐地有种“惨胜”的错觉。原先贴身伺候川少爷和兰馨的丫鬟都没有遣散,一个大些的调去绣楼陪着溦姐儿,两个小的调来了令秧房里。令秧打量着把这两个孩子调教几年,等当归哥儿娶媳妇儿的时候,正好送去伺候新来的少奶奶。众人都说夫人是真心疼爱当归哥儿,事无巨细都打算得这么仔细。令秧心里隐隐地希望,云巧这个时候能来跟她说上哪怕一句暖和些的话,当然她自己也知道这是奢望。如今在这宅子里,若想看见云巧,只怕必须赶着初一十五的大清早,能看见她带着丫鬟出现在院子里——那是她去庙里进香的日子,当然了,她也不会跟宅子里的任何人交谈半句。
令秧最不喜欢初冬这个时节,室外的阴冷虽不剧烈,可是丝丝入扣,即便是着了厚裙子棉比甲,脚心里还像是踩着一团湿淋淋的冰冷的布。她吩咐小如在房里多生几个火盆,待久了却又觉得热,炭气弥漫,嘴唇上似乎从早到晚都结着一层硬壳子。怕是只有在谢舜珲造访的时候,才有一点鼓舞她的欢欣。她清亮地吩咐丫鬟们筛完了酒定要好好烫一下,窗外零星地飘着冷雨,雨滴里隐隐掺着些硬的冰屑。
“我知道云巧现在一定恨死了我。”她落寞地叹气,“你是没看见,她整日过得像个姑子,我真没料到,仅仅因为恨我,她便连‘活着’都好像觉得没趣儿。”
谢舜珲皱皱眉头道:“夫人千万别这么想。一个人若是觉得没了生趣,多半是厌烦了整个人世间,这可不是夫人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办到的。”
令秧困惑地托住了腮:“这话我便真是不懂了,这人间即便再凄清,也还是有热闹的时候啊。”
谢舜珲温暖地笑了:“夫人可不是凡人,若世人都像夫人似的,这天下可就断断不能太平了。”
“你一日不打趣我几句,你便浑身难受是不是。”令秧气急败坏地白了一眼。
那段日子里,令秧是幸福的。唐家大宅的里里外外,有蕙娘在挥斥方遒,似乎一切都按着本来的规则井井有条地运转,她只有一个任务,便是扮好那个如同府里招牌的“节妇”,这件事她擅长并且驾轻就熟;溦姐儿的病好了大半,虽说见了她仍旧是淡淡的,可是在绣楼上跟自己的丫鬟倒是有说有笑;当归哥儿也长成一个结实的少年了,这孩子人高马大,憨厚,心眼儿实在,他算是心如死灰的云巧眼里唯一一道光线,只可惜这孩子完全不能领会大人之间那些微妙的紧张,跟令秧日益亲近着,有了什么他自己也晓得比较过分的要求,去夫人房里撒个娇便是——蕙娘跟令秧商量过,也是时候定下来当归的婚事了,可令秧觉得,不如等到次年春天,也许川少爷明年就中了进士,这样当归可以挑选的姑娘便更是不同,蕙娘还笑,说夫人真是深谋远虑;因为川少爷离得很远,那种时刻隐隐威胁着她的恐惧便放宽了,她终于可以放心地做一个宅心仁厚的“继母”,入冬以后便着人打点着厚衣服和吃的用的,命侯武找到合适的商户带过去。
隔三差五地,谢舜珲还是会来。虽说如今已经没有了和哥儿切磋学问的幌子,不过府里的人也早已拿他和令秧的友谊当成了最自然的事情。令秧给他烫上一壶酒,他们闲话家常,互相嘲讽,若是谢舜珲太过刻薄,令秧恼了便拂袖而去——不过撑不了多久便又忘了。偶尔她也会跟谢舜珲念叨两句,也不知杨公公许诺过会尽力帮忙,究竟还算数不算——不过,都无所谓,她不再觉得煎熬,岁月从此便会这样若无其事地滑落下去,到四十岁,到五十岁,到死。
六公的死讯是在腊月初的时候传来的。其实六公缠绵病榻已有大半年的光景,所以众人看到唐璞骑着白马,带着一众着丧服骑黑马的小厮们前来叩门报丧的时候,也都不觉得意外。都说六公刚刚咽气的时候正是天色微明,六公的小儿子拿着六公的一件衣裳,爬到正房南边的屋顶上大喊着招魂,因为周遭寂静,这喊声凄厉地传了好远,惊飞了远处树上的一群乌鸦,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沉寂了很久的老夫人突然间从床上坐了起来,像是因着打了个巨大的寒战才被弹起来的——搞得看守的婆子们异常紧张地屏息看着她,就像一群猎人埋伏着观察一只豹子,犹豫着,不知是不是又到了必须上去绑她的时候。
唐璞是六公的侄子,在六公繁冗隆重的丧仪里,理所当然地成了“护丧”,负责监督跟打理丧仪的所有往来环节。报丧的队伍离开的时候,蕙娘手按在胸口笑道:“别人家报丧最多来两三个人,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浩浩荡荡的排场,不愧是九叔。”转过头去急急地寻侯武去派人送奠仪了。
人死之后三天,便是大殓,尸体入棺的日子。六公家里请风水先生看过了,入棺之后,六公须得在灵堂里停放七七四十九天,正月下旬的时候才可入土。大殓次日,族中子弟乃至女眷悉数到场举哀,按照“五服”的规矩穿戴好各人该穿的丧服。唐璞请来了和尚道士,要做足四十九天的法事超度亡魂。在这四十九天里,族中各家须得出一两个人守着灵堂,每日朝夕各哭奠一次。这委实是个苦差事,族中各家被推出去的人行“朝夕哭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