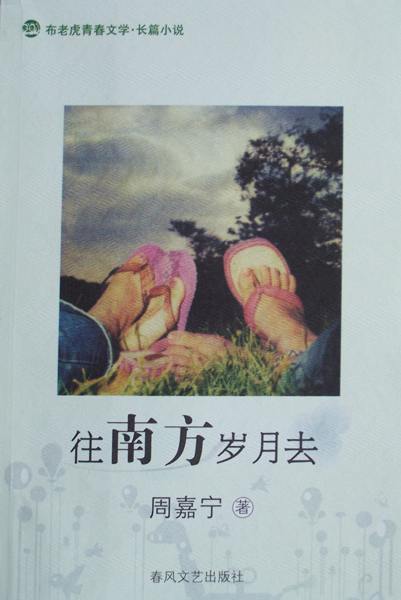南方有令秧-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喝水撑不住的——我老婆子也没法子,长老们吩咐过了,只准我给夫人水,不准给吃的。”
片刻之后,令秧听见了关门的声音,她知道此时屋里只剩下了她自己,和那碗毒药。她怕,可还是忍不住睁开了眼睛——毕竟,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毒药是什么样的。捧起那杯子的时候胳膊都在打战,但是她还没有意识到那其实是因为饥饿。不然——先稍微用舌尖舔一下呢——她还是把那杯子丢回到炕桌上,还以为它会被打翻或者直接摔碎,但是它只是危险地颤了颤,像是转了半圈,就立住了。她从小就怕死了喝药,这跟那药究竟是为了治病还是为了死根本没关系。手抖得太厉害,洒出来的一点点弄湿了她胸前的衣裳,若是让嫂子看到了准又要数落的,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自然而然地想起嫂子了。一夜之间,成为唐家夫人的那段日子似乎已经成了一场梦,她的心魂又回到了童年去。
死就死吧。既然这么多人需要她死——那可能真的像门婆子说的,不是坏事。虽然说她若真的守到五十岁,也有牌坊可拿——但明摆着的,长老们不相信,也等不及。一具新寡的,十六岁的女尸换来的牌坊更快,也更可靠些。到了阴间,能看见娘,还能看见唐简——糟了,娘认不得唐简长什么样子,他们如何能够聚在一起,迎接令秧过来呢?令秧像是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在这世上,她最亲的两个亲人都已经走了,可是他们彼此还形同陌路。令秧并未期盼过会有人来救她,因为她从不觉得自己能有那种好运气。唐家大宅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有每个人要做的事情,老夫人只消隔几日兴师动众地犯疯病,宅子里的岁月就没什么两样,蕙娘继续日理万机地管家,厨娘年复一年地记清每排坛子里究竟装了什么,哥儿要等着迎娶新媳妇,云巧的孩子一旦出生她就有了偿不完的债——可能,唯一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便是她这个没了老爷,并且什么都不会的夫人。就像是筷子一样,哪怕是象牙雕出来的又镶了金边和宝石的筷子,其中一根丢了,另一根又能怎么样呢?若是她成为了一道牌坊,就不同了——她有了恰当的去处,所有的人都会在恰当的时候想起她。
有道光照了进来。她不得不抬起胳膊,用袖子遮挡住眼睛。发髻松垮了好多,软塌塌地堆在脖子那里,几缕散碎的发丝沿着脸庞滑出来,脸上的皮肤不知为何紧得发痛,就好像躯壳马上就要裂开让魂魄出窍。她仰起头,注视着光芒的来源。门婆子站在门槛里面,垂手侍立。院子里是唐璞和那几个随从。“夫人。”门婆子不疾不徐地说,“长老们马上就到,是时候去祠堂了。”
令秧微微一笑,端起面前那碗水,一饮而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空碗捧在胸前,轻声道:“知道了。”
门婆子走到卧榻边上:“我来扶着夫人。”令秧的右手轻轻搭在门婆子的手腕上:“我不敢喝。你来帮我一把?”门婆子摇头道:“这种事,除却夫人自己,谁都插不得手。”令秧的笑容突然间有了一丝慵懒:“灌我喝下就好,谁还能为难你呢?”门婆子弯下腰,摆正了令秧的鞋:“夫人若是实在下不去手,也别为难自己。凡事都讲个机缘,夫人说对不对。”
多年以后,当令秧已经成了整个休宁,甚至是整个徽州的传奇,唐璞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三月的清晨。她一瘸一拐地停在他面前,一身缟素,衣襟上留着毒药的污渍,粉黛未施,眼睛不知何故明亮得像是含泪。昨天把她带来的时候,她还不过是个只能算得上清秀的普通女人而已。可是现在,有一丛翠竹静悄悄从她身后生出来。发髻重新盘过了,不过盘得牵强。她宁静地垂下眼帘,甚至带着微笑,对唐璞道了个万福。屈膝的瞬间她的身子果然重重地趔趄了一下,她也还是宁静地任凭自己出丑——唐璞奇怪,自己为何会如此想要伸出手去扶她一把,又为何如此恐惧自己的这个念头。他清早出门的时候,接过他的小妾递过来的茶盅,还轻描淡写地抱怨过,也不知这个妇人能不能知晓进退,早些了断了自己,也好快些结束他这桩差事——毕竟谁愿意白天黑夜地守在祠堂里看这些长老的脸色行事呢。
可是此刻,一切都不同了。令秧的眉头始终顺从地垂着,眼睛却停在他已经往前稍稍凑了几寸却马上收回的右臂上。她柔声道:“有劳九叔。”唐璞心里长叹了一声:人们常说的老话有些道理的。若是让这妇人一直活下去,她怎么可能不变成个淫妇。
他却实在说不清,为何,当他再一次在这妇人面前打开那本记载节妇的册子,开始念的时候,悄悄从散发着一股霉味的纸张后面看了看她的脸。她和前一晚一样,跪着,眼神清爽地凝视着那些林立的牌位——今日长老们决定换个地方,挪到了唐氏宗族的女祠。这里供奉的,都是整个家族几百年来恭顺贤德的女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很快也会加入她们——并且成为她们的荣耀。
他诵读的声音不知不觉放缓了,有了一点琅琅的韵律。他甚至有意识地跳过了一些过于残忍的例子——比方说,有个女人,为了不改嫁,拿银簪捅穿了自己的喉咙,生生挣扎了一天一夜才死;还比方说,有个女人,在马上就要临盆的时候丈夫突然落水溺亡,她在守灵的夜里撞了棺材,脑浆迸裂,人却没有马上断气,却在这撞击中惊了胎气,她死的时候婴儿也死了——婴儿的脑袋已经出来,身子还在她肚子里;还有个女人自己跳进了烧着开水的大锅里,人们把她捞上来,救活了她,从此她带着一个怪物一般的躯壳活着,她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节妇,殉夫未死,却也拿到了牌坊……
唐璞跳过了所有这些记载,他只把那些轻描淡写的“自缢而亡”“溺水而亡”之类的读给她听。不过他不知道,令秧其实早就听不见他的声音了。她清楚有个声音在持续着,可是就像知道雨水滴落在屋檐上而已。她的腰支撑不住了,不得不用胳膊撑着蒲团,她觉得自己像个木偶,若不是有提线抻着,四肢早已散架。门婆子时不时会走进来,为长老们添茶。终于,也靠近她,在她身旁的地面上跪下,擎着一只水碗,喂她喝下去,似乎门婆子知道她的胳膊已经抬不起来。周遭突如其来的寂静刺进她的耳朵里,她扬起头,静静地看着六公的眼睛。
“又给你念了两个时辰了,唐王氏。”六公的嗓门比昨晚小些,更家常了点,大约也觉得这戏没那么好看了,“你明白了点儿什么没有?”
“我依长老们的意思。”令秧心无城府地笑笑。长老们面面相觑,神色惊喜,十一公道:“这话可就岔了,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天道。”
“我死就是了。”令秧的笑意更深,“我夫君走了,我也该跟着,长老们满意了吗?”
“天佑我唐氏一门,难得有唐王氏深明大义。”六公突然间声若洪钟,祠堂里所有坐着的老人们都跟着笑了,好像看戏的时候心照不宣地知道什么地方有个好。
“只是六公,那毒药,我实在喝不下。我一个妇道人家,胆子太小。我上吊行不行?”唐璞默默地合上那本册子,垂手侍立到一边去,经过令秧的时候,他的腿极为小心地一闪,怕碰到她。
“也好。”六公向唐璞道,“马上叫你的人去准备点白绫过来,要上好的。”
“依我看……”长老中那个从未开口说话的老人放下了茶杯,跟其他长老比,他面色上泛着奇怪的红润,“在祠堂自缢,不妥,打扰了祖宗们的清静不说,祠堂这地方,可是一点秽气都见不得的。”
“这容易。”十一公摆摆手,“叫人押着她回她们家里不就得了。在自己府里自缢,说出去也没有不妥的地方。”
“只怕又生枝节。”
“这话糊涂,谁又敢生什么枝节?哪个不知道这是整个宗族的头等大事,我倒借他个胆子……”十一公的胡子伴随着说话,一飘一飘的。
线断了。祠堂的屋顶在不停地转圈,就像小时候哥哥给她做的那个陀螺。眼前的一切隐匿于黑暗之前,她觉得自己能稍微看清的,是唐璞俯下来的脸。然后,她真以为自己用不着上吊,就已经死了。所以她不知道,门婆子冲上来掐了一阵她的人中,未果,又搭着手腕把了她的脉。
门婆子不慌不忙地对六公说:“老身略略通得一点岐黄之术,唐夫人的脉象,怕是喜脉。不敢乱说,还请诸位长老赶紧找个大夫来给瞧瞧。”
祠堂里顿时嘈杂了起来,似乎没人再在乎打扰到祖宗。唐璞微微地攥住了拳头,也许她用不着去死了——正因为这个,他胸口才划过去一阵说不清的疼。
唐家大宅里,不少人都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
云巧坐在蕙娘的房间里,不肯走。“出了再大的事情,你现在都得去歇着。”蕙娘把这句话用软的、硬的、软硬兼施的语气讲了无数次,一点用也没有。不只是云巧,这几个人房里的丫鬟都静悄悄地站成一排,正好挡在蕙娘的屏风前面,没有丝毫要散的意思。蕙娘颓丧地把脸埋在十指尖尖的手掌中,重重地叹气:“你们都在这儿耗着也没有用,早就差了好几拨人去打探了,离祠堂还有好几丈远就被九叔的那班小厮拦了下来……”“我不信,就连她的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罢呦。”蕙娘无奈地摊手,“真听到什么动静,哪有不告诉你的道理?”“那就让他们一直在远处守着!”云巧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你不是说他们要逼着她断指立誓吗——她总不能连叫喊声都没有吧——可是若真的断指,哪用得了这么些时辰?别看她十六了,其实她根本就是个孩子她什么也不懂……”云巧放声大哭了起来,蝉鹃也即刻跟着抹起了眼泪。
“这算什么意思!”蕙娘气恼地站起身,椅子在她身后“轰轰”地划拉着地面,“深更半夜的,你是不是非要吵醒了老夫人和哥儿才算干净?断指也是我过去听人家说的,谁能真的亲眼看见……”管家娘子在此时推开了房门:“蕙姨娘,小厮们回来,听说祠堂里散了,六公十一公他们的轿子都走了,只是没有咱们夫人的信儿,那个跟着的小丫头也不知被支使到哪儿去了。夫人好像是就在祠堂的后院歇了,族里看祠堂的那对老夫妇伺候着她,祠堂里彻夜都还有九叔的人轮班守着,咱们靠近不得。”
蕙娘招呼管家娘子在圆桌边上坐了,云巧急急地招呼蝉鹃,扶她起身离开圆桌,坐到旁边的矮凳上去。却立刻被蕙娘拦住:“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些虚礼。若真的丁是丁卯是卯地论起来,她是伺候过老夫人的人,她坐下的时候我都该站着。”管家娘子也劝道:“巧姨娘眼下可千万哭不得,不能伤了胎气。依我看,今晚夫人不会有什么事情,明天天一亮咱们家的小厮也还是会过去打探着。不过九叔家的那些人向来跋扈——”“使些银子罢了,倒没什么。”蕙娘苦笑道,“我最心慌的,就是不知道这班长老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怕就算是打探到了消息,咱们也来不及想主意……宗族里的事儿,官府都能躲就躲,我怕咱们……”眼看着云巧又要哭,管家娘子硬硬地给蕙娘递眼色:“我倒觉得,谢先生像是个有主意的,他一向起得早,明天,我打发人早点去把早饭给他送过去。”“正是这话。”蕙娘会意地点头道,“我一早就去跟他商量商量,看他有没有什么法子。”
次日清晨,跟着令秧去往祠堂的小丫鬟被一众唐府的小厮骑马带了回来,他们是在去往祠堂的半路上遇到了她。蕙娘和众人都在哥儿的书房里。一见着蕙娘,小丫鬟便跪下哭道:“蕙姨娘,可了不得了,我一整夜被他们关在祠堂的柴房里,根本连夫人的面都见不着。是一大早,那个看祠堂的老婆子,有一只眼睛有毛病的……”蕙娘急得叱道:“你这孩子就不知道拣紧要的说么,都火烧眉毛了还管人家的眼睛!”“是她偷偷放我走,嘱咐我来给咱们府里报信的。”小丫鬟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像是从账簿上扯下来的纸,“那老婆子说,把这个交给咱们府里管事的就好。”“一个看守祠堂的婆子,倒会写字?”蕙娘惊愕地挑起了眉毛。打开匆匆看完,却僵硬地跌坐在椅子里,都忘记了叫小丫鬟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云巧面如土色,甚至不敢正视蕙娘的脸。
蕙娘把那张纸交给她的丫鬟:“去给谢先生看看。”云巧此刻才想起来,谢先生一直安静沉默地站在回廊上。
“没事。”蕙娘用力地笑笑,朝向管家娘子道,“叫你当家的马上去把罗大夫请来。告诉罗大夫人命关天。再去账房支银子,有多少拿多少过来。”
“蕙姨娘。”管家娘子面露难色,“老爷的丧事刚完,现在要银子,只怕都得动厨房买菜的钱了。”
“不怕。我房里还有体己的首饰。”蕙娘笑笑,“顾不得这些了,救命要紧。等一下,你知不知道六公平日里都请哪个大夫?”
“这个得去问九叔身边的人。他们一准知道。”
“那就叫小厮们去打听,把跟六公熟的大夫和罗大夫一起请到咱们家。顺道把我的首饰押到当铺去,全是在京城的时候攒下的好东西,只怕还真值个六七十两。”
“要那么多?”管家娘子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么多,只怕人家大夫还不肯收呢。”蕙娘似笑非笑地看了云巧一眼,“咱们又不是叫人家来诊病,是求人家来撒谎的。”
“我横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云巧淡然地抿了抿嘴唇,“不过我就知道一样,若是大夫不肯收你的首饰,我跟我肚子里这个孽障,一块儿死在他们跟前。”
谢舜珲站在回廊上,背对着窗,注视着远处烟青色的天空。
“谢先生?”哥儿站在他身后,“蕙娘她们,究竟在商议什么?夫人到底被带走做什么呢?”
他转回头看着这十七岁的少年,头上依然纶着月白的方巾,白皙,清瘦,俊美,有一双大且漆黑的眼睛。谢舜珲知道自己答非所问:“这几天,怕是没心思想功课吧?不打紧的,咱们缓两天再念书。”
哥儿微笑的时候,眼神里却总有种动人的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