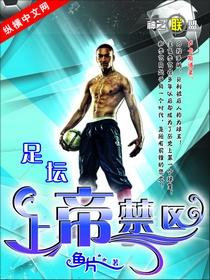08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显得烦躁不已,对自己的估计错在何处感到非常纳闷。他对哈特克说:“他们是怎么做到
的?如果我们这些曾经干过同样工作的教授们连他们(理论上)是怎么做到的都搞不懂,我
感到很丢脸。”德国人讨论了多种可能性,但一直到14号,事情才起了决定性的转变。
到了8月14号,海森堡终于意识到了正确的计算方法(也不是全部的),他在别的科学
家面前进行了一次讲授,并且大体上得到了相对正确的结果。他的结论是6。2厘米半径
16千克!而在他授课时,别的科学家对此表现出一无所知,他们的提问往往幼稚可笑。德
国人为他们的骄傲自大付出了最终的代价。
对此事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在1998年出版的《海森堡与纳粹原子弹计划》(Paul Rose)
和2000年出版的《希特勒的铀俱乐部》(Jeremy Bernstein)二书中找到非常详尽的资料。
大体上说,近几年来已经比较少有认真的历史学家对此事表示异议,至少在英语世界是如
此。
关于1941年海森堡和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也就是《哥本哈根》一剧中所探寻的那
个场景,我们也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关于这场会面的讨论是如此之多之热烈,以致玻
尔的家属提前10年(原定保密50年)公布了他的一些未寄出的信件,其中谈到了1941年的会
面(我们知道,玻尔生前几乎从不谈起这些),为的是不让人们再“误解它们的内容”。这
些信件于2002年2月6日在玻尔的官方网站(nbi。dk)上公布,引起一阵热潮,
使这个网站的日点击率从50左右猛涨至15000。
在这些首次被披露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玻尔对海森堡来访的态度。这些信件中主
要的一封是在玻尔拿到Robert Jungk的新书《比一千个太阳更明亮》之后准备寄给海森堡
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这本书赞扬了德国人在原子弹问题上表现出的科学道德(基于
对海森堡本人的采访!)。玻尔明确地说,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每一句谈话,他和妻子玛
格丽特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海森堡和魏扎克努力地试图说服玻尔他们,德国的最终胜利
不可避免,因此采取不合作态度是不明智的。玻尔说,海森堡谈到原子弹计划时,给他留
下的唯一感觉就是在海森堡的领导下,德国正在按部就班地完成一切。他强调说,他保持
沉默,不是海森堡后来宣称的因为对原子弹的可行性感到震惊,而是因为德国在致力于制
造原子弹!玻尔显然对海森堡的以及Jungk的书造成的误导感到不满。在别的信件中,他
也提到,海森堡等人对别的丹麦科学家解释说,他们对德国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因为德国
的胜利十分明显。玻尔似乎曾经多次想和海森堡私下谈一次,以澄清关于这段历史的误解
,但最终他的信件都没有发出,想必是思量再三,还是觉得恩恩怨怨就这样让它去吧。
这些文件可以在nbi。dk/NBA/papers/docs/cover。html找到。
容易理解,为什么多年后玻尔夫人再次看到海森堡和魏扎克时,愤怒地对旁人说:“
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不是一次友好的访问!”
这些文件也部分支持了海森堡的传记作者Cassidy在2000年的Physics Today杂志上的
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哥本哈根》一剧而写的)。Cassidy认为海森堡当年去哥本哈根是
为了说服玻尔德国占领欧洲并不是最坏的事(至少比苏联占领欧洲好),并希望玻尔运用他
的影响来说服盟国的科学家不要制造原子弹。
当然仍然有为海森堡辩护的人,主要代表是他的一个学生Klaus Gottstein,当年一
起同行的魏扎克也仍然认定,是玻尔犯了一个“可怕的记忆错误”。
不管事实怎样也好,海森堡的真实形象也许也就是一个普通人毫无准备地被卷入战
争岁月里去的普通德国人。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他对于纳粹的不认同态度有目共睹
,他或许也只是身不由己地做着一切战争年代无奈的事情。尽管历史学家的意见逐渐在达
成一致,但科学界的态度反而更趋于对他的同情。Rice大学的Duck和Texas大学的
Sudarshan说:“再伟大的人也只有10%的时候是伟大的……重要的只是他们曾经做出过原
创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贡献……所以海森堡在他的后半生是不是一个完人对我们来说不
重要,重要的是他创立了量子力学。”
在科学史上,海森堡的形象也许一直还将是那个在赫尔格兰岛日出时分为物理学带来
了黎明的大男孩吧?(终)
***********
贴图:惠勒的龙
Field Gilbert画,扫描自Niels Bohr: A Centenary Volume(Harvard 1985);p151
://://newbbs4。sina/groups/arts/history/upload/1073328470_3ff9b155080d
07c2000019ccdragon1。jpg
第九章 测量问题四
castor_v_pollux
吃一堑,长一智,我们总结一下教训。之所以前头会碰到“意识”这样的可怕东西,
关键在于我们无法准确地定义一个“观测者”!一个人和一台照相机之间有什么分别,大
家都说不清道不明,于是给“意识”乘隙而入。而把我们逼到不得不去定义什么是“观测
者”这一步的,则是那该死的“坍缩”。一个观测者使得波函数坍缩?这似乎就赋予了所
谓的观测者一种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享有某种超越基本物理定律的特权,可以
创造一些真正奇妙的事情出来。
真的,追本朔源,罪魁祸首就在暧昧的“波函数坍缩”那里了。这似乎像是哥本哈根
派的一个魔咒,至今仍然把我们陷在其中不得动弹,而物理学的未来也在它的诅咒下显得
一片黯淡。拿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科特?戈特弗雷德(Kurt Gottfried)的话来说,这个
“坍缩”就像是“一个美丽理论上的一道丑陋疤痕”,它云遮雾绕,似是而非,模糊不清
,每个人都各持己见,为此吵嚷不休。怎样在观测者和非观测者之间划定界限?薛定谔猫
的波函数是在我们打开箱子的那一刹那坍缩?还是它要等到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并在视网
膜上激起电脉冲信号?或者它还要再等一会儿,一直到这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的某处并最
终成为一种“精神活动”时才真正坍缩?如果我们在这上面大钻牛角尖的话,前途似乎不
太美妙。
那么,有没有办法绕过这所谓的“坍缩”和“观测者”,把智能生物的介入从物理学
中一脚踢开,使它重新回到我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轨道上来呢?让我们重温那个经典的双缝
困境:电子是穿过左边的狭缝呢,还是右边的?按照哥本哈根解释,当我们未观测时,它
的波函数呈现两种可能的线性叠加。而一旦观测,则在一边出现峰值,波函数“坍缩”了
,随机地选择通过了左边或者右边的一条缝。量子世界的随机性在坍缩中得到了最好的体
现。
要摆脱这一困境,不承认坍缩,那么只有承认波函数从未“选择”左还是右,它始终
保持在一个线性叠加的状态,不管是不是进行了观测。可是这又明显与我们的实际经验不
符,因为从未有人在现实中观察到同时穿过左和右两条缝的电子,也没有人看见过同时又
死又活的猫(半死不活,奄奄一息的倒有不少)。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是骑虎难下,进退维
谷,哥本哈根的魔咒已经缠住了我们,如果我们不鼓起勇气,作出最惊世骇俗的假设,我
们将注定困顿不前。
如果波函数没有坍缩,则它必定保持线性叠加。电子必定是左/右的叠加,但在现实
世界中从未观测到这种现象。
有一个狂想可以解除这个可憎的诅咒,虽然它听上去真的很疯狂,但慌不择路,我们
已经是nothing to lose。失去的只是桎梏,但说不定赢得的是整个世界呢?
是的!电子即使在观测后仍然处在左/右的叠加,但是,我们的世界也只不过是叠加
的一部分!当电子穿过双缝后,处于叠加态的不仅仅是电子,还包括我们整个的世界!也
就是说,当电子经过双缝后,出现了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世界,在其中的一个世界里电子穿
过了左边的狭缝,而在另一个里,电子则通过了右边!
波函数无需“坍缩”,去随机选择左还是右,事实上两种可能都发生了!只不过它表
现为整个世界的叠加:生活在一个世界中的人们发现在他们那里电子通过了左边的狭缝,
而在另一个世界中,人们观察到的电子则在右边!量子过程造成了“两个世界”!这就是
量子论的“多世界解释”(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简称MWI)。
要更好地了解MWI,不得不从它的创始人,一生颇有传奇色彩的休?埃弗莱特(Hugh
Everett III,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叫Hugh Everett,因此他其实是“埃弗莱特三世”)讲
起。1930年11月9日,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论科学与宗
教》,他的那句名言至今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
宗教是盲目的。”两天后,小埃弗莱特就在华盛顿出生了。
埃弗莱特对爱因斯坦怀有深深的崇敬,在他只有12岁的时候,他就写信问在普林斯顿
的爱因斯坦一些关于宇宙的问题,而爱因斯坦还真的复信回答了他。当他拿到化学工程的
本科学位之后,他也进入了普林斯顿攻读。一开始他进的是数学系,但他很快想方设法转
投物理。50年代正是量子论方兴未艾,而哥本哈根解释如日中天,一统天下的时候。埃弗
莱特认识了许多在这方面的物理学生,其中包括玻尔的助手Aage Peterson,后者和他讨
论了量子论中的观测难题,这激起了埃弗莱特极大的兴趣。他很快接触了约翰?惠勒,惠
勒鼓励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到了1954年,埃弗莱特向惠勒提交了两篇论文,多世界理论
(有时也被称作“埃弗莱特主义…Everettism”)第一次亮相了。
按照埃弗莱特的看法,波函数从未坍缩,而只是世界和观测者本身进入了叠加状态。
当电子穿过双缝后,整个世界,包括我们本身成为了两个独立的叠加,在每一个世界里,
电子以一种可能出现。但不幸的是,埃弗莱特用了一个容易误导和引起歧义的词“分裂”
(splitting),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宇宙像一个阿米巴变形虫,当电子通过双缝后,这个
虫子自我裂变,繁殖成为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变形虫。唯一的不同是,一个虫子记得电子
从左而过,另一个虫子记得电子从右而过。
惠勒也许意识到了这个用词的不妥,他在论文的空白里写道:“分裂?最好换个词。
”但大多数物理学家并不知道他的意见。也许,惠勒应该搞得戏剧化一点,比如写上“我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用词,可惜空白太小,写不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埃弗莱特的理
论被人们理解成:当电子通过双缝的时候,宇宙神奇地“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宇宙,在
一个里面电子通过左缝,另一个相反。这样一来,宇宙的历史就像一条岔路,每进行一次
观测,它就分岔成若干小路,每条路对应于一个可能的结果。而每一条岔路又随着继续观
察而进一步分裂,直至无穷。但每一条路都是实在的,只不过它们之间无法相互沟通而已
。
假设我们观测双缝实验,发现电子通过了左缝。其实当我们观测的一瞬间,宇宙已经
不知不觉地“分裂”了,变成了几乎相同的两个。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叫做“左宇宙”,
另外还有一个“右宇宙”,在那里我们将发现电子通过了右缝,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和我们
这个宇宙完全一样。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我在左宇宙里,而不是在右宇宙里?”这种问
题显然没什么意义,因为在另一个宇宙中,另一个你或许也在问:“为什么我在右宇宙,
而不是左宇宙里?”观测者的地位不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宇宙都会分裂,实际上“所有
的结果”都会出现,量子过程所产生的一切可能都对应于相应的一个宇宙,只不过在大多
数“蛮荒宇宙”中,没有智能生物来提出问题罢了。
这样一来,薛定谔的猫也不必再为死活问题困扰。只不过是宇宙分裂成了两个,一个
有活猫,一个有死猫罢了。对于那个活猫的宇宙,猫是一直活着的,不存在死活叠加的问
题。对于死猫的宇宙,猫在分裂的那一刻就实实在在地死了,不要等人们打开箱子才“坍
缩”,从而盖棺定论。
从宇宙诞生以来,已经进行过无数次这样的分裂,它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很快趋
于无穷。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宇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在它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
宇宙。有些和我们很接近,那是在家谱树上最近刚刚分离出来的,而那些从遥远的古代就
同我们分道扬镳的宇宙则可能非常不同。也许在某个宇宙中,小行星并未撞击地球,恐龙
仍是世界主宰。在某个宇宙中,埃及艳后克娄帕特拉的鼻子稍短了一点,没有教恺撒和安
东尼怦然心动。那些反对历史决定论的“鼻子派历史学家”一定会对后来的发展大感兴趣
,看看是不是真的存在历史蝴蝶效应。在某个宇宙中,格鲁希没有在滑铁卢迟到,而希特
勒没有在敦刻尔克前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而在更多的宇宙里,因为物理常数的不适合,
根本就没有生命和行星的存在。
严格地说,历史和将来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实际上发生了,或者将要发生。
只不过它们在另外一些宇宙里,和我们所在的这个没有任何物理接触。这些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