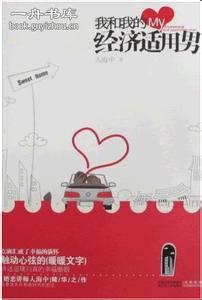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最大量的财富的欲望的影响更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至今还不能解释或预告实际的事件,除非用和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当的、正确的调整来修正这些结论(见穆勒,1967年,第321—3页)。
穆勒关于经济人的定义中有的特征需要强调。穆勒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象他那样地看待整个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能够正确地预告一个人在经济事务中的实际行为。
这种说法是“现实人”的理论,思诺不管穆勒的论文一生中都坚持这种理论(见鲍利,1949年,第47—8,61—2页)。
“现实人”理论后来为阿尔弗雷德·马尔萨斯所接受,而且人们敢说,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见惠特克,1975年,第1043,1045页注;马克卢普,1978年,第11章)。①穆勒所说的是,我们应该把特定的经济动机抽象化,这些经济动机如,在受到生计收入限制的情况下使财富最大化,追求闲暇;但同时又要承认生活中非经济动机(比如习惯和风俗)的存在,即使这种生活是属于经济学的一般范畴的。总之,穆勒所运用的是“虚构的人”的理论。此外,他又强调经济领域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从这个程度上说,政治经济学做了两次抽象:第一次是对真正受到货币收入推动的行为所做的抽象,第二次是对与“其他方面的冲动”有关的行为所做的抽象。
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人所熟知,马尔萨斯承认除了“痛苦和邪恶”这个积极的因素和“道德束缚”这个预防的因素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人口的压力,其意思就是要推迟结婚并在婚前实行严格的禁欲:马尔萨斯从不指望在婚后会有自愿的限制家庭规模。在马尔萨斯的后来版本的《论人口》中,他承认道德束缚的确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自动限制因素,这种因素是从人口增长中自己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相对于每个人都“尽力改善自己的条件”这个同等自然的斯密趋势,他提出了“生育的自然热情”(见布劳格,1978年,第74—5页)。于是,最大的马尔萨斯困难可以说是引起了这样的经验式问题,即已婚的人们当他们考虑应该给这个世界养育多少个小孩时是不是真的做了有理性的精打细算。这样,很清楚的是,经济人的概念就直接地和马尔萨斯学说的确实性以及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版本的关键问题联系了起来。
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穆勒还是思诺,都没有把经济人的讨论同工人选择工作时非金钱动机的作用联系起来,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册中非凡的第10章里是把这种动机做为工资决定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见布劳格,1978年,第48—50页)。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非金钱动机所关系到的并不仅仅是“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而是包括了甚至在牺牲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人们也要使心理收入最大化这一事实,包括了要减少不确定收入的变化而不只是要使其平均收入最大化,我们就会清楚,要详细地说明经济人的强制性动机比穆勒所想象要更困难。以现代的语言说,甚至要决定对据说经济代理人要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功能提出什么样的争论也是困难的。
在穆勒的论文中,紧接着经济人那一页的是描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说政治经济学是采用“演绎的方法”的、“基本是一种抽象的科学”,(见穆勒,1976年,第325页)。演绎的方法是同归纳的方法相对而言的,穆勒承认采用前一术语是有点不幸的,因为这个术语有时候是用来对一个哲学化的模式命名,而在经验中是根本找不到这种模式的:“对于归纳的方法我们指的是,这种方法需要以特定的经验而不是仅仅以一般的经验做为它的结论的基础。对于演绎的方法我们指的是(即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从一个假定的假说进行论证”(见同上,第324—5页)。因此,经济人的假说是以某种经验为基础的,这经验即对同胞们进行内省或观察所得出的经验,但是这个假说并不是从特定的观察或具体的经验中得出的。
由于假说只是一种假定,它也许完全“没有事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结果,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象几何学的结论一样,按普通的说法就是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的,这就是说它们的结论只是在特定的假设下才是真的”(见同上,第325—6页)。
于是,穆勒的政治经济科学指的是一种推理分析的东西,其基础是假定的、心理学的前提,甚至从这些前提看来,这种推理分析也是从人的行为的非经济方面抽象出来的:
当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运用于某个具体的事例时,就需要考虑这个事例的所有个别的情况;不仅是考察……这个事例中和研究的问题相对应的情况,而且同样要考察这个事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对于任何庞大的或具有强烈特点的事例来说,这些情况都是不平常的,而且没有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范围之内。这些情况被称为干扰因素。
以上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所仅有的不确定性;而且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一般地说以上原因也造成了各种道德科学的不确定性。在知道了干扰因素以后,为这些因素所做的必要的调整决不会改变科学的精确性,也不会有任何对演绎方法的偏离。对于这些干扰因素是不能仅仅用猜测来对付的。人们经常把干扰因素比做机器中的摩擦力,首先是仅仅把它们当做根据科学的一般原理猜测的、不能确定的扣除;但是很多这样的干扰因素会及时地被带到抽象科学自身的范围中来,人们会发现对于它们的影响能够象对受到它们调整的更重大的影响一样进行精确的估计。干扰因素也象那些受到它们所干扰的因素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可以对干扰作用的性质和数量做出先验的预告,这就象对受到这些规律所调整或干扰的更一般的规律所做的那样,但更恰当地可以说这些规律和一般的规律是并存的。于是,特殊因素的影响增加或者减少了一般因素的影响(见同上,第330页)。
正是因为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没有学习科学而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企图把他的科学运用于实践时他就会失败”(见同上,第33页)。
由于在人的事务中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混合的归纳一推理方法在事前就成为唯一的“道德科学的哲学研究的合理方法”(见同上,第327页)。但是,专门的归纳方法在事后就发挥独立的作用,它“不是做为发现真理的手段,而是做为检验真理的手段”:
因此,在检验我们的理论时我们不必过份地小心翼翼,在我们已经接近的特别事例中,通过把这个事例本应引导我们预告的结果和最值得相信的原因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得到那些确实已经实现了的理论。在我们的期望和真正的事实之间的差异经常是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重要的干扰因素上的唯一的事情,而这些干扰因素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不仅如此,这种差异经常揭开我们思考中的错误,这种错误比对任何可以恰当地称为干扰因素的忽视还要严重。这种差异经常可以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整个论证基础本身是有不足的;可以向我们显示我们所用以论证的资料仅仅是确实对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情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见同上,第332页)。
虽然这完全是一种无懈可击的证实主义的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勒不能使自己把对预言检验的失败等同于拒绝以下的理论:一个“我们的期望和真正事实之间的差异”表明,要抛弃原先的理论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而仅仅是因为它有“不足”。
穆勒的论文中为了满足检验我们的理论需要的那几页转向了对趋向律的极好的阐述。
毫无疑问,一个人经常对一整类的东西做断言,而这些东西中只有部分是真的;但他的错误通常不是断言做得过宽了,而是做了错误的断言;他预先指出实际的结果,但本来他应该只指出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例外这种东西的。被认为是一个原理的例外的东西,总是侵犯了这个原理的某些其他的和与之有别的原理:一些其他的力量冲击了原来的力量,并使之偏离原来的方向。没有和它的例外共同存在的 规律——一条规律在99%的事例中起作用,而它的例外在1%的事例中起作用,这是不可能的。有两种规律,每种都可能在百分之百的事例中起作用,通过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共同的结果。如果在两种力量中较不明显的一种被称为干扰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一个事例中足以超过另一种力量,造成了人们通常所称为例外的事例,这同一个干扰力在很多其他的事例中也许都作为一种影响因素起作用,没人会称这些事例为例外(见同上,第333页)。
三、趋向律
我们在前面说到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候已经遇到了趋向律,现在我们最好是暂时离开主题来考虑趋向律在科学工作中的正确性。古典经济学家考虑到了干扰因素,认为干扰因素能够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矛盾,这种考虑在现代经济学家中也有回响。现代经济学家呼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是永恒地和经济“规律”的一般前提或论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①在俗人和学科学的学生中,都广泛 地存在一种印象,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充塞在社会科学中,而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就极少存在。然而,离开事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不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科学理论事实上将导致完全封闭:在这个理论中引起所研究的现象发生重要变化的变量没有一个被省略,实际上只是在这个理论中的变量相互之间发生作用,它们同外界的变量没有发生关系。也许只有天体力学和非原子热动力学曾经接近于取得这种完全的封闭和完整(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6—8页)。物理学的高度封闭和完整的理论是很例外的,但甚至是在物理学和物理学以外的自然科学中也很少有有关的情况都被包含入它的理论中的例子,而这些情况远不是保持不变的。②
通常,只要是对一个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在自然科学中的出现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出现是一样多的:这种检验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在假定检验之外的其他有关的起始条件和有关的因果关系缺席的情况下来论证结果。总之,自然科学中说的是辅助性假设,这种假设在对科学规律的每一个检验中都存在——这使人想起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而社会科学说的是,如果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满足,社会科学的规律或假说就是正确的。但是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要排除理论中专门解决的问题之外的所有可变因素。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命题都是趋向律。但是,在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大多数趋向论证,以及所有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趋向论证,在它们之间的确有完全不同的世界。举例说,加俐略的落体质量定律当然带有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这一暗含的假设,因为在所有自由降落的情况中,物体在降落过程中都遇到空气阻力。
加俐略事实上采用了“绝对真空”这个理想来排除他所谓的“意外事件”的影响,但是他对诸如摩擦力等因素造成的干扰作用的大小进行了估计,而这一点在抽象的定律中是忽略了的。正象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穆勒完全意识到古典力学中这种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特点:“就象力学中的摩擦力那样……干扰因素也象那些受到它们所干扰的因素一样有自己的规律”(见穆勒,1976年,第330页)。然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中,遇到不是以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做趋向论证是很平常的——用一堆杂乱的东西来对任何未知的东西做假设——或者如果是专设的,也仅仅是在质量上专设而不是在数量上专设。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据说是受到特定的“相反作用因素”支配的,虽然对此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人们还是坚持认为和这些因素起相反作用的利润率的下降使这些因素发挥了作用(见布劳格,1978年,第294—6页)。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藏在基本规律中的负变化率和几个正的相反作用的变化率;很清楚,所有这些作用力联合作用的结果既可以是负的也可以是正的。①
总之,除非我们做些努力把一个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含义严格化,对“干扰的”或“相反作用的因素”的作用做确定的界限,否则整个争论甚至在总的变化方向方面也难以产生一个可以反驳的预言,而在变化的大小方面做出这样预言的可能性就更小。
穆勒从比索普·沃特利从两种意义对趋向论证所做的有用的区别中得到好处。沃特利是在1831年做了这种区别的,这两种意义是,(1)“如果一个因素不受阻碍地起作用,这个因素将产生一个结果,”和(2)不必管这个因素的确没有受到干扰因素阻碍这个事实,“这样一种状况的事情的存在就使得人们可以期望那种结果发生”(索厄尔,在1974年,第132—3页中引用)。就象穆勒自己所说的:我们经常说一个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指“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象例外这种东西的”(见穆勒,1976年,第333页)。沃特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