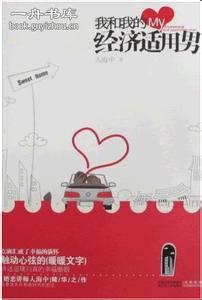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把历史学派总结为持有一种“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经济学观点也是同样地简明的:历史学派否定5个思诺—穆勒—凯尔恩斯论题中的每一个,更加上,他们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是持赞成的而不是反对的态度(见同上,第20—5页)。①
就象我们已经提到的,凯恩斯喜欢说经济学“必须以观察开始和以观 察结束”(见凯恩斯,1955年,第227页),他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含义有敏锐的感觉,他认为在一个论证的开始所用的“归纳的前提决定”和在它的结尾所用的“归纳的结论证实”采取了不同的逻辑操作(见同上,第203—4页注,227页)。虽然凯恩斯有时候说经济学的前提“只不过是对某些最熟悉的日常事实的深沉的思考”(见同上,第229页),他的书还是再次提醒我们,就象威纳尔曾经说的(见威纳尔1958年,第328页),“内省……不管在今天是不是时髦,在过去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研究的‘经验’技术,并且鲜明地和直觉或‘天生的思想’区别开来。”对于凯恩斯来说,不只是内省是经济前提的经验背景资源(见同上,第173,223页)而且“收益递减规律也能用实验检验”(见同上,第181页)。当然凯恩斯确实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从定义上说,内省不是一种可在人际之间检验的知识资源,那么它是如何为经济论证建立真正的经验起点的呢?他从来没有引用一个通过把一个变量放进定量的土地中来对收益递减规律进行真正的经验检验的例子,虽然黑恩利奇·冯·屠能和其他的几位德国农学家早些时候在事实上进行过这种检验。然而凯恩斯抵挡住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谴责,这种谴责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凭空地捏造假设,却很少关心这些假设是否现实(见罗特文,1973年,第365页)。
凯恩斯还提供了另外的证据说,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概念是一个对“现实人”而不是对“虚构人”的抽象。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穆勒坚持经济人是一个假说的简化的观点,这种简化是把真正暗含着经济行为的一套有选择的动机孤立出来。诺思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认为经济人只不过是理性的假定,是使受限制的行为最大化的假设。
凯尔恩斯恢复了穆勒的立场,强调经济人的假说远不是胡编乱造的。自从那以来,经济人被各式各样地描绘为是公理,是先验的真理,是不需证明的命题,是一个有用的虚构,是一个理想的典型,是有启发的构思,是不可辩驳的经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中的人的典型的行为模式(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1章)。现在凯恩斯强烈地为经济人概念的现实主义辩护,认为在当代的条件下自我利益的经济行为的确是支配了利他主义和仁慈的动机(凯恩斯,1955年,第119—25页)。他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并不是在“好象”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当纯理论是在人为的简化条件下假设发挥作用的力量时,它仍然宣称它所研究其结果的那种力量在其的确起作用的意义上是真实原因,并且在经济世界中的确以一种支配的方式起作用”(见同上,第223—4页;又第228—31,240页注)。
然而,在为这个命题所做的辩护中没有提供证据,只有因果关系的经验主义。于是,明显地和经济人的假说相抵触的现象就干脆被允许做为这个规律的例外存在。因此,“对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地方、惰性、习惯的爱,对个人尊重的愿望,对独立或权力的热爱,对乡村生活的喜好……都属于影响财富分配的力量,经济学家可能发现这些都是需要认识的”(见同上,第129—31页)。穆勒—凯尔恩斯的非竞争等级的劳动力的教条被誉为是“对公认的价值理论的调整……
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它的目的是把经济学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得更紧”(同上,第227页注)。
可以肯定,只有当我们检验经济的预言时我们才能判断一套特定的假设的现实主义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援引了穆勒的《逻辑》:“在任何具体的演绎科学中,其信心的基础并不是一个先验的论证本身,而是在它的结果和那些其经验的观察之间的一致”(见同上,第231页)。但是甚至在这时候,他又来了一个两面保全的说法:“我们可以有一个相信我们的前提和事实一致的独立的基础……尽管事实上要获得显现的检验是困难的”(见同上,第233页)。此外,由于“在所有采用演绎方法的情况中,它(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都或多或少存在,”我们不能“认为理论被推翻了,因为理论作用的事例并不是专门给观察提供的”(见同上,第218,233页)。为了说明“干扰因素”的广泛影响,他讨论了取消谷物法的失败,取消谷物法导致了麦子价格立即下降,对此李嘉图早就预言。在完成他的争论时,他责备李嘉图表现了“对所达到的结论的绝对的和一致正确的过份的信心”,忽视了“时间因素”和“时期的变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原因的最终结果已经自己产生了”(见同上,第235—6,238页)。
从凯恩斯在书里对“采用演绎方法中的观察功能”的很重要的论述中我们得到的观点是,不能指望这样的经济理论能得出直接的结果,它是一部“分析的动力机”,用来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把细节的观察和相关的“干扰因素”联系起来(见哈奇森,1953年,第71—4页;赫希和赫希,1975年)。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从马歇尔的影响中得出来的。凯恩斯向我们保证说“自由竞争的假说……从大量的经济现象方面看是近乎正确的”(见凯恩斯,1955年,第240—1页),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在任何特例中我们如何才能断定一个正确的近似。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一章是有些简化的,除了一些图表之外没有提到统计技术。当然,统计学史的现代阶段是同诸如卡尔·皮尔逊、乔治·尤勒、威廉·戈塞特和罗纳德·费歇尔这些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从1891年开始的(见肯德尔,1968年)。凯恩斯承认在对一个经济理论的检验和证实中统计学是基本的,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一个经济争论被统计检验解决的例子,虽然在杰文斯、凯尔恩斯和马歇尔的研究工作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结果,他留给读者的不可抗拒的印象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假设一般是对的,那么它的预言一般也是对的;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这些预言不对,那么通过对事实进行努力的研究总会发现某些特定的干扰因素能够解释这种不一致。
八、罗宾斯的《论文》
凯恩斯和马歇尔对所有方法论差异的最后调解的希望是短命的。新的世纪刚一开始就听到了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挑战声,到1914年或在此前后,凡勃、米切尔和康芒斯的著作已经产生了横跨大西洋的一整个异端的归纳主义学派;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一些时候,制度主义逐渐强大,一时具有成为美国经济思想中的支配地位流派的威胁。然而,到了30年代早期,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虽然最近新制度主义有点复活。
正是在这时候里欧涅尔·罗宾斯认为,是以现代的语言重申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立场的时候了,要表明正统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些什么和他们还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而在罗宾斯争论中的要素,例如有名的经济学的手段—目的定义和宣布所有效用的人际比较的非科学特征,是从奥地利的而不是从英美的经济学传统中得来的。①
在一个以经济学的大辩论为标志的十年,罗宾斯的《一篇论经济 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1932)作为一篇辩论的名著脱颖而出,产生了一场真正的轰动。就象在1935年第二版的前言所表明的,当时对罗宾斯《论文》的反应的内容集中在第6章里,具有坚持福利的人际比较的纯粹常规的本质。同时,在考虑到经济政策的客观性、认为经济科学是中立的争论中,罗宾斯被广泛和错误地认为在讨论政策时发布了自我否定的法令。另一方面,他的奥地利型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一门把人的行为做为在'给定等级的]目的和具有可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抓住了人的行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型式(见罗宾斯,1935年,第16—17页,弗雷泽,1937年,第2章,科涅尔1960年,第6章),这定义不久就站稳了脚跟,现在在每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的第一章中都有这一定义的回响。
罗宾斯宣称(罗宾斯,1935年,第78—9页):“价格理论的主要假设是个人能按秩序来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了。”这个基本假设立即成为一个先验的分析真理,“一个我们在经济方面的行为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和一个“经验的基本事实”(同上,第75,76页)。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是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命题,类似地,这一原理也是从有不止一个的稀缺生产要素假设和“简单的和不可辩驳的经验”得出的(见同上,第77,78页)。因此,这些假设中没有一个是“它在现实中所对应的存在允许做广泛的争论的假设……我们不需要有控制的实验来证实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它们的材料是那样丰富,以致只要把它们说出来人们就能明显地认识”(见同上,第79页,又第68—9,99—100,104页)。就象凯尔恩斯很早以前说过的,从这方面看来经济学的确有物理学的一面:“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经济学中我们基本上一般化了的东西的终极要素是通过我们直接的认识知道的,而在自然科学中这些要素只能通过推理知道。
怀疑个人偏好假设在现实中的对应物的理由比怀疑电子的假设的理由更少”(见同上,第105页)。这当然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悟教条,而这一直是奥地利经济学最偏爱的组成部分。悟教条总是和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怀疑相随相伴的,在罗宾斯那里也能找到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比强调它们的相似所造成的危害更小”(见同上,第111—12页)。
追随着凯尔恩斯,罗宾斯又再次否认了能够从数量方面预言经济影响;需求弹性可以显得是估计它的反面,它的估计在事实上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见同上,第106—12页)。经济学家所处理的不过是定性的微积分,这在特定的事例中当然是可用可不用的(见同上,第79—80页)。他突出地反对历史学派关于所有经济学真理都是因时因地的断言,大骂美国的制度主义者——“没有一条‘规律’是名副其实的,没有一个永恒正确的定量的一般化东西从他们的努力中出现”——并完全赞同“自从思诺和凯尔恩斯时代以来这门科学的所谓‘正统’概念”(见同上,第114,82页)。
另一点是,罗宾斯在“检验即将取得的答案的适应范围”的“现实主义的研究”和一个“能单独提供解决方法”的理论之间做了对比(见同上,第120页),并总结道:“某一个理论的正确是从它所做的总的假设中进行逻辑诱导的问题。但是它在给定情况中的运用依赖于它的概念对在那种情况中起作用的力量真正反映的程度,”这个论述在当时从货币数量论方面和从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做了说明(见同上,第116—19页)。就象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底下跟着的是以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在所有的经济预言检验中所固有的危险(见同上,第123—7页)。
在那有名和充满争论的第6章里,罗宾斯否定了对效用做人际客观比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永远无法通过观察和内省证实”(见同上,第136,139—41页)。几年之后,在1938年出版的对运用内省做为经济知识的一种经验源泉进行毁灭性的批评中,哈奇森指出了在接受把一个人内部的效用比较做为消费理论的有保障的基础的同时又否定把人际的效用比较做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的逻辑矛盾(见哈奇森,1965年,第138—9页)。当然,一方面在那么大的程度上把价值理论建立在假设别人和自己具有同样的心理的基础上,而同时又否定把关于人们的福利的假设做为同一种论证的骨架,这是很奇特的。换句话说,如果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福利做任何推断时没有客观的方法,那么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偏好做任何推断时也没有客观的方法。因此,假定“个人能按一个秩序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是这样做”,而毫无疑问“日常经验的材料”是和也是“日常经验材料”的某些消费者的行为相抵触的:尽管情况在变化,保持习惯的消费模式是刚性的;无节制的购买和受到刺激的购买同先前的偏好秩序是极不一致的;消费仅仅受到希望从经验中了解到自己的偏好的刺激,不要说消费不是受到自己的偏好而是受到一个人所感觉到的其他人的偏好的刺激,象所谓的赶潮流和势利影响(见库普曼斯,1957,第136—7页)。先验推论在需求理论中的危险并不比它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的危险更小。
幸运的是,从罗宾斯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方法论学家对他早期的方法论主张的事后思考。在《论文》发表了近40年之后,罗宾斯出版了他的自传,在自传中回顾了人们对《一篇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的欢迎。他仍坚持不接受对该书的大部分批评,不过在回顾中他同意他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和含义的检验问题注意得太少了:“在论经济的一般化的本质的一章中对今天所称的实在论抨击得太多了……这本书是在卡尔·波普这颗星在地平线上升起之前写的。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他对科学方法的开拓性的分析……书中的这一部分会是很不同的一种写法”(见罗宾斯,1971年,第149—50页;又1979年)。
人们对罗宾斯早期对定量研究的敌意的揭露很多,但大部分的揭露是很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做出的,让我们看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8年给罗尹·哈罗德的信中的评论(见凯恩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