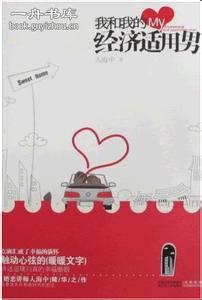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四章 新家庭经济学
一、家庭生产函数
最大化家庭(效用)的芝加哥理论,有时被称为新家庭经济学。它为我们提供了对方法论原理的最新的具体阐述。从加里·贝克尔1965年的有关时间分配理论的文章,以及此前雅可勃·明塞和贝克尔在生育率、人力资本构成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新家庭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种范围广大的研究框架,对家庭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活动作了一致的解释:最初的婚姻决策,生育孩子的决策,丈夫和妻子之间家庭爱好的区分,劳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最后甚至包括通过离婚而解散家庭的决策。
根据传统的观点,家庭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它最大化从市场里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所规定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经济学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最大化生产函数,其投入为不同家庭成员的市场物品和时间、技能以及知识。结果,这不仅扩大了通常属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问题范围的微观经济学标准工具,而且改变了对消费者行为的传统解释。①就象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见第六章)一样,消费者被认为是最大化从属于物品的效用的,这种效用主要取决于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因此,他们不会最大化比如说他们所作旅行的数量,而会根据旅行的各种特性(速度、舒适、费用等)把它们变换为不同的旅行模式,使之变成生产家庭合意的商品——“旅行”的投入。事实上,家庭规模、年龄结构、教育水平、种族、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其它指标,现在除了传统上的作为价格和收入变量外,还通过它们对家庭生产的服务的影子价格的影响,引用为家庭消费的解释变量。
新研究框架武装了新的“硬核”。在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所有家庭决策(包括组成一个家庭单位的决策)都是各种选择反复权衡的结果这种理性主义观念上,新研究框架没有新东西。但极力回避对偏好随时间变化而变动和不同人的偏好不同这对孪生假说的依赖,则是它的创举。未作具体规定的偏好随时间变化而作的变动和未作具体规定的不同人的偏好的差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正好能解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任何行为。因此,家庭经济学中的新研究框架是站在明确的“消极其发”立场上的:没有偏好问题。为了积极地表述它,“普遍而(或)一致的人力行为可以在不引进‘偏好保持相同’这个备格的情况下,用对效用最大化行为推广了的计算进行解释”(施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第76页;又见贝克尔,1976年,第5,7,11—12,133,144页)。
因此,作出稳定而相同的偏好函数这个假定的原因,显然是方法论方面的:它是为了明确作出有关行为的可确证的预言,尽可能避免建立在偏好变动、偏好差异、无知和冲动或神经质的行为基础上的特殊解释。所以,可以发现,象现代经济学中的少数其它研究框架一样,芝加哥研究框架是坚定地采用卡尔·波普设计的方法论形式的。由于这种原因,即使不因其它理由,这个研究框架也应得到我们的关注。
然而,这里不是对芝加哥家庭生产模式作出全面评价的地方或时候。它的主要思路是清晰的,但它的许多详细内容还有待确定;它已经开始受到严厉批评①,但不作出批评性讨论,就不可能对任何新生研究框架的优缺点作出公正的评价;此外,恰当的评价还必须考虑家庭行为的各种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解释,这就将把我们带到了遥远而陌生的领域。因此,我将把自己限定于对贝克尔的著作作出某些挑战性的评论,这也许能刺激读者去研究新家庭经济学,形成他们自己的评价。
二、自相矛盾
正如我们说过的,贝克尔决定把如波普所说的免疫策略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地说,也就是避免一旦理论与观察结果矛盾时作出特殊解释。然而,他常常采用特殊假定以便得到可检验的内容的做法,却又与这种决定相背。例如,人力资本形成是以它是对儿童“质量”的投资这种借口而进入家庭生产模型的,而拥有孩子的决策则始终当作在孩子“数量”上的投资;孩子则被视为培育他们的双亲希望消费的耐用消费。模型预言,家庭收入并不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而与从孩子的帮助中取得的效用正相关——在家庭生产函数中,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被认为是可以替代的。而且,由于母亲抚育孩子的时间的机会成本的影响,随着家庭收入提高,会发生为了节省时间而以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一句话,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但是,关于生育行为的模型的这个核心结论——在任何时点和所有家庭之间,收入与生育呈负相关关系——不是由模型本身解释的,而是用用来帮助解决初始的最大化问题的似是有理的辅助性假定(如对儿童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要比对儿童数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得多)来说明的(贝克尔,1976年,第197,199页及105—6页)。
类似地,在贝克尔的利他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他断言,捐赠者收入的增加将不成比例地增加他的慈善捐赠,而受赠者收入的增加产生的效应将正好相反(第275页),他对“合意的决策”进行了尽情嘲讽,而这种“合意的决策”正是捐赠经济学传统方法得出这种充分证明的结果所要求的。然而,这种结论又是基本上取决于对捐赠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和受捐者的福利作为一个自变量在那种函数中作用形式这二者作出什么假定。
或者进而言之,贝克尔不可能得出他的犯罪理论中的某些结果,例如,在对罪犯之间的风险偏好没有作出辅助性假定时,较之于判罪后的严厉惩罚,判罪的可能性对罪犯具有更大的威慑力(第48—9页)。换言之,贝克尔自己的分析方法几乎与传统的分析方法一样特殊;如果没有随意增加的额外信息,单期、静态的家庭生产模型的数量计算,就完全不可能得出人力行为各方面问题的明确的数量结果。
三、某些结果
贝克尔的著作全都简易得很容易被人当作漫画讽刺的对象,因为为了得到有时不说是平庸的、也是浅显的内容,它们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工具。①他的婚姻理论是从下列观察开始的:“由于男人和女人为寻找配偶而竞争,所以可以假定婚姻中存在一种市场”(第206页)。一个人当“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预期效用或再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配偶的预期效用时”,就会决定结婚(第10页)。结婚的收益来自于在投资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的生产率和获取市场物品的力量方面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互补(第211页)。为了解释实际中的婚姻模式,贝克尔运用了埃奇沃思的随意交换经济的“核心”的理论②,以表明男人和女人按照家庭生产的可买卖和不可买卖的“商品”的产出在所有婚姻中最大这一原则相互选择而组成家庭:“一种选择,如果个人不根据这种选择相互成婚就不会结婚并相互得到更多的好处,则这种个人选择就可以说是一种均衡选择”(第10页)。根据不同目标中男人和女人的比较利益分析完“适当的婚姻”后,贝克尔又评论说:
婚姻的收益也取决于品质,如美丽程度、智力、教育等,它们或许会影响非市场的生产率和市场机会。选择的分析……表明,品质价值的提高一般会增加婚姻收益,因为品质价值的提高对非市场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市场生产率则保持不变。可以相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缺乏吸引力或不很聪明的人很难与比较有吸引力或比较聪明的人结婚[第214页]。①
在经济学文献中,大概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用大锤敲钉子的例子贝克尔研究框架的一个更为严峻的困难是,家庭生产模型的阐述过于一般化,因而几乎适应于任何发现。在研究贯穿人类历史的婚姻模式的人类学文献中,遇到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一夫一妻制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主要婚姻模式,而曾经相当盛行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为什么又急剧没落。贝克尔假定把男人和女人联合成家庭而取得的生产力收益服从报酬递减规律,由此把一夫一妻制的兴盛原因解释为它是各种夫妻形式中“最有效的婚姻形式”(第211页),但是,如果事实表明由多个交互作用的家庭构成的联合家庭占优势,则只要设定不同形式的婚姻收益函数,这种假定就可以轻易地适用于联合家庭模式。
的确,贝克尔自己承认,存在一些能够说明多夫多妻制的有关男人生产率差异的假定,一种多夫多妻制的特殊解释(第239页)。换言之,如果不加上性别角色行为方面的各种文化约束,这种理论就不可能预示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事实上,新家庭经济学也许表明家庭成员合理地使他们适应于家庭内家庭工作的传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本身并不合理吗?给定相当大程度上反对妻子成为边际工资获得者的劳动市场的约束,丈夫和妻子被认为是根据比较利益原理来分担家庭工作的。现在,我们已经运用了关于市场机会约束的习惯与传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们排除在偏好函数之外呢?(费伯和伯恩鲍姆,1977年,第20—1页)。
除了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盛行外,贝克尔的婚姻理论还直接解释经过充分论证的“积极联姻”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门当户对有利于婚姻匹配的现象,在这里,“门当户对”是以象年龄、身高、教育、智力、家系、宗教信仰、人种、财产数量、居住面积等等品质来衡量的。然而,贝克尔的理论预言,从夫妻取得的收益能力来说,会有消极的联姻,因为他们在家庭生产中是封闭替代的。可是,这种预言却是与有效的证据相矛盾的。然而,他争辩说,他的理论涉及所有婚姻,而有效证据则有失偏颇,因为它只考虑妻子正在工作的那些家庭(第224—5页)。因此,我们将论证的结果摘录如下,其中几乎全是言过其实的空洞结论:
……经济学研究中有一大堆关于行为的纠缠不清、可以证伪的暗示。例如,它暗示,智力、教育、家系、家庭背景、身高和许多其它变量‘门当户对’的双方易于相互成婚,而从工资率及其它一些变量角度看,这却可能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工资率相对较高的男人与工资率相对较低的女人结婚(其它变量保持不变)这一暗示令许多人惊讶,但一旦把有效数据调整为大多数不工作的已婚妇女的有效数据,它就会与这些数据一致。经济学的探讨还暗示,收入较高的人结婚较早,且离婚较少,这些暗示与有效证据相符,却悖于一般信念。还有一种暗示是,妻子相对收入的提高使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增加,这部分地解释了黑人家庭的离异率大于白人家庭[第10—11页]。
理论又一次表明它适应于有关结婚和离婚发生率的所有已知证据(第214,220,221,224页),这在给定模型的易变性情况下,是不足为奇的。例如,为了把购买的市场物品和服务连同不同家庭成员自己的时间和技能变成“全部收入”的单一总和,它假定,家庭的“技术”保证规模报酬不变,没有联合生产,而且家庭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同等地受到象教育这样的生产率自变量要素的影响(这些假定保证了微观生产函数有意义的加总)。抛开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允许存在联合生产以及通过家庭成员的差异显示出来的品质的多样性,几乎能解释观察到的任何婚姻选择(第226,228页)①。
“我的分析是否证明了比较漂亮、媚人和能干的女人易于同比较健壮和成功的男人结婚这种流行信念呢?”贝克尔(第223页)问道。答案既是又否:积极的联姻一般是最合适的,因而会自发出现,但它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收益能力的差异标志着消极联姻。因此,如果漂亮而能干的女人婚姻上很少失败,这一定应当作理论的有力确证吗?最后,当我们增加上“喜欢”(Caring)时,任何事情都能发生:“大多数人无疑发现在恋爱婚姻中市场配置概念是奇怪而不现实的。但正如我表明的,喜欢能强烈地修正恋人之间的市场配置”(第235页)。事实上,“喜欢”完全能够把消极的选择转化为积极的选择(第238页)。
四、又一个证实主义
除了不断采用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形式外,整个贝克尔的著作还的确受到了证实主义的比较轻松的自由选择的影响:我们从传统上为经济学家们忽视的有关人类行为的有效证据开始,然后我们自己暗自庆幸,除了运用标准的经济逻辑外,我们并没有用任何更多的东西来解释它。我们从来没有做的是作出真正惊人的暗示,指示我们注意迄今没有料想到的“新奇事实”,那就是,这种理论没有具体打算作出预言。而且,我们认为这种经济学的探讨比任何其它有效的探讨都优越,但我们把比较的范围限定于我们自己的优势,却事实上从未确定我们知道的其它探讨方法①。显然,如果这些是游戏规则,则我们简直不可能害怕有何损失。
就其本身而言,在各种智力活动中建立经济学霸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尤其是它曾经同意,象贝克尔(第8,9,14页)那样,经济学的探讨不适于对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作同等的考察。可以设想,经济学家对其它知识领域的侵入的合理性,既得到了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角度研究老问题的新鲜眼光的证明,也得到了这种侵入在经济学传统主题上的反馈效应的支持。不管我们对芝加哥研究框架在前一方面成就的评价如何,都难否认它对后一方面的贡献。毫无疑问,消费的非金钱费用、特别是时间丧失的费用,对于分析与旅行、娱乐、教育、迁居、保健、事实上还有对有关可消费物品和服务的性质知识的搜寻行为,均具有解释价值。②
家庭与厂商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