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幻象-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通过大量的发现活动获得的真正学问相去甚远。最后,科学教育不得不面对那些科学也许不屑一顾的平庸之才,毕竟,一所公立学校总得要让它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够毕业。如果说科学教育是帮助人们了解科学研究精神的一种手段,那么,科学研究精神由此得益实在有限。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朱迪思·格拉比纳(Judith Grabiner)和彼得·米勒(Peter Miller)就进化论在科学教育中占有的位置所作的分析。1925年〃斯科普斯案件〃美国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田纳西州代顿市的一位名叫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的中学教师,不顾州议会的禁令,在生物课上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指控。审判结果,他被宣告无罪。译者注以后,创世说丢尽脸面,受到人们的怀疑。美国科学界信心十足地加紧了对进化论的研究,仿佛斯科普斯案件的判决已被普遍接受,成为铁案。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化论反而从公立学校的科学课程中删除掉了,因为各个州和各地方学校的董事会害怕引起争议,不愿再看到在斯科普斯案件发生地田纳西州代顿市发生的那种麻烦。科学教科书的出版商,自然也要迎合学校董事会的那种担心。把进化论从中学课程中删除,其实与进化论和创世说孰对孰错毫不相干,那只不过是为了保证科学不要过多地干涉学校的科学教育。所以,格拉比纳和米勒才这样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进化论者以为他们在斯科普斯案件中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说到中学的生物教学,他们并没有赢得案件,反而是输了。他们不仅输了,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输了。〃科学大众化遇到的最后一个难题,是科学的对象,他们各式各样,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新教徒模型的受众,几乎是可以懂得新教所说的善或者启示的任何人;有用知识哲学则可以取悦于知道发财致富、民主和独立中任何一项或两项是什么的一切人。可是,有可能喜欢科学研究精神的人,相比之下,那可是少多了,他们只是人口中希望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那一部分人。领会科学研究精神的价值虽然不一定要是职业科学家,但他在智力上一定要在他周围的大多数美国人中表现得卓而不群。由于这个缘故,于是便逐渐出现了四种不同形式的讲述科学的文体:一种是科学家与科学家进行交流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另一种是针对喜爱这种研究精神的非科学家所用的语言;第三种是面向广大群众的语言,即上面提到的那种产生误导的新闻体;第四种则是向孩子们讲解的语言,即科学教育所用的文体。
上面最后谈到的这个大众化难题,使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目前的状况仍然是三种非常不同的科学观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同时并存。这三种科学观当中,不用说,自然是有用知识哲学与美国文化的主流最为合拍,因为人们指望这种模型有可能产下的果实进步、民主和独立,仍然同200年前一样,都是孜孜以求的东西。至于新教徒模型,它的影响力自是大不如前,因为大多数新教徒都趋向把他们的信仰转向物质,而不愿再与现代科学争论应该怎样去研究自然界。不过,新教徒模型今天仍然有一定能量,例如颇为流行的〃科学创世说〃,就是它改头换面后的应时翻版。
最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科学研究精神。它虽然已经抓住了美国大多数科学家的心,但它却难以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清除前两种信仰系统。时不时,总会有人提出希望科学是善良公正的和有用处的要求。这种研究精神善良公正,但只是按其本身的解释才是如此;它是有用处的,但仅仅有时如此而已。比起这种新的科学观来,其他两种模型,因为它们的善良公正十分显而易见,用处也看得见摸得着,基础倒是雄厚得多。这种研究精神已经存在于美国文化之内,纵然美国文化宽宏大量,它与这种文化的种种明显的道德特征,联系仍然十分松散。这里对美国科学史所作的简略回顾还表明,似乎不可思议,造成冒充科学现象的那些条件不是来自早期的两种科学和自然观,反而缘于现代科学的出现。科学研究精神的实质虽然并未被大多数美国公众充分理解,但这种精神还是赢得了他们的敬重,这就是我所说的〃旧约全书式的科学〃。我想,毛病不在于这种科学本身,而是由于大众化工作的失败。然而,不管毛病出在哪里,我们都必须明白,这种现代科学观遇到了以前两种模型不曾有过的麻烦。它的智力实质与普通民众的大部分是不相容的,而它的常见符号却是从一种不同的自然和科学观那里借来的,即来自有用知识哲学。如果说冒充科学是在科学的实质与其符号之间存在的空档处出现的捣蛋鬼,那么,科学研究精神则远比它的两位前辈新教徒模型和有用知识哲学更易于受到这个怪物的伤害。
第三章 民主文化与科学的精神自主
在大众化的早期,即在19世纪末和进入20世纪以后的大约头50年,大众化在文化上的失败还不十分明显。那时候,其实采取了两种办法来回避这种失败。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和其他一些为美国联邦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他们按照新的科学研究精神从事研究工作,却十分注意借助有用知识哲学向公众说明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兢兢业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理论研究,同时,也向公众许诺会有看得见的切实成果。他们解释说,这种按新精神从事的科学工作确实是非常好的科学,不过,要按照选民、纳税人和获选的官员的接受能力完全解释清楚这种科学的合理性,那是不可能的。
科学家们采取的这种态度,当他们能够拿出大量显而易见的过硬成果时,看来效果不错。然而,如果拿出的成果比较抽象,例如关于相对论、测不准原理和哈勃常数,例如地质学中关于很早以前地球上的生命曾有过多次重建的假说,这种态度就不灵了。倘若科学家直言相告他的工作是Scientia gratia scientiae(为科学的科学),那自然更是不行。在那种情况下,用有用知识哲学遮掩起来的科学研究精神便要露馅 ,终于暴露出它无法汇入美国文化主流的那个矛盾。
从理性上欢迎这种科学研究精神的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本身并不是科学家,当时就对科学与美国文化的关系作过很多思索。他们断定,爱是盲目的。他们只看这种科学精神让他们倾心的长处,他们喜欢那些长处,认为它们同时发扬了关于科学和美国文化的两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理论。他们的这两个理论,我称之为〃精神自主理论〃(认为科学的道德精神可以脱离更大文化的道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和〃增强理论〃(认为科学和民主可以自动地相互加强)。两个理论全都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种科学研究精神有可能与美国的民主文化根本不相容。这两个理论低估了大众化在文化上的失败,因而反而违背初衷,使得科学得以被冒充的那些社会条件更为肆虐。科学精神自主权
有一种显然属于欧洲式的而非美国的逻辑,主张科学应该享有不受民主程序挟制的特殊的豁免权,也就是〃科学自治。向科学研究提供时间和金钱不应当有附加条件,也不必向外行人说明研究的方向或者可能获得的结果〃。那样一种主张一直是大陆科学文化的基石之一,美国科学家自然羡慕不已。
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就企图在大西洋的这一侧建立起欧洲那样的科学模式,梦想着有朝一日科学甚至不会受到捐助人的左右能够自己决定该做什么,而保持自主权。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来自理性方面,另一个来自政府的改革),在这片新教徒模型的有用知识哲学占上风的土地上,那种梦想才差一点有可能得以实现。
这头一个有利原因,是人们当时对法西斯主义公然宣称科学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侍女极度反感。所谓〃人种优生工程〃、〃德国物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希奇古怪的研究计划激怒了美国知识分子,让他们忍无可忍。〃人种优生工程〃是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及其同伙的一项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要弄清楚纯血统的日耳曼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在解剖学上的绝对差异,把前者遴选出来。〃德国物理学〃则不过是对〃犹太物理学〃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场粗暴的围剿。美国的知识分子光凭直觉便知道纳粹科学的那些做法,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精神道德上,都十分有害。但是,美国知识分子怎样才能驳倒纳粹分子宣称科学证实了纳粹思想的谬论呢?
一种做法,或许可以就一些经验细节问题展开批判,具体指出某个假说不成立,或者揭露某项实验的虚假性。进行这样的批判,不用说,必须具备相当的科学专业水准。但是,对纳粹科学持积极批判态度的那些人,大多数是科学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缺乏向纳粹科学挑战的必要学识和资历。美国的许多科学家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对为科学的科学的解释,极而言之,是要求科学家不过问政治。此外,也许还有一个麻烦,最近几十年,德国的〃人种优生论〃在英国和美国的优生学家中还找到了不少同情者。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想要把德国的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从科学中清除干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种做法产生于一种政治道义感。因为纳粹科学显然是纳粹政治思想的不加批判的延伸,所以,根本的问题应该是纳粹国家所确定的科学与政府之间的那种广泛的关系。如果证明了民主的价值要比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价值更能够帮助科学,亦即民主文化要比法西斯文化更能够促进科学的发展,那么,纳粹分子关于〃人种优生论〃和〃德国物理学〃的种种论点便会不攻自破。这种做法要奏效,就必须对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作出较为宽泛的定义。
影响最大的一种从政治道义感出发的观点,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来的。他在1938年和1942年先后发表两篇论述〃科学与民主社会结构〃的文章,论述了一种分为四个部分的〃科学的规范化结构〃。默顿分析说,科学结构的合理性取决于四项内在价值:普适性、知识所有权共有、无偏见和系统的怀疑主义。这其中,尤以普适性与纳粹思想格格不入。按照默顿的定义,普适性要求科学面向一切人,当然包括犹太人,而不应分人种、宗教或者血统。而且,在默顿的论述中,他提出的其他三项价值也全都不利于法西斯主义。他的无偏见要求,在科学与思想意识之间筑起了一堵隔离墙。知识所有权共有,驳斥了国家对科学知识的垄断。系统的怀疑主义,则反对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内部提倡的那种盲从。
默顿的四项价值规范化理论一提出,社会上就产生了一股要求遵守这些价值标准的强大压力。作为默顿理论的成果,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都信守了这些价值。这样一来,非科学家也就不难看出科学是一种有着重大内在精神价值的人类活动,而且它的规范化结构是与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绝对不相容的。通过单独把科学的功绩开列出来加以褒扬,这个理论特别强调了科学活动应该在精神上是自主的。默顿在论述科学是一种非常善良公正的活动的同时,也把它说成是不同于其他精神系统的一种精神系统,因为再没有别人的精神系统也同时具有这四种规范化价值。
那么,社会与科学的正常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按照默顿的观点,社会的正确方针应是支持科学家的工作却不干涉他们内部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界自身由于它那独特的规范化结构而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可以管理它自己的事务。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也就是非科学家,全都不具备裁判科学事务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科学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默顿通过论证指出:一个民主社会才会支持科学却不干涉它的工作;一个法西斯国家则必然会利用科学来扩张它的政治思想意识。更进一步,这种观点还认为,任何政府,即使是民主政府,企图让科学家对科学之外的价值承担说明的责任,那都是非民主的行为。
当然,我并没有把这种理论连同它的优缺点全都只归功于罗伯特·默顿一人的意思,那种理论绝不会像智慧女神雅典娜那样突然一下就带着智慧从主神宙斯的额头跳了出来。德国法西斯主义刚一冒头,在警觉的左翼人士中早就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不过,默顿用文字把那种情感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比别人更加透彻。他的精神自主理论,自那以后,便成为关于科学的社会学主流理论。有一个例子是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科学家的社会角色》(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在该书中对科学在欧洲文明的兴起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分析。本戴维认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社会相信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从而承认科学家在其中扮演的是一种合法的角色;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是非集中的,从而保证科学家拥有他或她所需要的全部学术自由。以此为根据,本戴维对最大限度提高科学家声望却不怎么要求他们直接解释自己工作意义的做法,备加称颂,而对反对这样做的人,则尽情嘲弄。他的著作是对默顿论点的详细扩充,其中也包括了非科学家只需要尊重科学,而不必理解它的那种观点。体现了这种自主理论而影响力还要大得多的因素,是美国战后采取的科学政策。它是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两届总统的科学顾问范纳瓦·布什(VannevarBush)提出的建议而制定的。在1945年的那份题为《科学,无垠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Frantier)的报告中,布什通过论证建议,联邦政府应当承担起支持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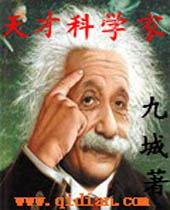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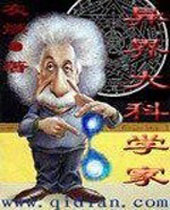



![(科学的超电磁炮同人)[黑琴]末世之我一直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