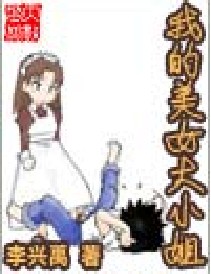女大王和她的压寨夫人-第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楚玄听到褚云驰三个字,心里一沉,心想苍莩也知道了?!难道阿姐与褚云驰早就……只有他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
楚玄越想越觉得苍莩说的是那回事,便问:“你既知道了,也该明白,不与他争,他却与你争,怎么办?”
“……那我也不能怎么办。褚云驰回京城的那几日,你可见他熬瘦了多少?我一开始还高兴,这人走了也好,总是与咱们不该有瓜葛的人。可见他饭也吃不下,功夫也懒得练,就叫我也跟着难过起来。”苍莩想着阿冉那些日子的可怜样,叹了口气,“我不过是要看着他高兴,至于让他高兴的是我,还是‘褚先生’,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年的情谊,还能因为来了个褚云驰就散了?”
楚玄听了,沉默良久,才道:“多谢你劝我。”
“嗯?”
楚玄苦笑道:“我本打算回家好好侍奉父母,再不回来……你看院子里我收拾好的东西,不过是将这些念想一起收拾了,都抛了去。若没有你,只怕我不日就要回去了……”
“什么?!你要走?!”苍莩一急,猛地推了他一把,“为什么?”
二人并肩躺着的屋顶原本就窄,叫苍莩猛地一推,楚玄一个没稳住就骨碌下去了,苍莩没想到他能滚下去,连忙伸手一捞,还是晚了一步,楚玄四仰八叉地摔在了院子里,亏得院子早就叫他收拾好了,不然摔在那些木头块上,只怕要磕出个好歹来。
看苍莩气急败坏地跳下来责问他,楚玄忽地反应过来了,苍莩说的似乎不是自己与庄尧的事,忍着疼痛问:“你说的那个人,是谁?”
苍莩挠挠头,一边扶他一边道:“还能是谁?阿冉啊。”
楚玄长叹一声,甩开苍莩的手,道:“你走!”
楚玄的一腔离情,叫苍莩毫不留情地打断了,她揪着楚玄下山,把楚玄打算要走这件事告诉了罗绮,还嚷嚷着要进去告诉庄尧,叫楚玄气急败坏地给拦住了。
一来是褚云驰说不定就在里头呢,他可是占了便宜,将自己的卧室搞成病房,随时进去也没有人说什么;二来,庄尧若是知道了楚玄为了自己差点要走……楚玄不知怎么的,并不想让她知道。这是他作为一个少年人的自尊。虽然不能得到喜欢的人,却也不想做出这种幼稚赌气的事来,叫别人把他看低了。苍莩的话,虽不是说与他,却字字敲在他心里。
我们这些年的情谊,岂是一个褚云驰就能给拆散了的?
楚玄拉着罗绮道:“不要与阿姐说。”
罗绮含糊地嗯了一声,望着什么都不知道的苍莩,心里默默叹息,还是这样天真无邪的人活得最轻松。
☆、第 83 章
京城。
薛魁才带回了褚云驰的回信,褚凤驰愁的直揪头发,连睡觉也是唉声叹气。袁氏劝道:“天大的事情也要休息好了才是。”
褚凤驰嗯嗯两声,却仍是一夜乱梦,一早天不亮,又得起来去朝上站班,等忙完回来了,禇靖正叫他过去一道吃饭。
这父子两人也是奇怪,鲜少一处用饭。从前郑氏喜欢一家人和乐,褚云驰又跟父亲不够亲近,是以吃饭的时候郑氏总要将一家人聚在一处,可等她过世,褚云驰又溜到宁远边地,禇靖便发下话去,观鸾业已成家,便分开吧。除非年节,父子二人便各过各的。
褚凤驰一进门,就见禇靖脸色不大好。
禇靖这个人,也是官场上混久了的老手,要说他喜怒不形于色吧,其实情绪上来了倒也有那么一点儿微妙的表现,他生气的时候,唇线比平日绷得更紧一些,看上去似乎有些笑意,却并不是个好兆头。郑氏原是最懂他表情的,如今褚凤驰继承了这项技能——要问褚云驰?只要他出现,老头就会把“喜怒不形于色”放在一边了,绝对是吹胡子瞪眼的。
褚凤驰只道父亲心情不好,也不知为什么,心里又装着一桩心事,要帮弟弟圆场,是以颇有些忐忑,一餐饭根本就没吃好。
禇靖放下玉箸,很有闲情地问:“小时候你与二郎总是争吵,你一个大个子,竟也打不过他,后来你母亲心疼你,说了二郎几句,你又护着他,倒真是亲兄弟。”
褚凤驰笑了笑:“总归是我弟弟,忍不住就要对他好些。”
话音刚落,就听禇靖冷笑道:“好到瞒着我弄鬼?”一指门外,“薛魁昨天傍晚回来,径直去找了你!我今天才抽空捉住他问一句,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揽了你弟弟的生意,帮他来糊弄我?”
禇靖竟然亲自审问了薛魁?听得褚凤驰吓坏了,当即跪下请罪,禇靖气得踢了他一脚:“没用的东西!我诈你一句就什么都招了?说,你那不争气的弟弟又叫你背什么锅了?”
褚凤驰擦了擦额角的汗,只觉得一阵胃疼,有这么个爹,实在是太闹心了,也没那个精力费心思说巧话与老头子周旋了,干巴巴道:
“二郎,二郎他还年轻,玩心大些也是有的,他……不欲这么快成婚。”
“屁话!”禇靖怒道,“这小畜生有多年轻?你这个岁数时,你家大娘都满地跑了!好啊,我说你怎么叫我把信夹在你二人往来的书信中,是为了方便他一道糊弄我?”
他越说越气:“他早过了玩闹的年纪!还不打算就迟了!他总是要回京的吧?门户相当的人家就这么些……”
褚凤驰插嘴道:“可此时为二郎张罗婚事,陛下岂不会多心?乐宁公主是陛下亲妹,阿爹不见,她坏了大事,陛下也不过将她下嫁而已。我也是做人兄长的,人君亦是兄长,便是嘴上不说,心里怎能不惯纵着?”
禇靖冷静下来想了想,确实如此。公主刚下嫁了个不怎么风光的人家——至少比不得褚氏吧,结果一回头褚氏就高高兴兴地说起亲来了?好像急于庆祝摆脱了公主这个大麻烦似的。
仍是怒道:“……谁又要他立时就成亲了?不过是慢慢相看,透露几分意思来,不要等他回来了,再没有合适的人选!京中淑女繁多,可合适的能有几个?二郎千好万好,却不在眼前,总有叫人忘了的那一天,你身为哥哥,就不能想得长远些?”
褚凤驰这回没话说了,灰溜溜地又被禇靖骂了一顿,又陪着禇靖用过茶,直到宫中差人来请禇靖进宫叙话,他才回去了。昨夜一宿没睡好,今天又被骂了一通,褚凤驰十分疲惫,准备歇个晌。
也是赶巧,他刚一回来,便有人来报:“宁远家信至。”
褚凤驰一听顿时头疼起来,直觉不是好事,便道:“拿来拆了吧。”
来报的仆役道:“是给相公的信。”
褚凤驰眉头一跳,愣了一刻,心说不会是二郎太心急,与禇靖吵架来了?便道:“信呢?”
“已送到相公案头了。”
褚凤驰想了想,他刚刚送走了禇靖,此刻禇靖的书房应该是没有人的,便也不歇着了,蹬上靴子就往禇靖的书房去了。
那封信果然就在案头。
因为是家信,送信的人也都是亲信了,并不曾用火漆封了,褚凤驰打开略扫了一眼,登时大惊!
恰逢有书童来收拾禇靖的书房,褚凤驰匆忙将未看完的书信收好放下,搪塞两句便出了门。
他才到了自己的院子里,就叫道:“快!速速去叫薛魁过来!”
薛魁一路上也是累得够呛,才歇过来,早饭午饭并在一起吃了,进来的时候还满头大汗。
褚凤驰道:“闻鹤竟如此莽撞,只怕阿爹要发怒了!”又连连叹气,“他还说不欲成亲,怎么又忽地冒出来个山野女子?我才叫阿爹骂了一顿,还不知道说不说得通,怎么他又变了卦?真是想愁死我!”
薛魁听得一头雾水,道:“郎君慢些说。”
褚凤驰一挥手:“我说,你来写!写好了速速送过去,叫二郎死了这个心!别说阿爹不许,就是我都不许这种事发生!”
当日晚间,禇靖回来得十分晚,褚凤驰听说他并未在书房久留,只坐了一盏茶的功夫就去休息了,也不曾大发雷霆,褚凤驰还纳闷。
结果到了第二天,禇靖终于爆发了。
这一日恰好禇靖在家中设宴,袁氏着人张罗了精致的酒席,款待的是几位朝中与禇靖面和心不合的老头子,席间不知怎么就去了书房,说是禇靖恰好翻看到了褚云驰的信,气得摔了杯盏,还把信给烧了,只留第一页,叫哪个老头子捡了去。登时闹得满城风雨。
尚书令禇靖家那个不肖子,欲求娶一边地山野女子。这下闹大了。
褚凤驰听说了事情经过,担忧得要命,连着好几天挂着黑眼圈去上朝,见着今上时眼睛都不知道该放哪儿了。
一头说褚家不要在公主的事情没有平息之前提及婚事,一头又闹得满城风雨。可气过了,褚凤驰又有些心疼,不知弟弟在宁远遇着了什么麻烦,怎么前后反差这么大。一边担心,一边还要想办法动用人手看能不能把这乱子压下去。在禇靖宴会上发怒的翌日,薛魁就被打发去了宁远,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可京里这一场热闹,到底还是没压住,这件事闹得太大,禇靖竟是一副完全不管的姿态,连今上都几次垂问,倒不像是不喜,只是叹息了几次,褚凤驰只觉得心里累得要命,还不敢表现出来,只能闷着头板着脸了。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今上望着他,有时竟带着些愧疚?
褚凤驰想不明白,又不敢问他爹,憋了好几天,直到禇靖有空了,才把他叫了过去,又是劈头盖脸一顿骂。
禇靖这几日多在宫里留饭,父子连见面都不多。
“薛魁人呢?”禇靖背着手,一脸怒气,“你又把他支使到哪儿去了?怎么,你是觉得家里该是你说了算的时候了?”
这话说得重了,褚凤驰脸色一白,不知怎么辩驳,几欲垂泪。
禇靖也知道大儿子不像二儿子,性子憨直些,受不得他这么重的话,于是又语重心长地安慰道:“坐下吧。也不知你像了谁,这么个脾气,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家交到你手里?你弟弟还要赖你照顾呢。”
褚凤驰默默坐在禇靖对面,看禇靖慢悠悠地斟酒。
“你是叫薛魁又去了宁远?”
褚凤驰干巴巴地道:“是。我叫二郎回京来,与父亲好生说一说。想必他也不过是一时糊涂,父亲莫要怪他太深。”
不想禇靖竟用一种高深莫测的眼神看着他:“我听书童说,你进了书房一趟,以为你知道了。怎么听你这话,竟像是什么都不知道?”
褚凤驰一惊:“我,我……”
禇靖也不曾怪他,从怀里掏出几页信纸来,皱巴巴的还带着体温,褚凤驰接过去看了一看,大惊失色。
☆、第 84 章
“阿爹宴饮之日发怒,就是为了这个?”褚凤驰目瞪口呆,又问,“这不对,不是除了第一页,其余都烧了?”
禇靖都不知道怎么教育儿子了,从案头抽出没被烧的第一页,和褚凤驰手中的几页正对得上。老头子早就换了信纸,烧信是做给别人看的,真正的信他没舍得。
不过,除了叫褚凤驰吓坏了的第一页,写了褚二要求娶一个边地的山野女子外,信中内容还真是该烧的。
前一半还好,写了宁远民生,略有些琐碎,后半段却叫褚凤驰看出了个大新闻——宁远开出一处矿藏来,就在褚云驰买下的那片密林里。那处地方靠近东胡,自来都是战地,并无人去开采,是以叫褚云驰捡了这个大便宜。
矿藏于国家来说,是一等要紧的资源,铸造礼器武器与货币都少不了它,是以褚家必要守住这块地方,对外防着东胡,对内防着其他士族觊觎。又说当地人种植了一种“草棉”,与木棉大不相同,可织布成衫,比丝易得;亦可絮进夹衣里保暖,比裘衣廉价。
最后褚云驰在信中道,先祖母亦出身边地小族,却与祖父伉俪情深,一生偕老,他愿效仿先祖,与一边地女子结发,为国,也是为褚氏守好宁远一地。
言辞切切,却叫褚凤驰半晌说不出话来。
而最后一段险些叫他一口老血吐出来。他的好弟弟嘱托他爹:还要想个办法,把这件事处理妥帖些。
什么叫妥帖些?首先,褚云驰要娶个边地女子,就够惊世骇俗的了,不能叫京城士族猜忌什么;其次,还正巧赶在公主下嫁这当口,不能叫皇帝猜忌什么。
褚凤驰憨直是憨直,却并不傻,这事涉及利益,顿时叫他脑子也转得飞快。禇靖那一怒,恐怕是故意做给京中贵族看的,好把这件事闹大了。
既如此,褚云驰自然是不可能再娶京中淑女了——也没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了。这样,留在宁远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只是……
“阿爹,二郎的婚事……二郎竟为了一座矿就委屈自己娶个山野女子?”褚凤驰惊诧,“我褚家就沦落到靠子弟的婚事换取利益的地步了么?”
禇靖面色也有些郁郁,不过倒也不算生气,想是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叹口气道:“你这个弟弟,自小就有主意……旁人若做了我的儿子,怎还会跑出京外去?旁人若得公主青眼,管她是什么脾性,只怕要先占了皇家的便宜再说。你算算看,凡事只要他想做,我可拦得住?我拦了二十年,不还是背着我,勾结他舅舅,跑到那么个边陲之地?”
骂了几句小畜生,话锋一转,又道:“可这回他求到我这里了,终究是心里有我这个父亲。有些事啊,毕竟是你这个兄长做不来的。”
褚凤驰仍是不能释怀:“难道是他在那边儿做下了什么?还是受人要挟?京中淑女如何不好……”
禇靖竟比他看得开:“你先祖母亦是边地小族之女,又有何不妥?”又一指信中某页某处,“这家女娘,听闻出自宁远崔氏。虽说与陇西崔氏不是一支,却也是谱系上有过的。”
褚凤驰仔细一瞧,果然寥寥提了几句,他看得不仔细也没注意。这回倒也不说什么了,毕竟禇靖生母也是小族出身,褚凤驰不敢多说,只好挑了个旁的,也是他十分不解的来问:
“话虽这么说……可陛下那里怎么办?先前二郎不是说,若是褚氏急于婚配,恐怕陛下不喜?”
禇靖看了他一会儿,笑道:“这话果然是闻鹤说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