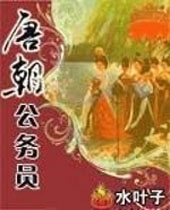唐朝有鬼之白骨变-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韩湛摇头,李岫也没有心思执著于此,只是冲着守城的城门郎吆喝,说要有急事需速速进城,一边还催着韩湛亮出羽林郎将的腰牌。
进城之后,李岫也不急着往衙署赶,只是命众人在门下守候。韩湛不解,问他何故,李岫回说:
“昨夜听得使者宣旨,我就觉得纳闷,为何非要在‘春明门’内缉盗呢?就算贼人不敢堂而皇之自明德门进入皇城,东、西、南尚有通化、延兴、启夏等其他七道城门……以我看来,圣旨上这般说,便是暗指贼人必从春明门下过,”顿了一下,李岫接道:“据华妃墓的守陵人说,那大冢便是这几日才‘入殓’的。华妃墓中的宝物在这期间早已被洗劫一空,显然已经自灵柩中被移往别处,现下那么大一笔珍宝,定是要流进城中来的,我们只要守株待兔便可。”
听罢,韩湛不以为意地摇头,道:“这样解释未免太过牵强附会了,况且就算如此你怎么知道贼人会在今天进入长安?”
李岫沉默了一会儿,道:“冥冥之中,我就是这般觉得。”
言下之意便是瞎猜的,韩湛不说话了,一边凝眉一边扶着隐隐作痛的额头。
可是不久之后,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辰时门开不久,真有几个身着孝服之人运着一只硕大的棺木进入城中,李岫当机立断,开馆查验:那棺中果然俱是被盗的随葬珍宝……
这一趟真算得上误打误撞,一把烂牌竟博出个贵彩来。
之后李岫便同韩湛分道扬镳,一个回到府中述职,另一个则押解贼人回归衙门。
此刻曹县令问询,李岫也不敢隐瞒,遂将昨夜种种,除却一些旁枝末节以及墓中那些怪诞诡事,尽数告知。
听罢,曹德淳起初还不相信,权当李岫是在胡说八道,直到李岫说有左金吾卫的韩将军佐证,他才信服,一边啧啧称奇,只道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少顷,京兆府差人传令说,需提调犯人直接下到大理寺狱中,曹县令和李岫一道将人送了过去。
到了地头,负责断狱的大理寺卿、掌管全城事务的京兆尹以及庆王府中掌事的幕僚都聚拢一处,还未提审犯人就先将李岫审了一通,李岫站在丹墀之下,向上位的朝廷大员们禀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这般待诸事安定,已经时近黄昏了。
李岫一整日未食一粟,加上一宿未曾阖眼,早已疲乏无力,腹中饥肠辘辘,他骑着马回到宣阳坊的小宅前,刚在朱漆斑驳的门上叩了两记,门便“吱呀”一声打开了。
原以为前来应门的是俞伯或者小桃,可是下一瞬自门后探出一张白皙俊秀的面孔时,李岫还是不自觉地楞了一下。
杜重蠹虫(上)
看到白晓谷出门相迎,李岫有些意外,正要开口问询,白晓谷却自门内钻出,不由分说扑进他的怀里。' ^'
此时虽然时近黄昏,可是路上还是有不少行人,见着这一幕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李岫迅速地涨红了一张脸,轻拍怀中人单薄瘦削的背脊,哄了一会儿才教白晓谷松开自己。
李岫拉着白晓谷进入宅中,刚阖了门绕过影壁,一对纤白的胳膊又从身后绕到他的胸前,不依不饶地圈着他,李岫轻叹了一口气回过身,面对怀中人,道:
“怎么了?”虽然知道白晓谷素来喜欢粘着自己,可是还从没见过他这般撒娇撒痴的。
“我……我……”白晓谷显然这些日子嘴皮子上的功夫没有多大长劲,嚅嗫了半晌才吐出一句:
“我……想你。”
话一出口,李岫着实愣了一下,再看白晓谷,虽然他依旧表情木讷,可是自那清澈的眼底可以瞧得出:这句话发自肺腑,说地情真意切,绝不掺半点逢场作戏的虚假。
李岫想着白晓谷身世可怜,现下定是将自己当成了唯一的依靠。而打从接白晓谷回来同住之后,除了值夜自己从没外出那么久,任他一人在宅中空等一定十分寂寞了。这般念道,李岫心中顿时一片柔软,执起白晓谷的手,一边问他有没有用过晚饭,一边牵着他往里屋走。
仆妇早就做好了一桌饭食,白晓谷虽然贪食,可他盼着李岫回来一起用饭,所以一直眼巴巴地候在门口,直到现在饭菜都有些凉了,李岫想唤小桃来将酒食温过,可是叫了几声,始终无人应答。
李岫明白那顽皮的侍童应是趁着自己外出又偷溜出去玩了,心中暗道待他回来定要好好数落一番,一边只得自己到灶房去温酒菜。
白晓谷原本想跟去的,不过才刚走了两步李岫便说无须跟来,只教他乖乖留在桌前等候便可。
于是白晓谷顺从地留在堂上,一边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李岫的宅子这个月来他来来回回瞧过无数遍了,屋内乏善可陈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就在这时,白晓谷忽然瞥见,原本李岫所坐的那方席子边角上,有个宛若压扁的杏仁般大小的物件正嵌在其中。
白晓谷好奇地挪过身子,拾起它,发觉这乃是一块木质的牌状物件,分黑白两面,黑面上绘着牛犊,白面则画着锦鸡,样子十分精致。
白晓谷并不知道这东西唤作樗蒲,是种赌博用的掷具,不过第一次瞧见还觉得分外有趣,于是便在掌间翻来覆去地倒弄,甚至还塞进嘴里咬了一口。
骰子并不好吃,白晓谷咂了咂嘴,将它吐了出来,之后又用两只手将其往外轻轻掰了一记——谁料“啪”得一记脆响,那骰子竟应声断开了。
眼看好端端的一枚骰子被自己生生折成两段,白晓谷愣在当场,再看那断开部分,原来中间是空心的,内里已经蠹烂腐朽,故尔一掰就裂。
这骰子毫无疑问应是属于李岫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要紧的事物,这么想着,白晓谷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却在这时瞧见李岫已经从灶房温好了饭菜折了回来,白晓谷唯恐被李岫发觉自己弄坏了骰子,急急忙忙将两块碎片重新按在一块儿塞回了原处。
重新步入厅堂之后,李岫一边殷勤地替白晓谷布菜一边催促他快吃。而这过程中,白晓谷一直心神不宁,只因为在李岫坐定的那瞬,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一记细细小小的呜咽声自李岫的身下传来,可是李岫却一无所觉。
晚饭过后,李岫洗漱完毕便早早回内室歇下了,他一宿未睡,一沾枕头便睡得香甜。趁此机会白晓谷重新回返堂前,在李岫原来落座的地方摸索了一阵,很快便摸出那枚骰子的碎片,以及席子下边藏着的……一只奇怪的小东西。
那是个不过指甲盖大小,圆不溜丢的玩意儿,肥乎乎肉嘟嘟的,乍一看就是个小小的肉球,可是仔细打量,这“东西”居然还长着口鼻,穿着衣裳,头上甚至还像模像样顶着一只不过蝇头大小的幞头。
“哎哟,疼死老夫了……”那个“东西”一边捶着自己的背脊,一边“唉唉”呻吟着,十分生动有趣,白晓谷将它捉到掌心饶有兴趣地拨弄了几下,对方立刻发出不满的抗议声:“轻点……轻点!哪里来的小妖……这般无礼?还有刚才那个人类的小郎官……简直就是目无尊长!”这般说着,还絮絮叨叨地抱怨方才李岫将它一屁股坐扁了,白晓谷遂用两根手指帮它揉了一通,将其揉回了一只整圆,那东西才懒懒地伸了伸自己那双又细又短的腿,而后趾高气扬地指着白晓谷,道:
“老夫姓杜,单字一个‘重’,你呢?”
白晓谷盯着小小的杜重,半晌才回过神指着自己呐呐回道:“白晓骨。”
“哦,原来是个白骨精。”杜重撇了撇嘴,用有些不屑的口气咕哝了一句,而后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皮,道:“老夫饿了,去弄点东西来。”
白晓谷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杜重这是在向自己讨东西吃,正好桌上有些残羹冷炙没有收拾掉,白晓谷撕了一小块汤饼小心翼翼地递到杜重的面前,他却一脸嫌恶地推开,道:“老夫才不稀罕人类的食物,你去找老夫能吃的东西来!”
白晓谷不知道杜重爱吃什么,于是呆呆地杵在原地,杜重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没好气道:
“听得老夫的名讳难道还不知老夫爱吃什么吗?(*杜重=蠹虫)真是个呆子!去找张纸来!”
话音刚落,白晓谷便乖乖地摸进东厢,在李岫的书案上随便抓了一张没有着墨的宣纸,盖在杜重身上,不一会儿,只见那纸中央蛀出一个钱眼大小的洞,接着那洞越蛀越大,直到最终全部消失殆尽——
“身子变小了还真是不方便,这纸滋味也一般,比不上那些贡纸……”杜重抱怨着,一边抹了抹嘴巴,打了个饱嗝,那肥嘟嘟的身子甚至在白晓谷的手心里弹动了一记。白晓谷一直安静地自上方看着杜重,虽然有股冲动想再揉揉这个触感很好的小东西,可是想到杜重方才气急败坏的摸样,便忍着没有再去摸他。
杜重“纸”足饭饱之后,在白晓谷的手中翻了个身,唤道:“喂,小白骨精。”
白晓谷把脸凑近,看到这小小的蠹虫以一种十分嚣张的姿势支着头,侧卧着:“你知道老夫是何许人吗?”
白晓谷摇摇头。
杜重清清嗓子,道:“老夫乃是个地仙,有五百年的道行,当年在渡天劫之时不慎被困于一枚樗蒲骰子中……今次因缘际会,从桎梏中脱身,多亏你出手相助……这般,你有什么要求老夫的,尽管开口便是。”杜重此话无非就是感谢白晓谷救自己出来,并许诺报恩之事,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被他讲得拐弯抹角,白晓谷一时没有听明白。
杜重不耐白晓谷的愚钝,正欲发作,忽而想到什么,一拍额头,道:“对了,你有没有瞧见另外一只骰子?”
听闻,白晓谷再度摇头,他只在李岫的席子下找到了这一枚樗木作的妖精容器。
杜重却不信,自白晓谷的掌中蹦到席子上,轻盈的动作和那臃肿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顿乱蹿之后,似乎确认了白晓谷所言非虚,他一屁股坐到了那断成两截的骰子上,有些失落地喃喃了一句:
“完了……老刁丢了……”
杜重蠹虫(下)
杜重正兀自烦恼着,白晓谷则饶有兴趣地蹲在一旁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两人都没有留意到此时正有个人影朝着他们的方向靠近。' ^'
小桃自身后猛地一推,白晓谷猝不及防,重重跌倒在地。
看到白晓谷狼狈的模样,小桃得意地叉腰笑起来,在笃定白晓谷不会在自家主人面前告状之后,常趁李岫看不见时使些小伎俩作弄他。这两天李岫不在宅中,小桃更加变本加厉,动辄便推搡打骂,将白晓谷完完全全当成了供他撒气取乐的人形木偶。
白晓谷也逆来顺受惯了,从来不晓得要反抗小桃,不过在听到“哎哟”一声,杜重那小小的身体被小桃踩在足下之后,他立马跳起来,将小桃一把推了开来。
而后白晓谷重又趴回地上,摸索着杜重被踩扁的身子,而被推知一旁的小桃回过神来,登时勃然大怒。
他一向对白晓谷颐指气使惯了,除了最初救蜘蛛那回白晓谷便再未反抗过他,今次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任他欺负的痴儿居然敢还手,小桃一时火气上蹿,扑到白晓谷身上没头没脸便是一顿拳脚。
白晓谷闷不吭声,默默承受,直到小桃打累了,松开了他,他又没事儿人似的趴着继续寻找。
见状,小桃气急,最后重重地踹了白晓谷一脚,方才离去。过了半刻,白晓谷终于在青石的缝隙中抠出了被挤扁的杜重,又是一通猛搓才将他揉圆。
恢复了原状的杜重先是在白晓谷的掌中喘了一阵,气息平稳之后忽然愤愤道:
“你身为妖精,怎么那么窝囊?”方才他是亲眼见到小桃是怎样待白晓谷的,很是替他报不平。
白晓谷的体质根本不知疼痛,所以对这事并不在意,于是便回道:“他打的……不疼。”
杜重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在他看来虽然白晓□行尚浅,又是初涉人世,可作为他的恩人,怎么能任“人”欺凌呢?这种事他绝不会坐视不管!
杜重眼珠骨碌一转,计上心头,他一蹦一跳跃上白晓谷的肩膀,然后挂在他的耳下“这般那般”一通授意……
月华如练,长安万家灯火。
寿王夫妇此刻正同咸宜公主于王府偏厅的灯坊下畅饮,酒过三巡,咸宜公主忽然提起了今早轰动全城的那桩大案:
“……据说庆王昨夜梦魇,他的生母华妃娘娘衣不蔽体地前来哭诉,说有贼人盗她陵冢……庆王至孝,醒来之后便入兴庆宫向圣人禀告。”
“圣人即刻召京兆尹彻查此事,不消两个时辰,万年县就抓住了发冢的贼人。”
“听得大理寺的差人讲,贼人为掘华妃墓中的珍宝,在百余步之外另起了一个大冢,一边掩人耳目,一边暗度陈仓……华妃的尸身被辱,双臂被斩,就连舌头都被割掉了……”
“啊呀,姊姊,别说了,”听到这里李瑁打断了咸宜公主,猿臂一伸将娇妻揽到胸前,“你说这般可怕的事体,玉环听了会害怕的。”
就像回应李瑁所说,杨玉环在他的怀里轻轻颤抖了一记,露出有些惊惧的神情。咸宜公主笑道:“玉环的确胆小呢,你得多宠着她一些。”
李瑁笑笑,单手覆上杨玉环的手背,二人相视一笑。这对少年夫妻至今已成亲五载,依旧恩爱无匹,咸宜公主见状,只是赞叹他们二人是对教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过了酉时,咸宜公主准备回府,她的住所也在入苑之中,乘上油壁车不消半刻便能抵达。
三人作别,依依不舍,直到公主的车舆渐行渐远,寿王忽然敛起笑容,一直牵着爱妻的那只手也在此时松了开来。
同咸宜公主在时完全判若两人,李瑁的脸色此时阴郁地吓人,他一语不发,丢下妻子转身就欲往内室走,杨玉环急忙上前捞住他的袖子试图挽留,却被李瑁无情地挥开。杨玉环脚下不稳,惊呼一声跌倒在地,李瑁闻声也不回身搀扶,只是侧过脸,不咸不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