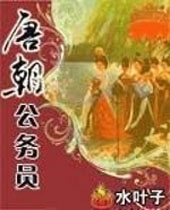唐朝有鬼之白骨变-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没有倒掉,忽然心念一动,也不知怎的,李岫鬼使神差地湿了面,再度望进盆里,只见里面映出一个眉清目秀的垂髻小童。李岫楞了一下,瞧那小童着实眼熟,而在他眼角同样的位置上也长着一粒小痣,这般李岫才认出小童竟是儿时的自己。
原来穆仙客并没有施行欺诈,这金盆确实是真,可为何别人使用的时候这盆没有反应,偏偏却能照见自己过去的形容?李岫不明就里,探头再看,那盆中的稚童却已经消失不见,改而映照出的是他现在的容颜。
李岫怔了怔,以为方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幻觉,还欲再试,忽然听得身后传来一声悦耳的轻笑,那声音如此熟悉,听得李岫心头一憾,他急急回过头,只见身后之人长身玉立,周身镀着一圈柔和的银光,那绝伦风姿……无疑便是这几月来令他朝思暮想的那人。
“怎么是你?”李岫喜出望外,惊呼出声,迎上前刚想去握白衣人的手,却被白衣人不着痕迹地躲了开来,李岫一呆,有些不悦地蹙起眉,白衣人遂柔声道:“岫儿,现在的我只不过是留在你梦中的残象,一旦你碰了我,梦就该醒了。”
李岫这才稍稍舒缓了眉头,但很快又质问道:“为何这数月来你杳无音讯?”
“我一直就在你身边……”
“那为何不现身?”
白衣人摇了摇头,道:“这数月你过得很好,我并没有现身的必要……”
听罢,李岫忽然觉得胸口犯起一阵酸楚——原来自己这数月来的相思对眼前人而言竟是一文不值么?这般念道,李岫不禁攥紧了拳头,白衣人见状,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口中喃喃:“我又何尝不想见你?”
虽然只是轻声细语,声量却足以教李岫听得分明,李岫闻言一怔,那些妄自菲薄的念头顿时被丢到了九霄云外,一时竟兴奋地双颊染绯。
两人就这样脉脉相顾,过了好一会儿,白衣人才道:“其实今次我托梦前来是因为有一桩要事相告。”
“何事?”
白衣人道:“这间逆旅,并不寻常。”
李岫颔首,即便白衣人不说,他也察觉到了此处的诡谲,可是究竟有哪里不对,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若是翌日离开此地,记得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再回来了。”白衣人顿了一下,“你一定要记得!”
李岫心中古怪:“为何这般说?”
“因为一旦梦醒,你便会忘记梦境里的一切。”
李岫一愣,又问:“包括你吗?”
白衣人缄口不答,算是默认了,李岫心尖一痛,忙道:“不会的……就算我忘记了一切,也不会忘了你。”
白衣人听闻,似乎动摇了一下,他张了张口,还是欲言又止,只是冲着李岫苦笑。
李岫却不依不饶道:“既然是梦,你把面具揭下来让我看一眼……”
白衣人摇了摇头,道:“没用的,就算瞧过我的容颜,醒来之后你自然会忘记。”
“即便这样,我也要在梦里看个真切!”
白衣人见他如此坚决,只得轻叹了一口气,将覆在面上的那半张面具轻轻取来下来……当李岫看清他的容颜,不由地大吃一惊,还未容他回过神来,白衣人已经走上前埋首在他怀中,李岫本能地环住他的肩膀。而就在刚碰到白衣人的一刹那,李岫只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身子仿佛陷入了一股激流漩涡之中!他挣扎着许久,好不容易睁开双眼,却发觉天色微明,白晓谷正被自己紧紧拥在怀里,二人正以一副暧昧的姿态纠缠着横卧在榻上。
李岫有些发怔,依稀只记得自己做了一场好梦,可是梦里种种却任凭他如何回忆,都忆不起来。
须臾,忽然感到身下异样,李岫松开怀中人,探进被褥里摸索了一阵,竟摸到一处粘腻湿润的物事,李岫有些怔忡,就在这时另一只并不属于他的,微凉滑腻的手也跟着遣进了腿|间,李岫浑身一个激灵,慌慌张张地将白晓谷的手抽了出来,却为时已晚,只见白晓谷的指尖正粘着那事物,一脸无邪地问他:
“云生……这是……什么?”这般说着,还要将其送到鼻下嗅闻,李岫见状大窘,急忙抓住白晓谷的手腕,替他揩净。
轮回逆旅(六)
作者有话要说:冒个泡~这几天工作扎堆,网络也不稳定~泪~ 起身之后,李岫就这样衣衫凌乱地匆匆奔回了自己的房内,逃也似的。白晓谷见他这般羞赧,不明就里,于是便问询二杜缘由。
杜升就睡在白晓谷鬓间,一早便被李、白二人之间的动静吵醒,晨间的那些旖旎光景尽数落进他眼里。杜升年纪尚轻,面皮薄,故而一下子羞得小脸通红,对着手指支支吾吾道:“小可……小可不知。”
白晓谷转而又去问杜重,只见小老头儿正捻着虫须,笑得一脸暧昧:“你现在还不经人事,待日后修习了采补之术自然便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
过了一刻,李岫整好衣衫,面上恢复了常色这般才折返白晓谷房里替他穿戴完毕,又搀着白晓谷下了楼。韩湛早已在堂上候着,三人坐在案前用了点饼食点心,之后李岫同店家结了夜宿的账务,伙计从厩子里将马牵了出来,三人便出了逆旅。
此时已过辰时,外间雨虽然停了,可是天气有些阴霾,骑行在阡陌间,蒿草上的未干的水珠都沾湿了衣摆。
李岫对晨间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虽然同白晓谷同乘一骑却不敢再多碰他一下,倒是白晓谷早就将那事忘得一干二净,还像往常那样倚靠在李岫怀里,教李岫好不自在。
三人行将了一阵,不知为何,离那逆旅愈远,李岫愈觉得心中空落,仿佛有什么东西遗落在了那里,可是仔细点数,行李物件都携在身侧,并没有落下的。李岫转而去看韩湛,但见他眉间微蹙,一脸心事重重的模样,李岫只道他晚间没有休息好,于是这一路三人都没有再作交谈。
过了晌午,眼看又要变天,李岫自包裹中取出雨具,此时迎面走来一个行脚的旅人,李岫忙上前将他拦了,问:“这位先生,敢问距离洛阳还有多少路程?”
那人看了他一眼,现出一脸古怪的神情,嘴里嘟囔了一句:“还远着哪。”李岫听罢,以为来人也不甚清楚,改而又问讯何处有歇脚的所在。那人遥遥指了一个方向,答曰附近没有逆旅驿馆,需再行十几里地才能看到店家。
结果三日还未赶到旅人所说的驿馆,半途中又遭逢一场滂沱大雨,韩湛见山中有炊烟冉冉而升,李岫三人便直直往那处疾奔而去。
然后……
辨识不清的牌匾,不合时节的白花——看到眼前的一幕,李岫忽然觉得背后一记发寒,他失神地在逆旅门前凝立良久,才转过头对着韩湛喃喃道:
“表兄,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
“春草青青万项田……清明几处有新烟?”
杜升口中一边吟诵着应时的诗句,一边心不在焉地摆弄着被他当作罗伞的苜蓿叶子,杜重听闻,笑骂了一句“酸儒”,便一屁股坐到白晓谷的肩头,脱了小靴子就往外面倒水:“真是的,四月天怎么总下那么大的雨?这般赶路得什么时候才能到东都呀?”
“重重……”
杜重口中埋怨着,话音刚落便听得白晓谷呼唤,他重又套上靴子,仰起头只见白晓谷正一脸困惑地瞅着自己。
“怎么了?”杜重问,白晓谷遂嚅嗫着轻道:
“这里……我们来过……”
“什么?”杜重闻言四下环顾,但见堂间的陈设和昨晚借宿的那间逆旅如出一辙,不由地怔忡了一记,可很快又回过神,笑道:“不可能吧?难不成转了一天又转回来了?天下逆旅大同小异,这间兴许只是昨日那间分号吧。”
“可是,叔父……”一旁的杜升听闻,搁下苜蓿伞,指着那个在堂前忙碌的身影,道:“难道逆旅分号除了内里的陈设一样,连伙计也是一样的吗?”
杜重微愕,终于也察觉了些许不对劲,可他还是嘴硬道:“或许是双生子吧……”
白晓谷不知道什么是双生子,杜重便叽里呱啦解释了一通,趁着他絮叨的空档里,白晓谷转而望向身边的韩湛,但见他正微微蹙着眉头,似乎怀揣着什么心事。白晓谷也没有打搅他,过了一会儿想着“七日籽”们又到了该喂食的时辰,于是向伙计讨了一个盛着牛乳的小碟,看着它们排着队围在小碟边上吃食。
就在这时,一人走近前来搭讪,来者乃是昨日那个胡商穆仙客,白晓谷自然是识得他的,可是白晓谷却不明白,为何明明才刚分别,今次这穆仙客却装出一副初次见面的模样,一脸热络地重复着和昨天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白晓谷莫名地望着他,直到穆仙客再度提出要购得“七日籽”制成药酒时,白晓谷才回过神,捏起那些粉色的小东西,将它们全数塞回了豆荚里。
少顷,李岫下楼来,三人一道共用酒食,门口又传来一阵喧哗吵闹,白晓谷朝那儿探了探头,只见刚进来的一拨人正同逆旅中的客人争执着,为首的独眼汉相貌奇特,白晓谷还记得他是伙计曾说的贼首。
哪怕白晓谷再不谙世事,也明白了现在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乃是昨日重现,他不安地扯了扯李岫的衣袂,唤了一记“云生”,李岫转过头来温言问他发生何事,那副自若的神情,似是浑然不觉此间有何异样。
“三位,别来无恙乎?”
蓦地,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男音,白晓谷回首,待他看清对方的相貌,眸中灵火猛地一窒,他吓得立时蜷进了李岫的臂弯里,李岫却只道白晓谷畏惧生人,于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背脊,软语安慰了两声。
来人正是段珂,他淡淡地扫了一眼缩成一团的白晓谷,不动声色地挨着李岫的身边坐了下来。
李岫则莫名非常,他自认同来人素不相识,可对方面善,态度又如此熟稔,正以为是哪位多年不见的故交旧友,段柯却接道:“诸位忘了小弟吗?昨日我们还在此间举杯共饮呢。”
李岫眉头微蹙,他不记得有这么一段故事,加之此时嗅到了段柯身上的酒气,便以为对方只是个糊涂的醉汉,看了看对面坐着的韩湛,见他也是一脸不耐,于是便要将段柯支开,那段柯却在此时毫无预警地纵声大笑起来,将李岫骇了一跳!少顷,段柯才渐渐敛容,可唇边还是噙着一抹笑,对着李岫道:
“看来诸位兄台一定是记不得了,那么请恕小弟唐突,现在证明给诸位看——昨日你们曾经到过这里的证据!”
轮回逆旅(七)
看到李、韩二人面上俱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段珂指了指柜台前的那个伙计道:“李兄不妨现在就去问那伙计,此间逆旅是否名为‘黄泉逆旅’?他一定会如此这般回答……”
听段珂说了一通,李岫虽不以为然,可还是为他笃定的态度所感,于是依言唤来伙计询问,出乎李岫意料之外,那伙计的回话居然同段珂所述一字不差,李岫大奇,不可思议地瞠目对着段珂,段珂遂笑道:“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小弟不过是重复了他昨日的说辞罢了。”
“这也可能是你同伙计事先便串通好的。”韩湛沉声。
段珂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耸了耸肩膀,又道:“的确,只是这些还不足取信于人,那么请二位兄台容小弟再说‘预言’一些事罢。”言毕,段珂指着那虬须碧眼的穆仙客道:“待会儿这个胡商将会和一个孟姓男子起争执,届时他会请李兄作为仲裁。”
李岫一怔,虽然段珂所言之事十分荒谬,可是冥冥之中又觉得他不似寻常醉汉,于是偷偷睨了韩湛一眼,但见韩湛眉头微蹙,那神情似乎也是对段珂半信半疑。
接下来,就如段珂所言一般,穆仙客果然同人争吵起来,李岫上前去问缘由,反倒被穆仙客拉去作居中调停,而在这空档里,段珂又凑过来咬李岫的耳朵,只说再过半刻还会有位来客。
果不其然,半刻刚过门外便冒冒失失闯进来一个蓑衣人,乃是个自兖州送信的小吏——而小吏的形容打扮与段珂所言几乎分毫不差,这番再度印证了他的“预言”,教李、韩二人诧异非常。
“小弟并没有什么未卜先知的异能,只是还记得昨日经历过的种种……相信二位对这儿也有种似曾相似之感吧?”段珂这话教李岫心头一动,脑中似乎有什么一闪而过,可凝眉细想,却又记不清楚。
“……还不止小弟一人记得此间发生的故事呢,”不容李岫细想,须臾,段珂又扭过头冲着身后道:
“小弟说的不错吧……白兄?”
这话说的意味深长,配上段珂那副诡谲的笑容,教白晓谷眸中的灵难以自抑地颤抖了一记。
打从那晚被此人窥见倒映在金盆中的真身之后,白晓谷一直处在不安惊惧之中,再度相见,他却惊觉自己的那份不安其实不是别的,正是灵识被压迫的感觉。
白晓谷涉世不深,熟悉的仅有寥寥数人,可无论是李岫、韩湛还是罗瑾,他们都只是毫无异能的普通人——而眼前这个段珂却不知是何种身份,竟拥有能够压迫自己灵识的力量。
见李岫和韩湛此时因段珂所言转头望向自己,白晓谷愈发局促不安,二杜唯恐他在李、韩二人面前露了怯,忙一左一右地于耳畔安抚,白晓谷努力安定着骚动的灵火,求助般望了李岫一眼,李岫虽然古怪段珂对白晓谷的态度,但见白晓谷一脸无辜,心中顿时一软,便没了继续深究的意思。
“晓谷心智不全,宛若童蒙,阁下就不要为难他了,”一边说着,李岫径自护到白晓谷身前,冲着段珂插手为礼:“敢问阁下究竟何方神圣?”
段珂这回也不再装傻充愣,他抱拳还施一礼,重新介绍自己:“贫道段成雪,蜀中方士。”
李岫听罢一愣,没成想这段珂竟是个道人,可看他未戴黄冠,也不穿道服,全然不似修道人打扮,段珂看出他的疑惑,解释道:“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