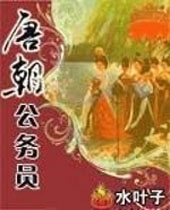唐朝有鬼之白骨变-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究竟在须弥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未成想,白晓谷此时也心不在焉,他正望着地上水洼中倒映自己脸孔怔怔出神。
灵识回到了当时蝴蝶幻境中。
白先生在他面前摘下了脸上那张面具。
而白晓谷看到他真容时,灵火竟难以自抑地剧烈颤抖起来。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白晓谷结结巴巴地问道。
白先生目光冷澈,凝视着白晓谷:“这就是我留在人间代价……是贪嗔痴欲伤疤。”
白晓谷听不懂他话,只是摸了摸自己脸,问:
“那我……会不会……也和你一样?”
白先生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
忽然,那异兽低声呜咽起来,似是在提醒什么,白先生低喃了一句“我该走了”,尔后又冲着白晓□:“以后,你要好自为之。”
话音刚落,那一人一兽化作二缕轻烟……
“你在看什么?”
就在这时,有人无声无息地靠近,教白晓谷猝不及防,他吓得浑身一个激灵,身子朝前一倾,险险就要踏进水洼里,来人猿臂一伸,将他稳稳抱住。
白晓谷扭过头,看到李岫放大俊容,不知为何,总觉得他这副神情竟和幻境中少年“李岫”如出一辙。
白晓谷冲着李岫眨了眨眼,确认般探出手来,指间碰到了李岫胸膛,可这一回,却没有再穿过去。
眼前这个人并不是白先生记忆,而是有血有肉李岫。
“怎么了?”李岫有些疑惑地问道。
白晓谷摇了摇头,李岫遂粲然一笑,捉起白晓谷手,朝着内室走去。
此时谁都没有发现,有一只蝴蝶,扑扇着泛着银辉翼翅,渐渐消融在老榆下斑驳树影之中……
97、端午鬼话
端午即至,天气炎炎。
这日县府放假,李岫不用去衙门堂值,便在宅中张罗起来:门前挂了菖蒲和艾叶,侍童也被差去东市购置角黍和雄黄,以供节日所需。
东厢的房门此时大敞着,李岫瞧见一个白色的身影正伏在案前摆弄着笔砚。晨间自己新教了白晓谷几个字,看模样是正在专心致志地临帖,李岫此刻也不想进去打搅。
闲极无聊,李岫忽然记起旧时曾听相熟的金吾卫说过,端午时节,宫中贵人之间有个时兴的小把戏,乃是以小角造弓,去射粉团和角黍,中者得食。
李岫琢磨着想给白晓谷也造个这样的玩物,于是便在中庭置了一席,取来工具和材料,动手做了起来。
约莫半个时辰过后,小弓雏形初现,李岫的额上却沁出不少汗液。
白晓谷搁了笔从东厢出来,见李岫这般,便拾起衣袂替他揩去额上渗出的汗液。李岫回过神,冲着白晓谷展颜,一伸手便捉住了白晓谷探过来的手。
白晓谷的手又滑又腻,毫无胼胝,李岫攥着一时竟不舍得丢开,这时脸颊又被一个冰凉柔软的物件触及,李岫一怔,侧过脸,发觉原来白晓谷正伏在自己背上,伸长了脖子亲昵地啄着那儿。
这记童稚的动作惹得李岫忍俊不禁,他猿臂一伸,搂过白晓谷的腰肢,将他轻松地打横抱起。虽然已朝夕相对将近一年,白晓谷身子仍似最初那般轻盈地不可思议,李岫不禁好奇:他每天吃的东西究竟去了哪里?
就这样被李岫置于膝上,白晓谷又凑过脸去香了香他,亲吻恰好就落在唇边,李岫面上微红,倒也不再抗拒。之前小桃在家中,他不便同白晓谷太过亲近,现下趁着小桃去了东市购置家用,难得偷得这片刻温存时光。
李岫又在中庭的席子上摆了个案几,取来粉团置于上面,正想教白晓谷怎样使用小角弓,却见他不由分说抓了点心就囫囵塞进嘴里,李岫哭笑不得,却还是将白晓谷揽至到身前……二人正耳鬓厮磨间,忽然听得身后传来熟悉的男声:
“哎呀呀,青天白日的……李大人你就不害臊吗?”
李岫回过头,看到罗瑾正环胸立于身后,他还是一身黄冠道服,只是臂上多悬了一串五色丝缀成的厌胜铜钱。
“怎么是你?”李岫见罗瑾这个时候不请自来,有些愠道,他松开了白晓谷,一边将其藏于身后。
“啧啧,你只顾着和自家宝贝儿亲热,难道就忘了好友我吗?”罗瑾嘟起嘴,自袖中取出一个铜盒:“你送的这个匣子我才摆弄了几天,里面的蝇虎就都不见啦。”说罢,就将盒子丢予李岫,李岫揭开一瞧,里面果真空空如也。
“赤蝇虎们大抵是跟着卢钩父女回浐水去了吧。”杜重这般说着,顿了一下接道,“子腾那孩子现在也不知怎样了,他不在身边,老夫还真是有些寂寞呀。”言毕,还煞有其事地长叹了一声,白晓谷见杜重垂头丧气的,便伸出指头安慰般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圆脑袋。
话说自从红夭和杜升一见钟情之后,两只小虫便相携回了蚍蜉国中,不多时,便有皇太女招驸马的喜报传来,杜重和白晓谷虽说乐见其成,可身边陡然少了那只应声虫,总觉得这间小宅又再度变得冷情起来。
“今日重五,我在红袖招设宴……你也带晓谷一同来吧。”罗瑾邀道。
听闻,李岫有些犹豫,自己虽然常在平康里进出,却从未走马章台,涉足勾栏教坊,而白晓谷怕生,前几日去回春堂时他还被张医生主仆吓到,于是刚要婉拒,身后却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袖。李岫一愣,转过头,只见白晓谷翕张着嘴,道:“红……袖招?”一副确认般的口气。
李岫点了点头,解释道:“那儿人多,三教九流汇聚,我们就不要去了。”
谁料白晓谷却摇了摇头,道:“我……想去。”
白晓谷至今仍记得自己初入长安城时,曾在红袖招居住的那一段时光。当时胡殷紫尚未被道士收走,她还教过自己许多怎样为“人”的根本。
提起红袖招,白晓谷便想到胡殷紫,想念着那些被她点着额头骂傻东西的无忧日子……这般眸中的灵火便又开始不自觉地轻轻摇曳起来。
李岫哪知白晓谷的心思,只道他忽然转性,于是向罗瑾应承下来,入夜之后便携白晓谷前去赴宴。
※
晚间,李岫同白晓谷依约而至,进了红袖招馆中才发觉,原来今次罗瑾不光邀了他们,座上客还有另外两人。
“表兄。”李岫同一边同身着元服的韩湛招呼,一边望向他左席的男子——来人一袭青衫,面白无须,正是自王顺山骷髅一案之后,多日不见的长安尉。
“薛大人,别来无恙。”李岫冲着薛矜拱了拱手,对方还施一礼,口中呐呐,不知怎的,他眼下青黑,竟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
“方才我在东市闲逛,巧遇薛少府,就约他一道来了。”罗瑾解释完,又咬着李岫的耳朵说,“这厮印堂发黑,大概最近又见鬼了,嘻嘻……”一副幸灾乐祸的口吻,似乎是专门为了取笑薛矜才将他请来一般。
李岫没好气地白了罗瑾一眼,转而又同韩、薛二人寒暄了数句,这才拉着白晓谷按次落座。
酒酣耳热之际,罗瑾又唤了一名女伶上来弹唱。
那女伶怀抱琵琶袅袅婷婷地上前冲着众人作礼,罗瑾在一旁介绍道:“姑娘名唤夜来,琵琶弹得极好,诸位有耳福了。”说罢,还亲热地将她招至身旁。李岫知道“夜来”乃是罗瑾的新欢,今次却是头一次得见,果然生地明眸皓齿,颜色妩媚。
夜来坐下,捻轴拨弦,不多时琵琶嘈嘈,莺声婉转,果真动人!一曲《临江仙》唱毕,罗瑾自己也荒腔走板地哼了一阙,歌完还道:“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夜来收拨,笑曰:“奴家技拙,教公子赞谬了……若是比起禁中的念奴姑娘,奴家还差得远呢。”皇帝御前有一倡女名唤念奴,相传当她啭声歌喉之时,声出朝霞之上,钟鼓笙竽的嘈杂也无法遮遏。
罗瑾摇着头,道:“两人各有千秋,你又何必自谦。”言罢,就欲抚上夜来的肩头,却被她不着痕迹地抹了开来。
罗瑾摸了个空,有些讪讪地挠了挠鼻尖,他百无聊赖,冲着众人道:“不知诸位有什么余兴可供消遣的?”
李岫回说:“我们之中哪个有你鬼主意多?”
罗瑾眼珠骨碌一转,“嘿嘿”诡笑了两声,道:“拇战粗鲁,酒令俗套,不如咱们换个新玩法吧!”
提出“新玩法”之后,罗瑾先引众人来到二楼,命人撤去了酒席,熄了灯,而后每人发了一根蜡烛,教他们分别点上,须臾室内重又亮敞起来。
“在古时,五月是凶月,五日乃恶日,端午之所以要挂菖蒲艾叶,饮雄黄就是为了驱祟辟邪。”罗瑾一边说着,将自己的蜡烛置于案前,如豆的烛光映照着他的脸庞,白惨惨地有种说不出地诡谲。
“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精魅鬼怪亦如此,据说这天晚间若是论及鬼神,它们便会悄悄地混到人群中来……”
98、端午鬼话(二)
众人大都同罗瑾熟稔,素来知道他秉性,所以当他故弄玄虚之时,大家神色如常。
惟有薛矜略略有些不自在,他嘟着嘴埋怨道:“如此佳节,却讲这些,难道不扫兴吗?”可能顾及今次乃是罗瑾做东,他的声量并不大,但却足以教座中所有人都听得见。罗瑾挑了挑眉,忽然不怀好意地笑道:“坊间常有薛少府的传闻,今天您既然本人在此,何不道一段故事让我们长长见识呢?”
“我可没什么好讲的!”薛矜说着,像是受气氛所感,他紧张兮兮地四下张望了一阵,忌惮地阖上了嘴巴,也不知是不是光线的关系,此时他的脸孔比平时又白了几分。
罗瑾明白薛矜惧鬼,却不想穷追不舍惹恼了他,于是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俏皮话,这才转回正题上。
“我备了几只酒筹,上面预先写了六个号儿……诸位就按酒筹上的次序每人讲一个故事,必须是亲身所历哦。”
罗瑾说完规则,为表公平,又将酒筹展示给众人观看,而后就把它们全数灌进一个小布袋里,教众人抽取。
“我也要……抽吗?”去摸布袋之前,白晓谷扯着李岫的衣摆怯怯地问道。李岫知道要白晓谷讲故事,未免太为难他了,正要说些什么,罗瑾却抢先一步道:“谁都不能例外,不然就要挨罚哟!”
“罚什么?”李岫问。
“烈酒三盅!”罗瑾比着三根指头不客气地回说。
“不妨事,”李岫转过头附在白晓谷的耳畔轻道,“到时候,我来替你受罚。”言罢,他还在案下偷偷地捉住白晓谷的手收进了大掌之中。
“李县尉甜言蜜语的功夫渐长呀,”杜重自在白晓谷耳窝里拱出肥嘟嘟的身子,伸了个懒腰,又道:“就不知道酒品如何了。”
杜重的话李岫自然是听不到的,而众人各自摸了酒筹,摊开一瞧,次序如下:
韩湛居首,罗瑾次之,夜来第三,薛矜第四,白晓谷第五,李岫最末。
发觉自己和白晓谷排在后头,李岫松了一口气,而韩湛不曾料到自己今次居然要打头阵,他一向不善辞令,不禁为难地蹙了蹙眉。
“韩将军可有什么故事?”罗瑾一边问,一边好奇地睨向韩湛的右臂。他曾数度从李岫那儿听说过韩湛右臂上的玩意儿,但一直无缘得见,所以每回见着韩湛都心痒难耐,恨不得扑上去扒了他的衣裳,好好端详一番那世上罕有的人面花……这般妄想着,罗瑾咽了咽口涎。
或许是洞悉了罗瑾的歪念,韩湛本能地以左手护着右臂略略侧了侧身子,未成想里面的人脸隔着布料感受到他指尖的碰触,本能地张开小嘴轻啮那儿,韩湛浑身一僵,硬生生地重又将左手搁回膝上。
只是被这么咬了一口,韩湛脑海中蓦地灵犀一闪,他忽然忆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桩奇事……
※
自从臂上生出人面花来,韩湛一直闷闷不乐,若不是念及它维系着自己这条性命,有时甚至恨不得将它生生剐去。好在这人面花除了有些贪嘴儿,喂食之际必须宽衣解带有些不之便,平时它并不聒噪。
韩湛渐渐掌握了它的习性,人面花虽不挑食,却也偏爱温软甜腻的吃食,尤其喜食蜜枣,吃完之后它还会把核儿乱吐,然后像个淘气的小童般发出“咯咯”的轻笑,韩湛固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
又过了数月,对着这朵奇葩韩湛习以为常,只是时近清明,晚上就寝之际,人面总是嘤嘤啜泣,有时甚至吵得韩湛无法安眠。
从东都归来之后,人面虽然不哭了,可不知怎的,臂上却奇痒难耐。一日韩湛晨间起身,赫然发觉人面的上缘又长出一颗黑点,无论如何揩洗都去除不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黑点渐渐长地突出隆起,宛若疖子一般。而每当去碰那凸点,人面花便会莫名地咯咯发笑,瞧在韩湛眼里,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难道又要长出一朵花儿来?若是这东西生地浑身都是,自己岂不是无法出门见人了?
怀着这样的忧虑,韩湛又惴惴地过了两天,直到第三日,那疖子忽然变成了乳白色,轻轻一碰便自行脱落了。
手臂不再发痒,一切如旧,韩湛不明就里,只是回想起自己最初返阳之时,罗瑾曾言(这里的罗瑾是指白先生幻化而成的)人面花每年都要开花结果,莫非这白色的疖子就是它的果实吗?
韩湛捏了捏疖子,只觉得肉呼呼,软中带韧,而一想到它是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不由地浑身起了一层鸡皮,韩湛嫌恶地将它信手丢进院中。
之后人面花再无异状,韩湛很快便将这事抛到了脑后。
就这样又过了一旬。
四月望日,晚间,韩湛在院中对月独酌,正喝地有些微醺,忽然觉得有人站在身后,最初他以为是府里的小厮仆僮,并不以为意,可是又饮了几杯,来人还立在原地,韩湛忍不住回过身看了一眼,不由地被吓了一跳。
那是一张白生生的怪脸,足有簸箕那么大,五官很小,扭曲着挤在一块儿,它的躯干和四肢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