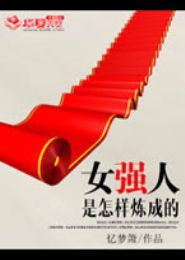风颜录(女强)-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何做,随心而已。
◇◇◇◇
皇帝的仪仗浩浩荡荡行在长街,身后是征战归来的十万大军。街头人流涌动,欢呼赞叹的声音响彻震天。
皇帝的车辇遮的严实,只有透过那偶尔随着晃动才翕开的车帘,才能窥的一丝人影。
帝少姜已经换下盔甲,夜般黑的长袍上似乎还残留着血腥的味道。
平坦的大道上,马车时而也会晃动,外间百姓夹道欢迎,这里间却有几丝凝滞的味道。
帝少姜睡着了。
这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即是用着凡胎肉身,那么终有疲倦困顿的时刻。
只是奇怪的是,这一睡,帝少姜却做起了梦。
重回人世二十多年,除了于生死极限上梦过往事一回,她从未有过梦境。毕竟是不同其他人,绝对的掌控也就意味着会失去常人入睡才会有的混沌或是思虑。
果然,这副躯壳还在试图夺回属于‘人’的特征。一旦她精神略微疲惫松懈,某些印象深刻的画面或是与之相关联的幻象便会闯了进来。
说是梦境,其实也不过是前生另一场旧事。
她从一场重要的宴会中撤身归来,管家在门口迎接,恭谨的报了晚饭的菜色和安排,在她点头表示无有异议后,临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恰似无意的补了一句。
“霍公子在花园里晒了一下午的太阳,这会儿还在,需要叫人去请吗?”
早春日头退的算早,这会儿天边也只有一线余光了,园子里的灯都开了,晒太阳的人却还不归家。
秋宅的女主人想了想,说了一句不必,便亲自到花园里去看了。
霍希坐在玫瑰架下垫了绒毯的椅子上,身上盖了一层毯子,远远看去,安静的像一副雕塑。等她走近去看的时候,这人原来是睡着的。
也许是阳光实在和暖,日子实在悠闲,这个在秋宅无所事事的男人心无顾忌的睡着在花园里。身上的毯子大概还是某个倾慕他的女佣偷偷盖上去的。他实在有一副很好的面孔。
她的目光落在这张精致迷人的脸上,看那晕黄灯光打映出的轮廓显出无限的安宁美好。离他一步的位置,她突然走了一会儿神。
这实在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那瞬间,她居然觉出了几分自己的茫然。
她弯下腰抬手,有些惘然地想触碰这张脸,却在最后关头蓦然清醒,讶然顿住。
“差一点点……”
“这样都没办法打动,看来是奢望了。”
他似要清醒,秋川困扰地摁了摁眉心,冷然一笑。
“分量不够也是白费心神,妄动的话,恐怕结局是我会杀了你。”
“杀人无数,却不想杀你。这一点,还是不让你知道的为好。”
她悄无声息的离开,园子里安静的没有人声。
只是一时情迷的话,大概不足以颠覆她那颗厌世冷漠的心肠。那还是不要尝试了。
是这样想的吧,当时?
帝少姜蓦地睁眼。
某个胆大包天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爬上她的御辇,试图触碰的手正尴尬的悬在她面前。
“你睡着了。”陆敏青妖然一笑,成熟风情艳光无匹。
帝少姜按了按太阳穴的位置,外间安静悄然,队伍很显然已经停顿。陆敏青凑上来,突然情绪不明地来了一句。
“那个十一皇子,孤皇……是他对不对?”
“真有本事的人。”陆敏青眯着细长的眼感叹,细碎的流光闪烁于双眼,里间的忌惮和厌恶藏得很好。
“的确。”帝少姜并没有怪罪他的胆大妄为,撩开额前垂落的发,目光意味不明。
没有本事,又怎么配她当初把秋家留给他?
☆、冤冤相报
“你果然在这里。”
年轻男子逆着风走来,高冠博带,眉眼俊逸的不似凡人。
面着墓碑而坐的男人却已沧桑垂老。他原本也有一张出众不凡的容颜。年轻的时候身为剑客也扬名一方。
那时候他有自己的庄园,娶了追逐已久的女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尽管孩子不是他的骨肉,但这不影响他将来对他视如己出。
一生之中所有的愿望似乎都已达成。却又一夜之间失去的彻底。妻离子散,容颜尽毁。
鬓白的男人以指勾勒碑上的刻纹,试图从那字里回忆起那女子的模样。她没有机会老去,即便再过二十年,留在他心底里的依旧会是那般年华美貌。
世人只记得当年飞花楼里艳名远播的丽姬,可他眼里心里的,一直都是初见时董氏庄园里孤世绝立的三小姐。
不肯相信真心,却又轻易被别人口里的‘真心’所骗。风尘退散终究将目光施舍与他时,时光又太短,挥挥手只留一场空梦般的悲壮仇恨给他。
花渐离早就已经死了。世上也再没有玉溪公子这个人。
“你杀了他?”陈年的伤口纵横交错,脸上斑驳不忍睹视的人没有回头看走来的年轻人一眼,恍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这不是你半生所求吗?”那一眉一眼都似多情的年轻公子回答,眼神投注到他未遮住的白石墓碑,声音模糊地像要散在风里。“毁了自己的脸,将她的一个儿子送给颜成,抛弃故国北上,从一介马夫爬到孤措亲封的贴身带刀侍卫,不就是望有朝一日为惨死的妻子报仇吗?”
一动不动的人没有回答。
年轻公子笑,“你为什么不笑?是怕她怪责你袖手她的骨肉相残吗?”
“当年送给颜成的孩子……我知道他的名字。也曾窥视过他。”花渐离脸上的肌肉随着嘴唇的起合动着,容貌煞是可怖,但眼神却是没有触动的,“颜烬阳是颜成起的名,我不知道如果她活着会给你们什么样的名字……他长得和你一模一样,无衣。”
“也许她早就不等我了,就算还等着,我这样去见她,她也不会认得我,就算认出了也只会恨,不过……你既然杀了孤措,对我来说,那就好了。”
空气中的血腥味并不难闻,但足够浓重。
迎风而立的年轻男子忽然笑出声,依旧是浅淡温文的口气。
“就这么确定站在你面前如今名为‘孤皇’的我还是无衣?”
花渐离猛然睁开沉重的眼皮,似是一惊。那人在身后不紧不慢地笑,“你真的觉得,那晚在沂水河畔,无衣能杀得了我?”
“我不是无衣。颜烬阳才是我原来的名字。”
“居然……”惊愕之下,花渐离几近失神,等凝聚起涣散混沌的视线再看了一眼那墓碑,他恍惚中竟是见到了梦里才朝他笑盈盈走来的伊人,某种喜悦油然而生并狂啸着蔓延了每滴血液。
“那又怎么样呢?”狂喜如斯已经顾不得其他,花渐离释然一笑,缓缓闭上眼,手上抓紧的匕首却又朝身体里刺进几分,血流愈快,他的心境反而平和起来,“于我而言,活下来的是谁已经毫不重要。孤措死了,而她的孩子抢走了仇人的一切,还坐上了那个位置……至于我,马上就能见到想见的人,就算下一秒要到地狱里去赎罪,又有何惧?!”
颜烬阳微怔,镜花水月一般不露真实的眼微晃波光。他无声地扬了扬嘴角,一刻后转身从容离去。
安静的天地里,风声呼啸。
帝少姜,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你?
◇◇◇◇
帝少姜归京第三日,紫宸帝卿病倒。
“你往棋子上抹了什么?”谢长安问陆敏青。
洛歌辗转多年终等得谢长安的点头,今次谢大小姐随军归来,女帝已金口允诺会亲自主持两人的亲事。但归京的帝少姜并不夜宿宫中,除了一次早朝,宫中消磨时光也仅有两次与幽篁对弈。
自成为帝卿,司命的弟子身体居然一日不如一日,损耗来得蹊跷。女帝不在京中,他还能勉强度日,一旦与那君临天下的人有了接触,恶化总会突然到来。
谢长安看着眼前容貌惑人心肠却越发歹毒的男人,实在无法明白皇帝为何再三地纵容。就因为这张出表的皮子吗?
多少人看不出帝卿病重的隐因?如洛歌,斯影,秋禀生这类的聪明人难道会不知道?却无一例外地故作不知。
死了一个出身不高分量轻微的帝卿的确没什么大不了。且,幽篁还出自帝少姜痛恨的太渊。
但这样明目张胆的妒忌和毒害,实在过于卑劣。
谢长安爱为人打抱不平,陆敏青却轻笑回应,眉眼间的瑰丽和轻屑几乎不做遮掩。
“谁要让他接近不该接近的人?”他一只指尖轻按眼角,嫣红菲薄的唇徐徐牵起,不紧不慢地调子显得慵懒随意,“少姜本身百毒不侵,但对他来说,却是见她一次,毒就愈深一分,离死更近一分。就算我不用这种方式,少姜对于别人来说,不就是毒一样的存在吗?他每见她一次,我心里的不快活就会多一分,等到那怒气积累到喷薄而出,我难道就不会将他折磨至死?这样慢慢的死法,算是我宽容多给了他时间。”
“你太肆无忌惮。以为别人都一无所知吗?”谢长安愠怒。
“那样怎样?”陆敏青满不在乎,“就算我想杀了他又如何?你以为少姜会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谁不知道她对太渊一门有多憎恶,就算我现在杀了那小子,她恐怕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反正我陆敏青横行无忌心肠歹毒,杀个空有帝卿名头的小子又算得了什么?还是……你真以为顶了个帝卿的名头,他就真是她的男人了?”
最后一句话出口,公子敏青的面容越发夺目。
谢长安从他更显愉悦的表情中捕捉到了什么,突然笑,“果然是无理的嫉妒。”
“你最愤怒的不过是主上不近情爱罔顾你痴心一片,却能轻易将虚名施舍给别人。主上根本不在乎你……即便你试图杀死帝卿的行径,也得不到她半点或恨或怒的回应。你得不到她一丝一毫的目光,这才是你真正失意彷徨的地方。我说得对吗?”
陆敏青笑,凄惶中仍是那种披着艳丽迷人的毒蛇吐信般的危险刻毒。
“你说的不错。陆敏青就是这样的人。”他眯着眼答,像日光下假装匍匐松懈的野兽。
☆、白塔
帝少姜归京一月后,帝卿病态缠身,卧榻不起。
秋府却正喜事。
秋家独苗,禀生少爷在老婆身边守了一夜,听了一夜产妇的鬼哭狼嚎,总算等到自个儿儿子出生。
这边高兴劲刚要掀起热潮,全府雀跃,小公子洪亮的哭声中,秋烈乐得一把胡子都快翘上天了,门外却传来通报。
皇帝上门来了。
下人的声音刚落,满屋子的人就僵了一僵,一盆水泼下来似的灭了欢喜。连刚刚还哭闹着的胖婴儿也突然安静下来,在亲爹怀里划着手足。
继杀人不眨眼冷酷专横的好名后,帝少姜三个字又多了小儿止啼的功效。
秋烈寻思着皇帝上门庆贺臣子添丁这由头过于小题大做,颇有几分忧虑。女帝在众人的恭迎中进了秋府,产妇房外先是让人颁了一道旨意,将秋少夫人封为清河公主,圣旨末了一句是‘将来一切与朕同享’,莫大的荣华来得莫名其妙。
这旨意下完,连里间被人丢下的产妇都觉得一头雾水了。既然是贺喜的,好歹该和喜字之源沾点儿边。突然来个册封皇帝是想干什么?桐夕按住疲惫听着外间动静。
君臣之礼那一套走完,秋烈实在忍耐不住,扫了一眼旁边若有所思的儿子一眼,正想说话,没成想帝少姜接下来的行为更是莫名。
女帝悠悠走到抱着小公子的奶妈面前,伸出手拨开襁褓淡淡然看了一眼,饱含估量的神色一划而过后,转过头眼神落到频频皱眉的秋禀生身上。
“令子相貌倒是平和。”女帝突然发了句话。
用忌惮来形容秋禀生的态度最是准确。秋老将军毕恭毕敬地走了承蒙圣眷的虚礼,秋少爷眉宇间的不愉却是越来越明显了。
帝少姜又伸手逗了逗婴儿软绵白嫩的脸,低低笑了一声,眼角余光里一屋子因为圣驾迫不得已压下喜庆的人,最后再看了一眼不得不丢开刚生产的妻子来迎驾的秋少爷,后者的不满已经明显摆在脸上了。
“名字可有选好?”皇帝算得上和和气气地朝秋老将军问了一句。
“回禀陛下,尚未。”
女帝退开一步,抱着孩子的奶妈顿觉松了一口气。“甚好。”她似笑非笑地挑了挑唇,“朕赐其重泽二字。”
“一夜忧劳,早朝可免。”一身黑衣的皇帝扬了扬手,眼角眉梢凝绕终年不散的冷意,“秋禀生,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秋少爷挺直的背突然僵了僵,隐忍地垂下头。
“臣不敢。”
皇帝一来,连他给儿子起个名的权力都给顺走了,秋少爷心里愠怒不少,却也只能自我安慰,好在秋重泽这名不差,听起来比老父一直琢磨着的‘秋报国’‘秋破虏’‘秋大壮’云云的要有文化有内涵上档次的多。
但还是有那么一些不甘心。即使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也不能叫自由。但凡头顶上还有一个人压着你,限制胁迫情不得已也不会只是一两点。一杆枪,就算打上‘御用’的标签,也改变不了它身为工具的事实。
秋禀生克制的垂眼。
女帝的背影十分冷落洒脱。
◇◇◇◇◇◇
六月。新帝广兴土木。
西郊建塔九层八角,汉白石为之,举高九十丈。塔檐龙凤飞延,挂铜铎,每逢风过,清音不绝。
从最顶端的一层俯瞰,帝都景色全收。
这是女帝登基以来为自己做的最奢侈的一件事,动用巨大的财力物力,只修了这么一座华而不实的白塔。
残阳如血,却映的白塔更见皎洁绝立。
帝少姜一身青衣盈然,慢慢自塔中石梯登上。而后于顶层殿中静立。
第九层。垂鲛绡缀鸣铃,轻纱随风轻摇鸣铃声泠泠,帝少姜仰头,视线久久驻留天际一端。
直至夜□□临,星河遥挂。
九十丈。当仰望之时,无数人惊叹手可摘星辰地宏伟,实际与那云霄依旧是参商永隔的距离。
帝少姜振衣坐地,身后鲛绡隔着纯白的轮廓不动,塔上风大,偶尔吹开一缝,那后面的人便露出了痕迹。
安静地,苍白地,坐在轮椅上。
“你看到了什么?”女帝忽而出声,似有几分寂寥的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