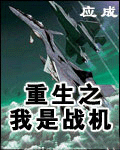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你的终生黑-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家少爷”。
“他家少爷”自那次洗了一回碗之后,他就再也没让他洗过碗。后来老方又来了好几次,要煮煮那骨头汤给小顾补补骨头什么的,每每饭后这小顾竟还屡屡请缨,要亲身上阵洗碗。把方杰吓得直接就拦下了他,说碗就不用他洗了,他就好好待着吧。他竟然还不明白为什么他屡次请缨,却屡次被拦阻。后来方杰被他问了后,才教他怎么洗碗,他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方杰问他一个人在国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说听说但凡出国的人,独立生活能力都是不错的。他就回答说他并不独立生活,说他买在那里的房子是空着的,他仍旧住寄宿家庭,包早晚餐,午餐他就在外面吃。
方杰一听,反正有钱人的世界他不懂,他也不再细问了,只是现在教了他怎样把一只碗给洗干净,免得以后他又想在他爸老方那里博取表现,结果到最后的罪却都得他来受。
方杰十一点半时已经眼皮子耷拉着,两眼眯缝着,顾孝成一看他这样就是已经困得不行了的样子。于是他下床去关了顶灯,他们没有床头灯,顶灯的开关在入门的门框边上的墙上,每回还得人下了床去关。
他回到床上时,动作是极轻悄的,借着窗外月色,凑近了看向方杰的脸,他是有点想就这样将脸无限地凑近过去,可是终究没有这么做。他确定他已经昏睡过去了。
他最近学会了洗碗,方杰亲身示范给他看怎么去洗碗,什么洗洁精、洗碗擦的,还有那些白色细密的泡沫,他回想了一遍当时方杰教他时那脸上一脸鄙弃的神情,仿佛在说“你个生活白痴!竟然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
方杰现在正平躺着,刚刚顾孝成去揿顶灯开关时,他就把上身披的外套一除,搭在他那个灰白色调的冷扎钢板“床头柜”上,然后就这样像条光滑的鱼似地张着尾鳍滑入被中,就这样先睡去了。
顾孝成看了一会儿后,也索性把自己的手机与方杰放在被上的手机都放到了写字桌上。方杰不会在睡觉时把手机放在身边的,但他仿佛知道每晚都要比他晚睡一会儿的顾孝成是肯定会帮他把手机由他身边挪走,所以这几晚开始都不再自己把手机放远了,而是随手往被上一撇,而往往它就微微陷在他俩睡的被子的中央那个凹进去的缝里。而顾孝成就略将被子拎一拎起来,将那手机显出来,再与他自己的手机一并放远。
这晚上可能到了一点多时,方杰难得被尿憋醒了,他们这晚上吃的那家外卖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咸了还是味精重,晚上时多喝了几杯水。明明睡前上过几次厕所了,以为都排空了的,却没想到大半夜了还被尿憋醒。
而他十分地不想下楼上厕所,往往夜半被尿憋醒了都会有一种倦意,就想赖着不去,仿佛这样就能将尿憋回去,憋不见了,而他又能再接着睡似的。他在一片“月朦胧,鸟朦胧”之中就这样憋着。所谓“月朦胧”倒是肯定的,他不用侧身向窗口那边看也知道外面有月色;而这“鸟朦胧”就没可能了,按说这小鸟儿早该睡了,哪来的鸟?
可他在逐渐清醒之中,像是真地听见一阵“鸟语声“,可这又与他平时在这开发区的街上听到外国人说的鸟语不一样,他再努力在大脑的一片浑茫之中着力分辨着,好像隔壁那几个值大夜班儿的女的之中有谁又把窗户牙开了,又有那种声音传出来。也不知听谁说的,说她们那边二楼是装修得很好的,隔音材料最足,楼上隔成了八间,有的是有窗的,有的是无窗而只有排气扇的。
而问题是,分辨清了这“夜来鸟语声”究竟是什么来源之后,他又觉得身上怪怪的,他觉得自己的两瓣臀正被什么东西抵着。他忽然大气也不敢出,眼也不敢睁开来,他就觉得那东西在他身后磨蹭着,他过了一会儿之后心里“大呼不妙”,心里想着:xxx!不但夜来闻得鸟语声,还真被别人的x抵着,这老天爷是在玩我不是?
他憋着一口气,非要看看身后那贱人又要做出什么不可告人的贱事来!而那人开始轻声细气地扒他的内裤,手先伸进了后面来抓了两把,跟揉搓着什么白面馒头似的。方杰这时已经忍不住了,他猛地跳下了床,转身后还不忘把内裤腰往上提了一提,大声咄叱:“我就知道你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变态!我心里面最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变态!你竟然在这个晚上就要来强^奸我!没有想到你!你!”
他本以为顾孝成会在受惊之后把他那副经典小媳妇脸又再显露出来,哪知这时他竟然在脸上显现出一种理所应当。他之前确实怔了一下,镇定了后竟然说:“你没听隔壁那叫的,正常男人都会硬,你怎么就不硬?足见你不正常,你看看你,对女人的□□声一点反应也没有。”
方杰竟然一句争辩的话也说不出来,哑立当场。也不知道是被刚刚的情形惊呆了,还是真地在逻辑上反驳不出什么话来。
而顾孝成就丢下一句:“你睡吧,我去去就来。”方杰知道他要下楼去做什么事。
他又躺进了被子里,这一次左想右想都觉得自己背对着顾孝成睡是相当不智且十分“惊险”的一件事。于是他将身体转向了东面,也就是朝着顾孝成的那一面。
过了有一段时间,方杰也不知道具体是多长的时间,他只知道这段时间本来就不短,再加上他心里如同擂鼓一样地紧张,就显得那个时间特别地长。顾孝成终于回来了,看到方杰朝向自己这一侧,他竟然十分坦然地掀了被子就躺回了原处。
方杰睁开眼,眼里荧荧地晃动着两圈光晕,更有点像是一双伏在草丛里观察身周动静的夜行性动物的眼。顾孝成躺着,身上沾染了一些体^液发泄后的气味,方杰闻得出来——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那味道真地那样明显地存在,可是他却感受不到他“事后”的快意,总觉得他还有些什么情绪正憋着。方杰忽然想到之前他那只伸进他底裤的手,有着滚烫的手心。静默了许久,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还憋着尿,于是也下楼小号,回至二楼后,也还是静默。
两个人这晚上直到再次入睡前都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白天时,方杰先起来,下楼洗漱时,才注意到顾孝成把他那浴巾上的红心又公然地叠在了最外层,竟显得像是在公然挑衅一般,显得那样地招摇。
方杰说是说一直都有些在顾孝成对他做的某些事情上面疑神疑鬼的,可是他仿佛一直都知道着一些事情。他这些年来是怀疑过,无从确定过,因为顾孝成从来没有说明白过,就连昨天晚上都那样了,那人还是用了听起来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借口就把事情给撇清了。可是他心里仿佛一直都知道着一些事的,可是他没有勇气真地去叫顾孝成把事情给他解释清楚。或许是怕顾孝成还是找些借口来撇清,那倒变成像是他在自以为是地误会别人,那好像会很没有面子。
他这天一整天都没有跟顾孝成说话,他心里除了怀疑,可能还有一种生气,他觉得顾孝成凭什么让一切都这么不明不白的,有种就把话跟他说明白。现在这样让他既没有办法就此明白地拒绝,也没有办法就此明白地接受——当然他心里是认定他自己肯定不会明白接受这种关系的。
当天晚上,他洗了澡,坐上床后,又是不说话,看手机。一旁的顾孝成也一样。
可看了一会儿后,才十点十几分,顾孝成忽然什么也没说,直接下床。方杰以为他要下楼小号,哪里知道他直接将房间顶灯关了。
方杰刚想问他怎么这么没礼貌,竟然不用问过他这个房主人的意思,就单方面决定把灯关了。顾孝成折回时,直接将方杰手里的手机抽走了,与他自己的摞了放在写字桌上。
他转身打开写字台侧边抽屉的第二层,由里面拿出一管东西,坐上了床。方杰这时候胸腔里好像又开始刮龙卷风了,心脏被狂刮得訇訇作响,而脑壳里也像是糊上了一层沙子似的,开始不清醒了。他潜意识里是觉得没什么好事,却还是下意识地看了顾孝成手里的东西一眼,又是那种正反都是洋文的东西,他也看不懂是什么。他只是知道顾孝成把那管东西拧开来,上面那个铝的封纸还没有被揭掉。
顾孝成一句话也不说,一脸面瘫地在他面前把那个铝纸的封口给揭掉了,往身后地上一撇。
而接下来,方杰就跟做梦一样,整个人被顾孝成牵着鼻子走。他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反抗。昨天晚上还像个抗争性极强的勇士似地跳下床,反抗了一回,喊打喊杀的样子比谁都厉害。可今天晚上竟然就这样任由别人再怎么抚弄都没有还手。
他不承认这是因为气氛到了才发生的事,虽然一样是“月朦胧,鸟朦胧”的夜晚,几线月华透过百叶窗的侧缝射了进来,可是他还是持有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态度的,他并没有对顾孝成浓情蜜意起来。所以这不是气氛的问题,可能搞不好是因为顾孝成的手指有练过,他的抚触太过于引诱人了,慢慢地就让人想着,在这样一个黑洞洞的寂静月夜的房间里,四下无声,这么让人舒服的事情不做白不做,做完了后第二天打开门出去也没人知道。等到了大天白日里,他“又是一条好汉!”
而事实上是,第二天早上他五点半就醒了——天生是奴仆的脾性,昨天晚上都那样子了,第二早还是该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只有更早,没有更晚!他醒了后,脑袋里就在琢磨着:这不对呀!前一天晚上顾孝成这厮试图强^暴我,结果强^奸未遂,所以昨天晚上就转为诱^奸我,结果还让这厮诱^奸得逞了……肯定是这样的!
他越想越觉得他自己昨天晚上是被人诱x了,总之想来想去都没觉得他自己是有半点情愿的。而身边这个顾孝成就在他眼里越看越可恶,不但来把他地盘侵占了,还把他身体给侵占了。他猛地跟诈尸似地坐了起来,而身边那个顾孝成竟一点反应都没有,依旧酣睡着。
方杰挪了腿要下床去,结果腿刚一动,就疼得不能说话。不动还没感觉,全麻木了,真一动,就觉得是要了命了。那并不是撕裂的那种刺痛,而是某些血管变得薄脆了,并且血管里面又充血了之后产生的一种胀痛。他忍着那种痛下了床去,忽然有一种羞愤,他接受不了这种事实,于是他还真把自己搞得像个过去那种被人□□后的妇女似的,带着那样一种神情夺门而出。不过过去人家妇女那样夺门而出后多半有可能是去投井以表明节烈的,而他夺门而出则是下楼去洗衣服的——这是他每早必做的家务之一。
他认命地洗着。是在他小卫生间的洗漱台上洗的,另有一拨外衣裤则是正在洗衣机里搅着。他这个小卫生间里的空间十分局促。由推拉门进来是正对着一个洗漱台,洗漱台前是整个的小半面墙的镜子,洗漱台下面有柜子——这些简单的装修是上一手店主留下来的,他也算拣了一点便宜。
人站在这台子前,左手边就是一台洗衣机,洗衣机侧面与镜子相对着的极窄的小半面墙上是上下三根杠子,上面挂有浴巾与毛巾,而那上面顾孝成的那条印有红心的浴巾还是那么招摇地挂着。洗漱台旁边又是一个又薄又小的浅碧色的毛玻璃做的推拉门,里面就是马桶与淋浴的莲蓬头。
方杰这个早上站在这个狭小空间里总觉得与往常站在这个空间里的感觉不一样了。以前他在这里面时也只是进行着一些日常生活的动作,像是洗衣洗脸这种事。而通常他做这些事时,脑袋里面想的无非也就是他小生意上面的事情,他并不会着眼打量一下四周,他也根本感觉不到这狭小空间的四壁带给他的一种压迫感。而今天早上,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他总是一再环顾,朝这里看看又朝那里看看,甚至也看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可是他就是有一种神经质,要去看上几眼。
他觉得他自己也有点什么东西已经变掉了,可是他情绪上又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一种变掉了的东西。
他拖着脚步上楼晾完了衣服,开下他的房门朝里面偷看了一眼,发现那人还睡得跟死猪一样。他轻声合上了门,想着要下楼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又或是重新思考一下人生。可他忽然又觉得凭什么,里头这人前天晚上强x未遂,昨天晚上就试图诱x,竟然还让他得手了。凭什么自己现在在这儿像个老妈子似地做这做那,而他竟然还安睡得像一个天生被人服侍的人。
方杰一口气冲到喉头,又“犯病”了,“嚯”的一下,将那个银色的球形门锁给拧开来了,左手还捏着他那只塑料洗衣盆的盆沿,大有一种破门而入之势。
顾孝成被这“嚯”的一声给惊醒了,猛地坐了起来,四顾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妥的事——浯城这种地方几百年都没有地震,所以他也不担心是地震,本来以为是什么书或是重物由桌上砸下来了。结果四顾之后再抬眼一看,原来是一个怒容满面的方杰刚刚破门而入,他手里还捏了一只洗衣盆,一看那架势,竟然跟古时候打仗时吹冲锋号角的小兵旁边的那个大敲锣鼓呐喊助威的小兵如出一辙。
顾孝成也不声辩他昨天晚上那样突如其来的一着,只是很静默地坐在床上,上半身裸着,两臂松松地搭在被子上,两眼黑黜黜地盯着那个有着“杀进门来的小兵样子”的方杰看着。
方杰本人大概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要与人“明是非,辨黑白”的时刻,手里面还捏着一个洗衣盆,是多么地像一个大婶,所以他为了不削减自己的气势,偏过头去看了一眼那只盆,就快速地往地上一放。然后人又是那样汹汹地走到顾孝成床前,哪里知道也不知是不是他那后面实在经不住他这样疾走,所以一下子也不知扯到了哪条正充着血的血管,整个人晃了一下,栽到了顾孝成身上。
顾孝成对他一大早竟然就能有这样的“投怀送抱”的自觉感到十分地欣慰,于是用两臂自然地环住方杰的上半身,说:“热情归热情,但不用这么急地冲过来,你还很不舒服吧?现在几点了?怎么这么早就洗衣服了,我晚点起来洗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