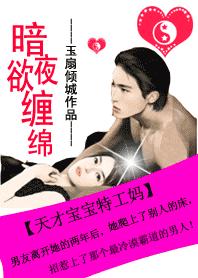宝贝吉祥-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说得好恶心哦,我不习惯了。”顾喆抽着两筒鼻涕道。
顾章,“……”娘的,果然不适合当慈父。
顾喆又跑过去问顾贝,“妹妹,你是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不知道。”她转过脑袋,看看唐诗诗,“娘,我什么时候回来。”
唐诗诗在一旁看戏般看着宝祥,她放柔表情,“等贝贝长大了就回来哦。”
“那是什么时候,我,我舍不得了,”顾贝带着哭腔道,“怎么办”
“贝贝,说好了哦,怎么能不算数了,乖哦,来娘身边,不要哭了。”
唐韦曲从船舱里走出来,他压根不想看到顾章,但临走前的唧唧歪歪让他很不耐烦,催促道,“诗诗,船要开了,抱着贝贝上船吧。”
唐韦曲对于要养唐诗诗前夫顾章的一个孩子,心里压根不情愿的。有些男人会对继子继女如己所出,那也是有一些啊,不包括唐韦曲本人在内啊,况且还是顾章的孩子,一想到心里就不舒服了。
生不出孩子,唐诗诗身体不好,也是一个原因。他也曾偷偷摸摸地出去尝过腥,他很爱唐诗诗,那是无可厚非的,毕竟等了她那么多年了,但在他观念中,喜欢和传宗接代又可以是两码事。
唐诗诗背后是唐将军,他不敢说要讨个二房给他生个儿子,就本想着在外面悄悄地生下来,等到瓜熟蒂落时,配合演个戏,他连剧本都想好了,就说是酒后乱性,当时害怕被唐诗诗知道会嫌弃自己,就不敢说,等到女人抱着孩子上门认亲时,就义正言辞一点,坚决不要那女人,给她一笔钱去自寻活路,不过想要回孩子,就得表现得好一点,证明自己是很爱唐诗诗的,到了那时候,就又有儿子,老婆也不必离散了。
如意算盘是打得很好,可是现实很弯曲,总不会顺着意来走。
愿意给他生孩子的女人是有了,播种也播过不少了,可就是怀不上。
他寻思片刻,觉得是那个女人的问题,便换了另一个,可是还是一直怀不上,几年间,换过的女人都赶上一个青楼的人数了,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
而夜出多了,总会遇上鬼。渐渐的唐诗诗也去怀疑了,对他渐渐不满,摩擦越来越大,总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他吵翻天。
于是,后来就提出要领养一个小孩,养生的不如养熟的,唐诗诗决定还是要一个自己亲生的。
唐韦曲衡量再三,还是同意了,毕竟自己不能生育一事,他觉得抬不起头,决定这密秘得守着。而且,要一个小孩,毕竟能换来家和。最近一年里,唐诗诗盯得他紧,时时刻刻在看犯人一样,让他很心烦。
唐诗诗看着满脸泪痕的顾贝,拖着她的手,上了船。
风在吹,呼呼的,顺着风,顾贝的哭声听得更大声了,一声一声,击在心上。
宝祥看着船远去,又看着船消失,站了很久,顾章心里叹了口气,一手牵着失了魂的宝祥,一手抓着哭得稀里哗啦的顾喆,走回车上。
顾喆回到家后,和顾章怄气了,一连几天不肯理他。
气得顾章又想抽他了。
一別后,其实顾章也不知道顾贝会什么时候回来,可能几个月后,唐韦曲上京视察时,顺便带她回来一趟,也许是几年,甚至真的是她长大以后。
其实想想也是挺悲伤的。
错过的不止是光阴,更是陪她长大的温情。
吃饭时,宝祥总会拿多一双碗筷,会念念道,“贝贝吃得习惯吗,南方的口味不一样呢。”
而这时,顾喆总不忘嘟囔几句,“当个屁的军长,连女儿都不会留下了。”
这话总是成功地让顾章哑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抨击中,还是无言以对。
地球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改变轨迹。时间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停止运行。
日子还是要过的。
只是冷清了不少。
顾喆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了,午睡也不在那个小偏厅,和他爹他叔混着睡在一起。
成长中,在顾章千锤百炼的棍棒下,慢慢的鲜少哭闹了,打得火热,疼极了,也只是红着眼眶,顾章问他,“知错没”
他甩甩额上碎发,故作坚强地,“打累了!”
拽拽的后果是严重的,换来顾章的父爱如山崩。
宝祥总是对这对父子感到无可奈何,但想想,还是觉得很幸运,顾喆留下来了,没被带走,有时候鸡飞狗走的,也不失是一种热闹。
几年后,顾喆长大了不少。某一天的黄昏中,顾章给儿子量完身高,发现他在不知不觉间就长到了自己胸口,忽然之间悲风秋月起来,摸着自己的脸,跑到宝祥面前,作出西子捧心状,蹙着眉头,脸皮够厚地问道,“宝哥,我是不是老了。”
“嗯。”宝祥洗着菜,头也没抬,随口道。
“噢,我的天啊。”他越演越激动,达到戏精上身的效果,又是摸摸脸,又是要宝祥抱抱。
宝祥一脚蹬在他小腿上,“别烦老子。”而后,没听到声线,抬头看到顾章深沉地站在黄昏下,黄黄的阳光,给他渡上一层柔光,逆着光,看不清他的表情。
宝祥,“……”老男人心,海底针。但他又忽然之间看着看着,觉得有点恍惚,他擦干手,过去,抱住顾章的腰,打趣道,“怎么啦,还没到四十,就跟个婆娘一样了,你烦不烦。”
“嗯嗯~”带着挑起的语调,他反问道,“我要是像个婆娘,晚上怎么服侍你。”
宝祥脸红,顾章胜。
顾章反搂着他,“你长得真好看,模样一直不变。”战争要开始了,怕自己老了,保护不了你。后半段,顾章咽在心里。
第 102 章
没多久,传来了唐韦曲阵亡的消息。
在热河中,唐韦曲奉命北上长城支援部队。
一战中,多少有着内部权力的斗争,并非积极抵抗。
在北平军分会仓促制定热河防御计划中,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两个集团军,由华北防御区的军长张良和张超分别统帅。
二月二十三日,日本第六师团第八师团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分三路向热河省会承德发动总攻。
热河守军有第四第五第六军团等八万余人,由于其中半数以上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各部只好仓促应战。
生死,荣华,牺牲,一系列反义词,在节节炮火连天的轰炸中,闪烁在每个战场士兵的头脑,有人愿意为国捐躯,有人也更多希望活下去,偏偏也是有人踩着累累尸骸,搂着黄金万两,投靠了敌兵。
三月四日,日军先头部队兵不刃血地占领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泉佯称督战,满载鸦片财宝逃离,因为此事,三月八日,张良被迫引咎辞职,由何裴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何斐是由唐将军一手提拔上来的,由于英勇无畏又有作战天赋,短短十年间,靠着过硬的战绩,一路高升走到了委员长一位。
唐韦曲也被调在他军营下,担任参谋长一职。唐将军对这位第二个女婿,谈不上欣赏,毕竟资历平平,天赋平平,但好歹也是在自己身边长大的人,对自己女儿也不错,出了小小私心,助他在官场上走得顺风一点。
前后不过十余天的时间,八万守军就仓皇败退,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于是日军的攻击作战变成了追击战,尾随中国的军队趁机扑向了长城沿线,随即以八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
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不唯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民族之罪人也。”一股苍凉悲愤的氛围弥漫在北部之地。
同时,山海关失守之后,多次呼叫国联制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
于是指望的希望就如被风吹起的泡沫一样,不被蒸发破灭,也会被吹破。
弹炮火连天的,即使己方人数是敌军三四倍,但区区血肉之躯拿着质量参差不齐的刀枪也挡不住日本兵队的大炮。用命去守住国土家园,代价太大了。
日军就像修罗场上的饿鬼,四面呼啸进侵,所过之境,无一生还,来不及出逃的居民,要不死得痛快,要不就□□至死。
战事延长,为求保住领土,战线也被逼拉长。
驻守天津的顾章也在仓促间,接到命令,统帅一方部队,严阵待命。
何斐驻守长城后,重新安排了战略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西北军东北军中央军,共十三个军,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约二十五万人,为适应军事,暂重新编排。
按着何斐的命令,在长城横跨面上,顾章所属的第五十一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第三十一军担任滦河以冬一带的防务。第五十三军在原地调整,以三个师助防第五十七师冷口以东地带。第二十九师和第四十军负责喜峰山、马兰峪一带防务,并依次类推,沿线五百公里的阵线上派军团驻守要塞。
长城抗战于三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个隘口,日军在坦克飞机打炮的火力支援下,猛烈进攻。
三月四日,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五十七师全体军兵在弹林枪雨中反攻收复。
纵使喜峰口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在冷兵器时代,一枚大炮足以虐杀躲藏在林中准备伏击的一个旅的士兵。
战争就是如此不近人情,哪怕揣着满腔的道理和热血情怀,占理但不占利。
人肉挡不过科技,只能节节败退。
当时一个炮弹冲天而来,司令部瞬间爆炸,唐韦曲等几个指挥官,刹那间,血肉模糊,尸骨无存。
后到的援兵一师十三团,暂时拖住了日军的进攻,十里春风,不知国恨,悠悠荡荡,吹拂拂面,拂起死去的士兵的亡魂,夹带着血腥,在阳光明媚下,泛起阵阵凉意。
十三团团长派人挖出司令部几人的残骸,人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他凭着衣着勉强分辨出是谁和谁。
战事刻不容缓,多少将士马革裹尸,葬身他乡。
回不去生育故乡,只能让坟墓石碑越过千山万水,遥遥在望。
死了很多人,但也换不来战争的止停。
一时之间,举国惶恐。
昔日的名城被三面围攻,无力感,充斥着每人身上。
顾章驻守期间,宝祥一直关注着战线,祈求平安。
一直延持到五月份,南京政府为自保,签署了《塘沽协定》。
……
宝祥记得那是一个红霞万丈的傍晚,唐诗诗披头散发带着顾贝,出现在顾家大宅门前。
顾贝改了姓氏,叫唐贝。
几年没见,唐诗诗隐约现着老态,面容憔悴枯瘦,虽涂抹着妆底,但像挂在脸上的面具,全然没了原先的风发。
她还没说话,眼泪就掉下来了。
顾贝记得宝祥,但几年没见面,变得怯生生了,小声地喊了他一声,“叔叔。”
宝祥也知道唐韦曲牺牲一事,看到母女俩这般模样,心里泛起酸苦的涟漪。他勉强笑笑,跑过去,弯下腰,摸摸顾贝的脑袋,又对唐诗诗问道,“你们,就你们两个跑过来?”
唐诗诗沉浸在自己悲伤的世界中,惘然不答,追问着要找顾章。
人总是有劣根性。
多少人在亲人活着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和欣赏,看到的满是对方身上的缺点。
当初离婚后,唐诗诗嫁给了唐韦曲,不算心甘情愿,也不算是被逼上梁山,就是觉得无所谓。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过得一如既往的无所谓,无所谓夫妻情意,无所谓乐意融融。
一潭死水,是唐诗诗对生活的评价。
但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终究会在不可抗力的因素中,改变了轨道。
她觉得一潭死水,不过是因为有人替她默默维持,如今,人死了,水被搞混了。
在唐韦曲出征的半个月里,是他离家最久的一次,每次离家前,他总会带着她去附近的寺庙求几张平安符,一张自己,一张她,一张是顾贝,他名义上的女儿,虽然不亲近,但也看在是她的份上,顺带捎一份。
每次求回来的符,唐诗诗也只是嘴上承应着,转过身便是随手一丢。
这次也不例外。
手一松,明黄的纸符便是随风飘荡,灼灼红艳的朱砂字,若隐若现。
她想,当时不应该丢掉的,她后悔了。
唐韦曲阵亡的消息在夜里惊雷般传来到她耳边。听的时候,没多大反应,甚至还条例清晰地询问着他的葬身之地,拿出当家做主的风范招待着传信之人。
在刘妈花骨朵抱着她哭,“小姐命苦啊!!!姑爷命苦啊!!!!”撕心裂肺的,但怎么也震不到唐诗诗的心窝里去。
她想,自己真是冷血动物。
就以为大家都觉得唐诗诗是撑过去丧夫之痛时,那天清早,阳光正好,透过红红绿绿的窗玻璃时,七色的彩虹折射在地上,她征住了。
窗玻璃是唐韦曲亲手换上的,只因经过教堂时,她随口一说,很漂亮。他便是记住了,下午端着工具,和硬闯教堂扣下来的几片玻璃,手脚麻利地安装上。
她心里耻笑,只觉得颜色鲜艳夺目的玻璃也寝室素雅的装修,浑然不搭,留下一句,“有毛病。”施施然离去,没去看定格在唐韦曲脸上的笑,憨笑变成苦笑。
她征征跪坐在斑蝥的窗台下,伸出手指,摸摸七色光,手指一碰过去,便会挡住光,留下阴影,伸回手,看着美丽可爱,但触摸不到了。
眼泪瞬间缺堤,倾斜汹涌而来。
没有大喊大叫,静静地,一个人,跪坐在冰冷地上,神奇呆滞,一切仿佛是静止,唯有眼泪簌簌。
再后来,她吵着要北上带唐韦曲回家,唐将军苦口婆心劝阻,说,北平一带战乱不堪,一个妇道人家即使带着精锐部队,没有指挥能力,遇上日本军,就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还拉着一队人去送死陪葬。
话说到这份上,再求,也是无济于事。
唐诗诗失了魂一样,喃喃自语,“为什么要派他去?!”
“什么?”她的声音嘶哑小声,唐将军听不清楚。
“为什么要派他去?!!!”她几乎是吼着出来。
“啪!”一声脆响,唐将军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