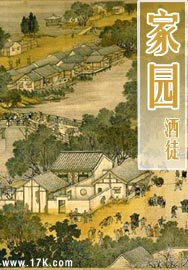外遇_徒魎屺-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用指尖捻去我眼角的湿润,我其实有些看得呆了,我觉得他穿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看,整个人在昏暗的地方像镀了层光,周身环绕着细小的棉絮。
嘴唇上还有我咬破的痕迹,他给我一个微笑,像是休战的讯号。
“还想做么?”他问我。
我用目光仔细临摹着这个人。
他惹我生气时就是我的仇人,笑着撩拨时又是爱人。
这样矛盾的角色,在他身上却转换地驾轻就熟,我不吭声,不想妥协,我维护着自己的面子与软弱,小心眼与偏执。
他这样打一巴掌又赏颗糖的套路,不是一次两次,但在我身上次次都能奏效。
因为他这颗糖太甜太好吃,小小舔一下就能回味好久,所以好了伤疤就会忘了疼,可糖吃一次就还想再吃第二次。
他穿着衣服操着一丝不挂的我,我紧紧攥着他的衣服,吻他被咬破的嘴唇。
我出乎意料地没有说话,平时在床上我总是话比较多的那一个,今天的我不知是因为酒精还是刚刚的闹腾,起落之间像置身于汪洋大海,只觉得晕。
这样温柔的杨齐霄我承受不来却甘之若醴,他一点一点带动着我的内里,再瘙着我穴口的痒。
“炎焱。”他唤我的名字,比任何时候都缱绻爱恋。
我喟叹了一声,搂住他的脖子轻吻他的细密的睫毛。
只是这样的好总是这样短暂,我被他搂在怀里,即可就要安心地睡过去。
却听见他说他要走了。
他含着情望着我倏地睁开的眼睛,指尖勾缠我的发丝,亲吻我的额头,我相信即使我不睁开眼也能知道他眼里的喜悦。
他说:“炎焱,我马上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他曾经在我暑期的生日里,送给我一驾自己做的飞机模型,那样精细的金属零件,不知他花了多少个日夜拼凑而起。
我为了它将从未用过的书桌上整理干净放于其上,每日擦拭,视作珍宝。
在收到礼物时,我还一度兴奋地对他说:“我等着看全世界最帅的机长。”
他笑答,略带感慨:“你看我们有多不一样,你喜欢的和我喜欢的,都是不一样的。”
是啊,我喜欢陆地,而他却一心向往天空。
但我没想过他会离开。
我闭上眼,不再看他,也不敢看他。
我全身止不住地颤抖,杨齐霄以为我冷,又把我抱的更紧一些。
第25章
我从来就没有梦想。
梦想是什么,记得小学的时候特地要求要写一篇题为《我的梦想》的作文,我看着其他小朋友都有话好写,但我确实没有。
我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没有理想的职业,也不喜欢去展望还没到达的未来。
所以当杨齐霄告诉我他的梦想时,我心里咯噔跳了一下。
我不希望他问我,因为我说出的话显得太没有志气,太不阳光。
可当他浅笑着说:“炎焱,你以后想干什么?”时,我还是努力地去拼凑一些语句应付过去。
我说:“我爸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不然我自己能干什么?
让自己活着的无非是柴米油盐,我不相信梦想能让人活着。
对我来说,怎么活的方式并不重要,可以衣食无忧,为什么还要自己拼搏。
杨齐霄显然对我的答案并不意外,他从背后环绕我的肩,下巴搁在我的肩窝。
我反问他:“为什么喜欢飞机?”
眼前是他送的飞机模型,在深色书桌上显得生动且高贵:“小时候有一次坐飞机,遇上了强气流,振动得厉害,所有人都很慌张很害怕,我也是。”
“但当我听见机长的话时,我就不害怕了,他说让我们不要慌张,他有自信能带领我们度过这次难关,请我们相信他。最后真的没事了。”
他用沉稳的语调说着整件事情,追溯过去喃喃细语,我挪了挪头,与他耳鬓厮磨。
他在我身后笑,笑出的热气喷涌在我的耳旁:“我有一阵觉得他是超级英雄,就是电影里放的那种。但后来发现他不是。他也是普通人,但像英雄一样值得让人尊敬。”
我撇头看他,说起他喜欢的事时他就不会悭吝说话,眼里都是灵动的光,我靠在他身上享受他把自己告诉我这一过程。
这时的我十分沉默,因为我并没有东西能够告诉他。
并没有能够启齿的东西。
回望我的童年在干什么,随着父母的事业四处奔波,不断转学,受欺负受的多了,就变为欺负别人的那一个。
谁都不会天生就会打架,我好不容易练就的打架技术也在遇到杨齐霄时变得毫无用武之地。
还是要告诉他我交的朋友都是一丘之貉,不务正业,不学无术。
或是要告诉他我名存实亡的父母已经离婚,使我现在真真正正地成为了孑身一人。
这些千回百转的事情,无一不是一种同情,耍可怜。
弱者才会这么做,我不希望看到杨齐霄的眼里对我的感情到时候会夹杂着怜悯与可惜,所以我能对他说什么。
我只需要把他攥得紧紧的,不让他离开我身边就好。
那晚的我一夜未睡,杨齐霄睡在我身边,眉头舒展,我看出他的心满意足,大部分与我没有关系。
他高兴于自己要离开我这一情况,高兴于与我的不同终将越来越显著这一事实。
我伸手轻轻地触碰着他的眉眼,再到他已经结了一个小痂的嘴唇。
就这么看了一夜,他睁眼时瞧见我正看着他,略带惊慌地吓了一跳,开口时是没有睡醒的暗哑,他摸了摸我的发顶说:“怎么醒那么早?”
我身体很累,但头脑却依旧高速运转,我想回他在一刹那就想出来的理由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他手摸到我的额头,皱眉道:“你发烧了。”
我感谢于自己身体突如其来的脆弱,让我有机会能看见杨齐霄为我忙前忙后,他连学都不去了,请假在家照顾我。
我的额头搭着他给我的冷毛巾,被子把我盖得严严实实,他还给我煮了粥,用勺子递到我嘴边可我实在喝不下。
“好歹喝一点,不然怎么好?”杨齐霄的脸上布满对我关心的神情,我心一软,张口喝了几勺。
“好乖,那你再睡一会儿,睡醒了如果还不退烧我们就得去医院。”杨齐霄给我喂了几口就不再强迫,用手指擦过我嘴角的粥水。
“我不想去医院……”
喉咙像是碎了,说出的话带着撕裂的突兀声,让杨齐霄听得摸上我的喉结,轻声道着:“怎么那么严重?”
我从来没有那么娇气过,生个病还要有人服侍,但这些是偷来的,一点一滴我都格外珍惜。
这个时候不娇气什么时候娇气,没人会为难病人的。
我在躺下去的时候拉住了杨齐霄的手,他笑着就像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你放心我不走。”
我说:“真的么,你说你不走。”
杨齐霄点点头,催促着我睡觉。
我却犯了傻,起了执念。“那你能不能别去?”
“去什么?”杨齐霄还不明就已。
我死死抓着他的袖口,真的想要把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
可我在那一刻却退缩了,我不敢:“别去外面,抱着我睡……”
“怎么那么会撒娇?”杨齐霄有些无奈地一笑,他捏捏我的手,睡到我的另一边,俯身亲我的额头,把我拦在怀里:“好了,快睡吧。”
随后我便真的闭上眼睛企图睡着,杨齐霄就在我的边上,他的气息环绕着我,手还轻轻拍着我的胸口,嘴里哼着熟悉的摇篮曲。
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放他走。
我鄙视于对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却又更为坚定。
一个月后他就要去空校,距离这里统共1094公里。
他的体格完美,成绩优异,所有标准都符合,即使不高考也能直接提前录取。
在我病好后他又重新返回校园,而我却以生病为由长期请假,我焦虑地整宿整宿无法入眠,手指上满是无法痊愈的蜕皮,杨齐霄每天都比前一天更显得精神奕奕,我扫了一眼他书包里那些白色的申请材料,上面正是他要去的地方。
我快崩溃了,不管是我的精神还是肉体。
在见不到杨齐霄的时候我如同个精神病人那样缩在角落,或是看见手边的东西就胡乱砸在地上,我把家里搞的一团糟,又在杨齐霄要回来之前把它收拾干净。
在见到杨齐霄的时候,我尽力表现地和正常的我一样,吃饭做爱,再到佯装睡着。
我找不到宣泄口,就这么坐地为牢,困在了自己划分的一寸方圆。
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找上了我,他是杨齐霄的父亲,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这儿的地址的,但当他说明他的身份时,我就知道我和杨齐霄的事已经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
他没有杨齐霄那么高,但也身材颀长,他有着比杨齐霄更强大的气场,带有审视的眼神从一进门就把我扫了个遍。
我以为他会直接让我离开杨齐霄,毕竟所有剧本里都是这么写的。
可他却说:“杨齐霄是我儿子,我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所以今天来并不是拆散你们。”
“但你们的行为我也并不赞同,不过这些事情以后再提,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杨齐霄他要去空校,这件事你知道吧,可我是打算让他继承我们家族的企业的,现在他舅舅如狼似虎,形势紧迫,我不可能再放任杨齐霄去上什么空校。”
“所以拜托你,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把他留下来,只要你办到这件事,以后你想和杨齐霄怎么样我们都不会插手。”
我怔愣地坐在他对面,全程没有开过口,直到他父亲出门的那一刻,我才叫住了他。
他转头看我,我问:“你是不想……让杨齐霄恨你们么?”
我深呼了一口气问他:“可我把杨齐霄留下后,他万一恨我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我想让他留下来,比任何人都想,可留下他必定付出代价,我没有信心去面对这个代价。
他微微地拾起笑意,我看得出他已经把我的心思看的清清楚楚,那般从容又暗藏狡黠:“你会有办法的。”
这句话把我打在原地。
我会有办法的,不管他是恨我还是如何,我都得把他留下来。
否则我可能连他的恨都讨不到一星半点。
第26章
现在想想,我只不过是被人利用,并且心甘情愿罢了。
杨齐霄父亲处心积虑不让他儿子逃离他的掌控之下,以一种最置之度外的方式谋取他想要的结果,事实证明他也找对了人。
我全身泛着被打后的酸疼,骨架都要散了,杨齐霄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
我略微撑起身,对一边向我投来满是担忧眼神的MIKE比了个眼色示意他我没事,MIKE退出房间把门轻轻合上。
我说:“事情都办妥了还不允许我休个假?”
尽量保持着正常的语气,不让他听出我现在其实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
杨齐霄又问:“你做了些什么?”
看来他还不知道我的英勇作为,我有些许失望:“不管做了什么,结果都是好的不就可以了?”
杨齐霄一阵沉默,我聆听着手机听筒下的细细电波声,臆想着杨齐霄此刻会是怎样的表情。
是蹙眉厌恶,还是面不改色。
我不介意他怎么想,最好把我想的无恶不作,越坏越好,这样知道真相后的他才能体会到更大的具有冲击性的反差。
“杨总,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睡了,毕竟我可是忙了一晚,很累人的。”
如果他想不到,那我就引导他想入非非好了。
杨齐霄果然连招呼都不打就挂了电话,我把手机艰难地甩在一边,睁着眼想着,如果我真的用那样的方法达到结果,杨齐霄会不会就不要这个单子了。
他比我有原则,知道孰轻孰重,善于权衡利弊。
所以当我直白地对他说我不想他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坐下来和我谈谈。
那天他父亲离开后,我就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他,我在想他父亲所说的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留下来。
或许只能用我自己。
我承认这一想法实属高估我在他心里的位置,试想撇去他一开始对我做的混蛋行为,之后的种种,都是因他对我的愧疚与我对他的执念。
他负责,负的是愧对我的那份责任,但到现在为止,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那份责在我心里早就不算数了。
是我自己先忘了我们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有一句话叫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说的就是那时候的我。
他进门后先喝了一杯我放在餐桌的水,听见我的话后才放下水杯走到我面前。
他不惊讶于我的话,握着我的手蹲在我身前,抬着头看着已然内里丑陋的我。
他说:“炎焱,你不要误会,我去那里不代表和你分开。”
我看着他的眼神真挚而肯定,可我偏偏不相信。
这样缺失的安全感是从何而来?
是从他劝诫我不要在与海哥那群人相处,还是从他在芸芸众生中都出挑的光芒,或是他与朋友之间露出的我从未见过的笑容。
我脑海里猛然想起一个画面,过年时的地下车场,他字里行间的敷衍与淡漠,也只有那时候的我才听不出来。
一旦开了个头,就再也收不住。
破碎的画面从四面八方波涛汹地涌席卷而来,我与他不得不相处时的勉为其难,他一开始见我时的居高临下不屑鄙夷,种种种种,都在我脑海中闪回般地跳动。
我受不了他离开。
再说,我承认,我本身就没有安全感。
即将分离的人不会开口说要分离,谁不会撒谎,谁不会哄人。我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我被骗过一次,就必须得长记性。
我说:“我不想你走,你能不能别走。”
我好不容易能够俯视他,可嘴里说的竟然还是这般低姿态的恳求。
杨齐霄神色冷了下来:“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突然想要自暴自弃,想把自己全盘托出,想要告诉他我的担心,我的自卑,我因为他要离开我的不安,但我并没有。
这些如果依然不能够挽留他,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只得尖酸刻薄,实际上如鲠在喉:“杨齐霄,你好像搞错了,是你对不起我在先,如果你要走,也得要我同意。”
杨齐霄皱着眉,他还穿着校服,显得挺拔且光彩照人。
反观我,邋里邋遢,萎靡不振,行尸走肉。
他生气了,我能一秒钟辨认出他是否生气,我不经意地瑟缩了一下,像是某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反应:“炎焱,你还把我们在一起的事情认为是强迫性的么?”
不是我认为,明明是他认为。
我回击道:“杨齐霄,你试问自己,如果不是你的愧疚,你会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杨齐霄无语轻笑,眼底深邃到一片墨黑,他似乎不想再与我这般无理之人纠缠,背起包便要转身离开,我惊慌地一把拉住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