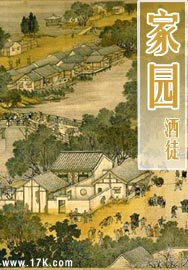外遇_徒魎屺-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在说什么啊?”我叼着烟皱起眉,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鼻音。
“一个月前,你在夜吧带走的那个女生,是我妹妹。”
他这样说我终于在脑子里对上了号,怪不得那个女生怎么看怎么眼熟,原来他俩是兄妹。
我咧嘴笑笑,觉得他管的太宽了,又有些嫉妒,看来兄妹俩关系很好:“所以呢,她又没有不愿意。”
话音未落,他就把我推到了墙上。
“操!”我被莫名其妙这么一推,口中的烟都掉了,气得抬起手想揍他一拳。
他灵巧地避开后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托住我的头砸到墙上,使得劲儿真够狠的,我被他砸的脑子嗡嗡作响,他又开了厕所隔间的门把我推进去。
这间是用来放杂物的,我被他推进去时,脚踩到了拖把,差点滑一跤。
我哪能就这样罢休,抬腿就想踹他,可头太晕了,连脚都使不上力气,于是我这一脚在杨齐霄眼里,只不过像只猫在逗着玩儿,他一抬膝,就把我的双腿用力地钳制住,并又给了我一拳。
这人是想怎样,他妈的比我还暴力。
我被他揍得牙齿磕破嘴里的软肉,血腥味充斥着整个口腔,说话间一股血沫味儿。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是真的被气得要死,太阳穴突突直跳。
他冷冷哼了一声,手指掐住我的腮帮:“我妹她怀孕了。”
我愣了片刻,又特别想笑,但被他掐着笑不出,只得发出有些嘶哑的呼吸声:“关我屁事!我操她?我他妈操你还差不多!”
我看着他表情越发森冷,我却有些想吐,大概是砸了头的后遗症。
“你给我放开……”他不听,反倒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
他的舌头和女生的不一样,强硬霸道,更别说什么甜味儿了,像条冰冷的蛇。
因为他的舌头我全身刷的一下起了鸡皮疙瘩,像被踩到尾巴那样挣扎,可杨齐霄力气太大,大到我的舌头一阵刺痛,也许是被他咬去一块肉,疼得都隐隐发着麻。
我没操上他。反而被他操了。
天冷了衣服穿的多,他脱衣服的速度却很快,只不过他脱的是我的衣服,校服连同里面的毛衣,都被他扒去。
我被他脱得一丝不挂,衣服被他踩在地上,长裤被他褪到脚跟,浑身冷得一激灵,而他却好整以暇站在那儿操我。
没有前戏,没有爱抚,如果那个为了堵住我唇舌的吻算前戏的话,那也太没有追求了。
我看过男人和男人做爱的片子,他们的表情一般都很享受,我就自认为他们都很舒服。
可当自己实行起来,滋味却不是这样。
他把我翻了个身,一手攥紧我的腰,一手伸到我嘴边,强硬地让我的舌头沾湿他的手指。
我还没有咬下去的反应,他的手指就抽离开,随后摸到我的后穴,直直插了进去。
我从来没那么疼过,脖颈在疼痛呻吟时向上弯起,被杨齐霄逮到咬了一口。
我看出他实际上也并不喜欢这一项举动,他的动作粗糙且带着不耐烦。
他把性器强硬地塞入我艰涩的后穴时,我听见他嘶了一声。
就算这时,我身体无力反抗,但我的嘴空着,他这样对我,我不能让他好受。
“杨齐霄……原来你是变态,真想不到……”我断断续续地说着,被他顶入时的尖锐痛楚卡住了脖子,死死咬着下唇,不让疼字说出口。
这算不上性爱,只是场泄愤,而我是被发泄的那一方,占据弱者,只能承受。
他抽插的动作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我双手撑在眼前的墙上,眼睛都是花的,腿被他操得快要塌下来。
“杨齐霄……唔……你对男人还硬的起来,同性恋啊你……”我随着他抽插的频率开口,我眼角湿润,却克制着自己不流眼泪。
他终于想起要堵住我不断开口的嘴,便用掐着我腰的一只手紧紧捂住我的嘴,我鼻子塞着,只能用嘴呼吸,这样一来呼吸不畅,竭力地摇头挣扎。
“说的好像你没硬是的……”杨齐霄另一只手伸向我的性器,抠挖着性器顶端,我的嘴被他捂住,发出气弱的唔唔声,“这么疼不还是硬了。”
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捂住耳朵不去听他的话,可手除了支撑靠在墙上,便再也没力气移动半分。
“炎焱,你很会夹啊……”他的气息在我耳畔逐渐粗重,这个主持时沉稳的声线,此刻在念我的名字,对我说着淫言秽语,我不知是因为他的话,还是他性器的动作,全身都不间断地发着热,嘴又被他捂住,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快要受不了了。
他见到我的眼泪身下的动作停了片刻,嘴唇靠近我的耳边,开口时像在吻我的耳垂。
“你不再说话,我就放开你的嘴。”
我只得妥协,眼神带着求饶,微乎其微地点点头。
他终于放开桎梏我的手,我犹如脱水的鱼再次跳进水底,大口大口汲取着空气。他听着我的喘息声,更加快速地冲撞着我的体内,我得呼吸,不再咬唇,只得把最露骨的呻吟都叫出来。
最终他射在我的里面,在我也射出来的同时。
他贴在我身后,我的背感受到他衣物的摩擦,出了一身汗,这样停下来又觉得冷。我低头瞥了眼地上的衣物,上面粘着白色的液体,我的和他的,聚成了一滩。
我竟然不觉得恶心。
我有些绝望,我被人操了,居然还射了,没有靠手,单纯被插射。
怎么能那么贱。
杨齐霄趴在我身上喘了会儿便放下握着我腰的手,离开了我。
没有他的手,我顿时腿软地跪了下去,后穴的液体顺着我的动作流了出来,粘稠地让我心里发慌。
我使了力气转身抬头,看着杨齐霄拉起他的裤链,明明眼前一片模糊,却看见了他气定神闲的姿态,似乎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居高临下看着我,声音平稳冷漠,对我说:“你别再见我妹妹了。”
我垂下头,堪堪翻了个白眼,无力地把手抬起挥了挥。
“滚吧你。”声音很轻,也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第13章
我在家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摸摸额头烫得厉害,便躺在被子里憋汗,迷糊睡过去,再迷糊地醒来。
等到两天后还不见好转,我才打电话叫来家里的私人医生。
我让他给我打瓶点滴,再给我配些消炎药,又让他给我查了查脑袋,说是之前打架磕到了,一直觉得晕。
他检查后说没有大碍,比较严重的是我的感冒。
我吸吸鼻子又躺会去,问他有没有外涂的消炎药。
那医生是个男的,我爸妈的朋友,我生病在家这事儿并没有和他们说,但我相信医生会告诉他们的。
我爸妈有各自的事业,现在应该在别的国家死命赚钱,一年能碰上两面就很好了。所以医生就算把我生病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也无动于衷,毕竟我不会死,那就没有从国外放下几千万的单子赶回来的必要。
医生看了我一眼,问我哪里还受伤了。
我伸出舌头,含糊地说:“嘴巴里被揍烂了。”
他给我一小瓶外抹的消炎药,又给我扎上点滴,还因为与我爸妈的交情在厨房煮好粥,让我醒来后喝掉。
我不习惯有人这样照顾我,而且消炎药就在我手上,我得做正事。
我脸色苍白地朝他笑笑,对他说放心饿了我会叫外卖的。
等他走后我便把消炎药打开,涂了一点,透明的,贴近鼻子闻了闻,没什么味道。
因为一只手在吊水,只能动另一只,我只能半撑起身子,艰难地抹上撕裂后酸疼的后穴,很凉,还挺舒服。
那天我被杨齐霄那一顿折腾后,在原地缓了好久,最后是因为听见放学铃声才把地上的衣服穿起来,只穿了毛衣,被沾上精液的外套被我丢进了厕所垃圾桶。
我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地狼狈,但在走出厕所之前,我瞟了眼镜子里的自己,还真是任谁看都是一副被操烂过的模样。
我内心如散乱的毛线缠得一团糟,躲避瘟神般不再看自己的脸。
幸亏已经放学,校门外没几个学生,我一瘸一拐走出校门,在厕所时连纸巾都找不到,只能拿校服随意擦了擦,现在走路时总觉得里面还有液体在顺着大腿根流下来。
我恨恨地随手拦了辆车,坐地笔直,不让司机看出异样,而头上却冒出冷汗。
最后连钱都看不清,随手把钱包扔给司机让他自己拿钱,他略带关怀地对我说:“学生你好像生病了。”
我他妈当然知道我生病了。
我接过他递还来的钱包,打开车门,说出我倒下前最后一句清醒的话:“大叔,我只是运动过度而已。”
直到打开家门,我才一股脑瞥去强撑的力气倒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这人并不娇气,按理说从小锦衣玉食想必是吃不了苦的,我的确没吃过多少苦,吃最多的大概也就是孤独。
这么说就有些矫情,谁都是孤独的,但我孤独地特别严重,若是孤独能分等级,我便属于3A级,过于孤独,孤独到我都不觉得自己孤独。
这是事实,因为娇气的人都是别人宠出来的,并不是物质堆出来的。
于是我并不觉得生次病能怎么样,自己挺着也就过来了。
其次我心理素质还特高,对于杨齐霄这样的虚伪人士,我除了惊叹他的演技一流,便是嘲讽他的头脑简单。
好学生也不过如此,就比我稍微暴力一些。
但他的行为明显比单纯的暴力更有建树,他把性阐释地淋漓尽致,性总比暴力更容易发泄,这句话我是从他身上总结的。
作为被发泄对象,总是会有超于常人的领悟能力。
我躺在床上发呆时就想,我讨厌他吗,恨他吗,这种愤恨程度会让我忍不住去杀了他吗。
可我明明也爽到了不是吗?思及此,我又会忍不住笑出来。
我脸皮的厚度让我当不起坚贞烈女的角色,因此我对这件事情的定位就摆在了一个很奇怪的位置。
不恨,难道就算了?
白让人操一顿,互相做对方的白嫖?
还未想出什么更有用的办法,我就会睡过去,催眠程度好比打进血管里的其实不是别的药水而是安眠药一样。
可睡梦中我也不得安稳,总是听见有人叫我。
炎焱,炎焱,声线沉稳绵长,催魂一般,做梦时身体周围燃着火苗,像极了我的名字,烧的快成灰了。
我回学校时恰好就要到期末考试了,一个星期没来学校老师也只是敷衍地关心一句,看样子我不在的日子省去他们不少烦心事。
我依然习惯性地去顶楼的厕所抽烟,垃圾桶里的西装已经被人收了,我心想收垃圾的人看见衣服上的东西会做何反应。
我再也没见到杨齐霄,因为考试取消了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不再听见他的声音,也不会再看见他抽烟时蹙眉的表情。
顶楼厕所又变成我一个人的地盘,但我突然没什么抽烟的欲望了。
校园里暗暗流传着他妹妹打胎的消息,说是暗地里,其实八卦闹得风风火火,我手插裤带吊儿郎当地走在路上,都会接受到他们异样的眼神。
去酒吧那天太多人看见我把他妹妹带出酒吧,以为是我搞大她肚子也正常。
外人也就罢了,我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可杨家人都是这样误解别人的么,杨齐霄,再到他妹妹,都把黑锅往我身上背。
我挠了把头发,觉得烦,回瞪向几个窃窃私语的人,他们见到后都快速远离我,犹如鼠窜,我嘁一声,也就这点胆。
我得找点事做,便重新去海哥那儿飚车,有一个星期没来海哥见我哟了声:“阿炎,你这一个礼拜去哪儿了?”
我坐上一直以来习惯开的红色改装车,透过车窗瞥了海哥一眼:“你什么时候管那么多?”
我见到他就觉得气,根本不想和他说话。
海哥被我呛了也不恼,朝我打着哈哈,手里递给我一根烟:“尝尝,新给你带的。”
我扫了一眼,又看见他笑着的样子,说不出别的,总觉得有些怪。
“算了,不想抽新的。”说完便发动车子留下他一人站在原地。
第14章
再一次见到杨齐霄时,是考试考完的那天,对于学校考试我都是应付了事,并没有其他人那样考完就要狂欢一通的兴致。
我一个人坐在夜吧的卡座里,拒绝了所有要坐到我边上的人,海哥最近忙得很,神出鬼没,我也乐得清静。
舞池里多数都是我们学校的人,他们脱去校服换上自己的衣服,装作社会人士,喝酒作乐,有些还尝试着钓妹子。
绚烂的灯光摇曳闪烁,酒喝了几杯眼前就被灯光闪出了幻影,所以当杨齐霄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怀疑我的酒量怎么突然变差了。
他没穿校服,而是穿了件卡其色的大衣,硬是绕过桌子站到我面前,表情淡淡,俯视着我。
我瞬时记起那天在厕所的情形,他也是居高临下,好像我必须得俯首称臣。
我有点不爽。
“好学生还会来这种地方,走错了吧?”我双手搭在卡座的椅背上,笑眯眯地看着他,只是这层笑里有多少讥讽,只有杨齐霄才能看清。
“你没看错,是我。”杨齐霄开口,明明音乐震耳欲聋,他的声音也不响,但我看着口型,就能听见他的声音。
“哈。”我被他的自信激得脚底都发麻,蹭地一下从卡座上站起来,站到杨齐霄面前,对上他的眼睛。
这人居然真的比我高,我挺了挺胸,这才差不多高。
“有何贵干,来找打是吗?”此刻的我像一只下一秒就要冲上去的小狮子,我看着杨齐霄平静的脸,都已经现出爪子,探出獠牙,就差把他咬的稀巴烂,“还是上次你没玩够,换我了?”
见不到他的时候我还没什么感觉,自个儿发了很久的呆一个劲儿纠结,但见到他我知道这些呆都白发了。
我很生气,非常非常的。
杨齐霄用他那双有些混血的深邃双眼,差不多盯了我有三秒,才说:“对不起。”
我怔住。
他又说:“之前的事情我问过我妹妹了,他说不是你,所以我来道歉,你要打要骂,随便你。”
就像拳头打在软棉花上,所有的一切都只有我一个人自作多情,一个人生气一个人纠结,一个人当个傻逼。
而当事人却轻描淡写来一句,要打要骂随便我,我打死他又能怎样,谁规定打死了就代表原谅了。
“你特意来这向我道歉?”我挑眉问。
“是。”他说。
我抄起桌上的酒瓶,举高往杨齐霄方向砸,可杨齐霄眼睛都没眨,看着酒瓶摔在地上,他连被吓到的一丝惊慌都不给我。
看,打他便是这样的反应,太无趣了,不是我想要的。
酒瓶碎了一地的动静让许多人把视线汇集到这儿,我站在一片汪洋下,攥紧眼前不在水里的干旱者。
我得把他拉下水。
“好啊,你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