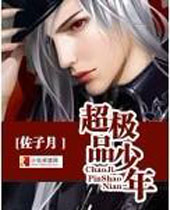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ÿ���������������ɣ��Ҹ�һ���м�ͷ��С�ÿ�����˵���������ҹ������µ��ˣ���ΪһЩ����Ҫ��һ�£���ʱ�����DZ߶�ʱ�䡣�㻹�ǵ����������ʲô�ɣ�����ï����
������������룬��æ��������ġ�����˵���ϸ����ͷ��ͣ�ó������Ϲ��ӡ�
�����Է�ʱ���Ҹ��ϸ����˴���С���ᣬ�ϸ�ĸ����������ÿڡ��Ǽ�ͷ���ÿ�ֻ��һ���dz�Сʮ���˵�С�ÿڣ�Ӧ��������ϵ��֧ϵ���Ʋ��ϵ��ÿڣ�ֻ��ط����������µ�����������֪���Ƕ�ծ���˵ĺ����ڡ���������Ϊ�ӣ��ط����ٶ��������˿ڣ�����ݷ𣬻��������㡣
�����������ϸ���Ķ��㰢��ร���
������Ҫȥ�ǽм�ͷ���ÿ�ǰ���죬�������ڻ�ݸ��������ڿ����ϣ˵�ǰ���㳦̯���IJ��İ������������������ָ��Ҵ��к��������������㳦���ҳԡ��Ҹ������˶��ڽ���һ��һ�ڳԵ��㳦���м���û�����ҵİ���������Ҫȥ��ͷ�DZߣ�����һ��üͷ��
��������צ����ͷ���DZ߲��ã���
���������ϸ翴����ϵ������������ï����Ͳ��ڿ�Ҹо�������������ͦ��ף������������Լ�ͷ�����ǰ�С��һ�㣬��������������ȥ����������¡����������ҵ��ģ������㳦����ЦЦҪ���ⷳ�գ��һ�ע��ģ������������ûȥ�������ܵܣ������̾���������˵����ܺܶ��ڣ�ס����ม��������־����ߵ��ߵ��ˣ������������а��ҵĻ�����ȥ��
��������Ҳ�����ҵĻ�����ֻ��ת�����ܵܵ���Ը���ѡ�
�����������е��������Ƿ������ҽ��и���˵���ϸ��Լ�������������ʵ�Ǻü��ֹ����ⶾƷ��ת���ܸɵ���ĵ�Ȼ���������Ǹ�����ʱ��˼��˼���ˣ������������˵��������ͷƴ�������з��ա��뱻������ȥ����Щ�����궼��û����������ǣ��ͳ����ϸ����ֵȼ�Ǯ�ĵ��ߣ����ұ����Լ��е����գ��������ϵ����ӡ�
���������������һ��������Ȼ��������ȴ�ܰ��˧�����Ҳ���ֻ��һ����ÿ�����䶼������������Ϊ˵�����ѷ������ɼܻ���̸�еȵ�Ŀ���ԣ���Ⱥδ����������������ٲ�����Ҫ����Ȼ���ǵ�λ���£���Щ��������λ���Ʋ��ϣ����������ǵ������������������ԣ������ڰ�����ڵ��������γ���Ҫ��һ���������������˼��Ŵ����ο���С���ĸ���Ը���������ֶΡ�����������Ч��һ����ǡ�����
�������ȿȣ��ǡ��Ǹ�����ï���㡭����ע��һ�¡���
�����������о����ď������Ҳ�˵��һ�룬����ھʹ���ң���̧ͷ�ɻ�����������˵��ʲô�����𣿾Ϳ������ڵ�ѧ��һֱ�������ơ�ԭ������ΪС�����Ҽ�̫����̫�ƣ��Ұѿ�ܺ������Ӓ�����¶������Щ����Ұʱ���µĴ��࣬Ȼ���ҵ����˲�֪��ʱ���̫�����ˣ����Ե���������Ϊ�Ա����IJ����о�����ѧ�ܣ������ÿڵ���Щ���ֶ��ŵ������С�
�������ɣ����������ҾͲ�����ΚG�䣡�ģ�һ��һ���Σ��Ҳ��ң���
�������㿴�������������������Ҹ���ʼ���������㲻�ǻ�Ƿ���Ԫ���ģ�����������G������Ƿ�������ʺò�����
���������ã���Ϸ¡�治�ã������ѣ��ϴγԼ�������ɱ���Ժ��ȥ���������ֵ�������Ц��Ү����
�������G�������۸�ò������ֻ�����û����·�Ե��������Dz��ǣ�ï�硣��
��������תͷ������������������ʮ�����ͷ��С��С��������ֻ��ЦЦ�Ļ���˵�Ҳ���������˵ʲô��������˵��䣬��ͬ���Ҹոռ���δ������к�Ҳ�����ȵĿ���˵����ï��û����Լ�����ļٵģ��ɣ��Ǽ���������
�����ҿ�����ЩС����һ��һ�����������ʮ����������û��������Ǿͼ���������������ʼ������Ҫ��ӵ��ֻ���Ϸ���eͷֻ��һ���Ƚϴ��ʮ����Ĵ�������Ϊ�������ǿ��еļ�ͷ���Ϻ���������õ���Ե�������·��ʣ�µ�С����ֻ���Լ����ÿڵ���·�����棬�ҵ�������һȺ����ͬ�ո���С�İ��Һ����Ĵ����У�����̶�����춼�������ÿڡ�
������ͷ��С�İ��ң�����һ������������ͣ������ź����������������µ����ֱ����Ѿ�������ͷ�ڿ����õĴ�����ߣ��ҿ���СС���ֱ�����������������������ܾ����е�ͻأ�������ƺ����úܰ������������ֵ���ҫ�Լ���δ��ɵĸ��߸壬������ͷһ���Ĵ�������������ɳ�����Ͼٸ��֣��ҿ�������Ҹ��û����Ҹë������ǬǬ�Q�Q�����ӡ�
�������Ͱ�������һ�����ʮ���������յķ�����������������Ƥ�����ó����Ǹ�����ԭס��Ѫͳ����Ϊ�ÿ�ֻ�з��ȴ������ѵ�����¶��������Ȼ���ظ�����ȴ�е�̫�ݵ����ģ��������Լ��и����Ժ���֮ǰ����������ϴ���ʱ���ܽ����ϲ�����������׳˶���ظ������е㾪��������ô������ô��ʱ�һ���˵���Ҳ��С���������Ÿ㶮������˵�ҵļ��ͣ�����ָ�ؼ��������ļ��Ϳɲ�������ˣ�һ��С��ʱ��ʱ����������Ƿʴ�ČŴӿ����e�ͳ���
��������С������ƽͷС���������ͣ�������һ��ʮ���꣬�����������������һ��ÿ����������н��绰�Ĵ������꣬��Ū�������������ڵ��ϰ����ȵ����ӿ�С��һ��Ĵ��������������һ���ÿڣ������������һ����������ʿͼ���ࡣ
���������ÿڳ�����������ˣ��ÿ�ǰ�Ǽ�˽��С�����⼸����������ʱ����æ����ͷ��û��ͷ��ʱ��ʹ���Լ���취ŪǮ��������ͷ���ÿ�����������һȺС����������ò��ȫվ�����Լ�ͷ��д��У���ͷ������۾���������������������һ�۾Ϳ��ó������˵Ĵ�����ͬ���˿�����˹˹���ģ�����Ҳ�ܿ�������Խ��������Դ�ȴһֱ������������ע���ľ�Ѷ��
������ͷ��������eͷ���Ĵ�����˵�ȵ�Ҫ�����⼸��С�ܲ�ͷȥ�����С����������̾�֪����˼��Ӧ�����������˺ø���Ӧ����������䡸�����С����Ǿ�֪����ô����ͷ�翴����ЦЦ��˵��������ȥ�Gʱ��û��־�������ݲ裿��
�����ҿ��˼�ͷ�����Լ�����ܺû�Ը��Ҳ�ô�Ӧ��������˵�����ð������������f�fû��־������ȥ��ͷ��һ�£�˳�����Ρ���
������һ��ȥ�ߣ������µط�����ֻʣ·�ƺ�С���������ģ����ܼ����������·���ҿ�ԭס��ķ�������һ̨�ձ����ʹ����棬������������ҳ�������ҡ�������dz��Σ���������������������������ҡ������ʱ�������ҿ�����Ȥ��ȥ�������к���
����ެ�������С�İ��������˶��������˱Ƚ����ƣ���������Ĵ����к���������ȻҲ����˵û�����⣬�����ᱣ�ֵ���롣�����ʷ�������Ҫȥ��ô����ެ�����Ͼ�˵������ȥ��Ӯ������˵����仰������ȴ�����ں���
��������������������dz���ҹ��������������ʺ���һ������������仰����������Ц������������ڵ��ϣ����Ǻ������Ц������˵����ï�磬�㰢�ڽ���������Ҫȥ����ͬ������ҽа��Ҹ��㽲����Ҫơ�ƣ����ںò�����
�������������Ҫ������������ҶԷ���˵��
�������ⲻ���ҽ��G������ï�磬��ֻ��һ��С�������������ߴ�������ֻ��һ���˵�Ϻ����Ա������������������������������Ȼ�ȵ��Ҹ���������ϴ���˿Ͱ���û��ûС����
��������˵�꣬�����ϾͿ�����ͷ�Ĵ����������ߵ�����������һ�������ɽ����Ȼ������к�ƽͷ�������Ͱ�ǹ���ڿ��e����������Ҳһ���Σ����ո����ͺ�һȺ�����˻��ڴ�綯�����Ӽ������������ˡ������п������ڳ�����ެ�����죬������ò�İ�������˵����ï�磬�Ҵ�G��������Ȳ裬��G�����ǰ��ϸ紦���������Ķ����ˣ����ִ�־������������û���������������
�����������ǻ������СС���������û�����Ǹ�������࣬������������С�к�������һȺ�����ϳ�������Ҳ�ǣ�����֮ǰ���һ���Ƥ���һ��֣��λ����������ϣ��Ҳ�������Ⱥƽ�������ദ���к��ǣ�������ʲôʲôԭ���߽��ÿڣ�Ը��������Щ������˼������ǹȥ������Ӯ��
����˵�ǺȲ裬��û���ھ�ȫ���ɾ��ˡ����ʼ�ͷ��������ÿ�δ���꺢�ӵ�������Ϊʲô���������e������ͷ�����ҵ�����ߵ�Ц���������������ʷϻ�һ�������ո���һȺ������ǰ��˹�ĵ����Ӳ�ͬ�������˱Ͼ����ǵ��ϣ������¶Ǽ�����ͷ���о�¶������Ϥ��ģ�������������ÿڵ�ɳ���ϳ����ơ�����η�Եĸ���˵�⼸������ͨͨ��������ͷ�����ġ�
������ײ����������ֳ�������ͷһ���˴�ѧУ�Ʒ�������ȥ������ͨ���ֽŲ�Ǭ�Q��͵Ǯ��͵�����ԣ���˳�۾ʹ�������������߰�������Ȥ�����Լ������ǣ�������Ҫ��Ҫ˵��ͨ���G���������e��־Ūѣ���������
�����ڶ�ȼ������ͷ�����������ˣ���Ȼ�Ǿƺ�ݳ�������һ���������ÿ��e����Ȼ�ⲻ�������ң����ǵ������ÿ��컨�������鵽������ʽ����Ӱ����һ��ʲô�������¼�ͷ��ͻ�֪�����Ҳ�֪����Ⱥ�к���֪��֪���Լ���ʱ��ض�������������飬�ҵ���Щ�����ʱ�䣬�͵����λΡ�
�����ÿں��и���Ƥ�����Һ���Ⱥ����˯���ĵط�������Ϊ��Ų����λ�Ӹ��ң�ެ������ȥ�����Ҽ����������˼����DZ���һ��˯�����е㱧Ǹ�������ǵ�λ�ã�������ֻ��ЦЦ��˵������������ǿͣ������DZȼ�ͷ���ü����ϸ���ˣ�����Ը����ϡ���Ƥ�ݵ���ͷ�Ա��и�Сԡ�ң�ͨ���к��Ӳ���������̫Զ��ֱ����ԡ�ҽ��С�����⣬�������e��������һ����ɧζ�����Ҿ���һЩ������������Ҳ�����e������Ҿ�������û�غ��ŵķ�϶�e���������������������ͷ���н��绰һ�ߴ���ǹ��
���������͵ļ��Ͳ���С����������Ūʱ�컹����С��һ�����Ϲ�������һ�߶Ե绰���Ͱ�˵һЩ����֮����Դʣ���Բ��Ĺ�ͷ�����������ڵ���һ���죬���������ص�����ָͷ�̼��Լ���ͷ��Ե�����ÿ�ˮ�����궯��ͻȻ��ͷһ����Һ�����ÿһ��������ԡ�ҵĴ�ש���ϣ�ֱ���Ŵ��º������Ͳ�������ͷ��ˮ�������Ϻ������͵ľ�Һ��һ���������������������ļ��ͣ�����Ů���´�ͬʱ��Լ��Ѷ��
����ԭ��������ֻ����˯��ʱ�������Ƥ�ݣ�ʣ��ʱ�䲻���ÿھ��ǹ���������㵽��������Ƥ���e���Ŀ��ܷ������������������f�ˡ�
������֪���˶�ã�������ɳ����˯�������ӿ��������������ŵ����������������ۣ����ſ�һ����һ��ǿ�������ÿڵ���ǰ��������³��������֣������������������ߵ���ǰ�Ŀյأ�����к�һ��û�٣��ڳ��ӵ�Զ��������ֵ��Ƽ����ͺ���һȺ���¿ε���ѧ��һ���������ϲ��DZ����α������ǵ����Ϳ��ڲ�����ǹ��
������ï�磡�������ȿ����ҵ��ˣ��е���
������ï�磡��������Ҳ�����С�
������������ĵ��³���ҹร��G��ï����û��û����Ǻ��һ�䣬�Է�����������
�������������ң����ҹ������磬����ȥ��Ӯʱ�����ͣ���˧����ô�����������Է�������ô����Է��Ĺ��ƣ���������ȥ���������һ����Ӱ���������ǵ�Ӱ�е�����һ����Ӯ���ɻ��ʤ���������������ϲ�����˵ʱ����ע�����һ֧�ֱ������������ֵij����£��ǰ����ĺۼ���
���������������������ԝFζ����ơ�ƣ����˴������⣬�����˶�û������ÿ���˶�����һ���룬���Ǿ�������ǰ�İ���ϳԡ��������������Աߣ���ԭ������Ϊ��Ҫ����û�뵽����Ȼ�ոյİ��������˵ĝFζǮ���ң��Ҹ���˵�����˵�����Ȼ��ְ�Ǯ�����ң���������˵����ï�磬�Ҹ�л������չ����ֵܣ����Һ����ֵ����Բ�����ؤ������Ը��������Ӿ�����Ǯ����
�����������С������ҿ�Ӳ���������е�Ǯ˵����������ȴ��ס�ҵ���Ҫ���պ�Ǯ�廰������Ӛ�����������̫�ã��Ժ����Ǩ߸о�������������������Ȼ�ߴ�־����û���������������뷨��ï������������
�����������С������Ҳ��գ������⡭��Ǯ����������
������˵�꣬Ȼ�����ڸ��ڵĴ�����¶��ɵס�ı��飬�����վݸ��������������Ժ������������������������ร����Ƕ࣡�ҿ�����ߡ��ˡ����e�����ۡ��������ɣ���ǧ�˰���ʮ�壡������Ѷ��Fζม���
�����ҿ�������һ����һ�����죬û�뵽����������ǰ�����������������ֿɰ��ķ�Ӧ�����̲�ס�������ļ��ѧ���������Ӹ���˵�������д�ߣ��������ï��һ�����ӣ�ʣ�µ�Ǯ����Ҫ�ٸ��ң��ò�����
��������������ï�磬����������������ҵ�û�𡣡��ҿ�ʮ����Ĵ����б��ҵĻ���û��ţ��Ҿ�Ц������˵������������������������о������ദ�������ڿ�������Ҳ�ǹ����ˡ���
���������ֵܨ����ǹ���ֻ�����ɳ��������������ֵܿ��������㡣��������˵����ǰ�����Һ�ެ��������Ⱥ�ÿ��ֵܣ�������һ����˳�����ڵķ�Χ������˵������Ϊʲô�д����У���
�������ҿ��綼�����ÿ����һ�ݹ����ǰ�ɥ����࣬��Ϊ�����ޣ����Դ�Ҿͽ��Ҵ����С���������˵�������������ˣ�Ҳ���Ǿ��������ֺ��˵�ƣ���������������һЩ���ĸ���˵˵�����ˡ�
������������������꣬����������ͺʹ�������ÿڣ���������֪�������������Ϳ�ŷ���ݨ���ͷ�ʹ�����͵���è��ɨ߳���ץ����ѵ��ͷ���������������Ҿͽ��������͡��δ���DZ��ѣ���ʱ�����ͱ���ѵʱ��������ð����ɱ����Ҫ�������ͣ�����һ������һ����ɽ�ѵ����
������һ����Ƿ�����ɽ��ԭס���Լ�����ƽ�أ����е����������ʹ�Ҳ������Ƥ���η���ͬ��ڣ���������ƨ�ɾ��η����e��ͬ�ƻơ�����ǰ��ң�����